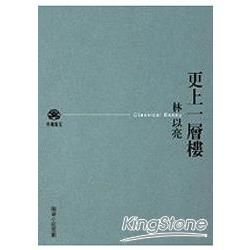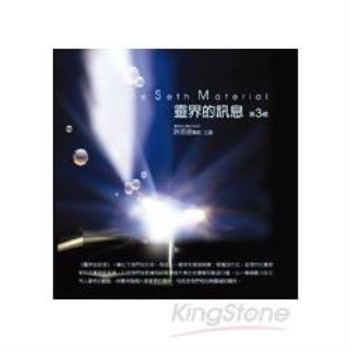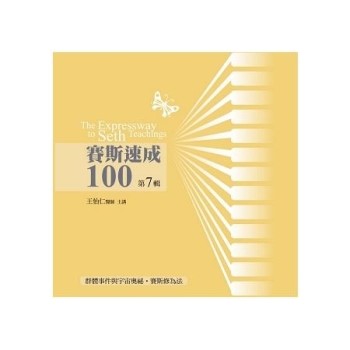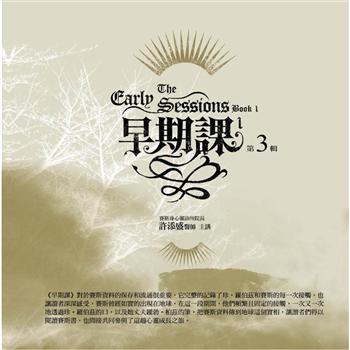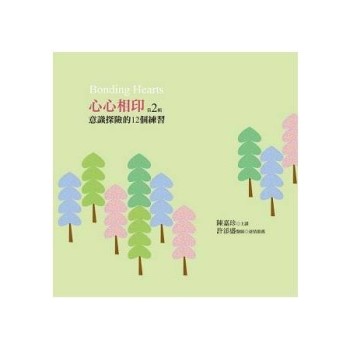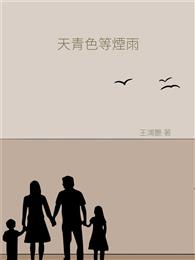駁雜中見性情 黃碧端
《更上一層樓》基本上是一本讀書筆記的合集。作者能體會讀書之樂,進而邀讀者同享,閱讀有所會心,短則發為雜俎式的文思錄,長則出以文論書評。雜記部分多為詩文軼事之隨想和心得,評論則多以翻譯大家或文壇新書為對象。
這本書因而就內容而言,堪稱豐富博雅。作者取材廣泛,古今中外兼收並蓄,書中隨處有趣味盎然的記述和評論。然而也許因為作者對傳統的筆記詩話一類文字多所涉獵,下筆時遂也不免讀書、記人、記事混同兼顧。中國傳統文人每每藉文友酬唱、記事寄託文思、發揮議論,本書頗顯示作者雖是一位接受了「五四」之後西潮的洗禮,也具備了相當的西洋文藝素養;然而基本上保留著中國傳統旳文學感性和知識趣味的人,這樣一種寫作特質,就評論來說,和晚起的從事文藝評論的作者相較,其中主觀和個人品味的色彩頗重,既不拘於理論,也少見建立架構的企圖(以樂曲的組織來詮釋西西的小說是一個例外);就雜俎而言,則題材的多樣自比傳統筆記為繁富多姿。可惜的是,由於和長篇文論、書評同列,這些雜記中或談明星瑣聞、或論文人趣事,不無枝節干擾,以致全書體例駁雜之病。
作者自謂平生之癖在「愛才如命」,這個「自供」事實上也點出了本書的一個特色:除了尚友古人之外,有關今人的評論,書中筆觸所及,亦多在友朋知交中取「才」。倘若觀其書知其人和察其友知其人的說法都成立的話,我們也許可以說,《更上一層樓》是一本從談文論藝和對文友的愛賞推重中流露個人性情的文集,駁雜枝節雖是其病,對於雅好文藝的讀者,卻也不失為一本枕下案頭隨手翻開均可有所會心的書。
──原載一九八八年四月《聯合文學》(本文作者黃碧端女士,現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校長)
不論順逆,無往而不美
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思錄〉發表於一九七七年,最後一篇〈偶思錄〉完成於一九八六年,前後相隔十年之久,數量竟如此微薄,看了不禁汗顏。可是細細一想,在此期間,另外寫過有關翻譯的論文四篇,因性質專門,已收入一九八四年的《文學與翻譯》一書中,而討論詩詞和《紅樓夢》的文章放在一起恐有格格不入之感;只好暫時擱置,留待日後另出專書,則又情有可原。不管自己文章的品質如何,至少可以說明這十年來我在公餘還不斷讀書寫作,將一點心得和樂趣筆之於文,以供同好。書中有些文章談到翻譯,又時常引用詩詞和《紅樓夢》,是題內應有之義;而整書以〈文思錄〉起,以〈偶思錄〉終,採取相同的形式,無意間構成了一個圓圈,周而復始,代表了生生不息和某一階段的終結。這本書,像我其他的書一樣,仍是文美和我長期合作的結晶。多年來她為我摒擋不少俗務,以免我分心,更重要的是她還耗費心神細閱原稿,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盡量減少贅語冗詞,務求行文流暢可誦。難怪友人戲謂我們非但是「患難夫妻」,還可算「文章知己」。希望這本集子依然可以保持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舊貫。
書名採取《更上一層樓》,因為它原是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同時對我說來另有特殊的意義。我絲毫沒有借用這說法來表示自己在寫作的技巧和學問的鑽研上頗有進展,達到更高的層次。我從未幻想自己具有寫作才能,可以成一家言,而且早已深深體會學問之道無邊無涯,不可能在這片汪洋巨浸中出人頭地。古人有志: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缺少那種氣魄和精力。杜甫名句: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躍然顯露詩聖的寬闊視野和浩蕩胸懷,我只能心嚮往之。然而書中文章所提到的翻譯工作者和作家在這期間大都實現了他們的諾言,有出色的表現。霍克思的《楚辭》訂正版於一九八五年由企鵝公司出版,重寫了一篇長達五十二頁的新序。華茲生的《哥倫比亞中詩選》於一九八四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分十二章,自詩經起至宋詞止。余國藩的《西遊記》全譯本大功告成,四厚冊由芝加哥大學出齊。閔福德的《石頭記》第五冊也於一九八六年由企鵝公司出版,霍克思的第一冊出版於一九七三年,兩人的合譯工作較諸「十年辛苦」不遑多讓。
喬志高的《天使,望故鄉》前後譯了十年,兩冊共五十萬字,於一九八五年底由今日世界社出版。林文月完成了《源氏物語》的修訂版後,在譯川端康成等短篇小說之餘,如今從事翻譯另一冊日本古典作品《枕草子》。聽說楊絳正在根據近年來出版《堂?吉訶德》的詳注本重新修訂原譯。
余光中於一九八三年將王爾德充滿雙關和警句的喜劇譯成中文,名之為《不可兒戲》,曾在香港舞臺上分別以國、粵語演出,這是他逸興遄飛之作;他在香港任教時期撰寫的詩文選集《春來半島》於一九八五年底由香江公司出版;散文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則方於一九八七年初由洪範書店出版。黃國彬的《中國三大詩人新論》和詩選《宛在水中央》由皇冠出版社作為海外學人專輯出版;評論集《文學的欣賞》於一九八六年由遠東圖書公司出版。西西的短篇小說集《鬍子有臉》和讀書隨筆《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由洪範書店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眼看我筆下的譯壇高手和詩文名家在這十年中,個個一本初衷,妙藝紛陳,難免自感慚愧。近年除了一九八四年正式退休前為《譯叢》編譯《中國詩與詩學》專號,一九八六年為《聯合文學》編譯《翻譯與文學》專號外,幾乎別無建樹可言。好在讀到上述俊彥的精采譯作,心胸為之開朗,自己的目光也隨著他們的成就伸展得更高更遠。
至於對人生的體驗上,文美和我幾年來倒是有了更深切的認識,的確達到了高一層的境界。尤其去秋病後,深感我們仍是凡夫俗子,做不到聖賢「不惑、不憂、不懼」的地步,但至少能夠不怨天、不尤人,力求心之所安。這半年中,親友的關懷和愛護使我們覺得人世間善意長存。他們往往用一句珍重、一紙便條、一束鮮花或一封懇切的長函傳達好心,帶給我們無限的溫暖。
本書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完成的。我要藉此機會向當初發表這些文章的報刊和它們的編輯致謝,尤其感激蔡文甫先生,若不是他的鼓勵、督促和容忍,這本文集根本不可能問世。文美剛校完第一輯,就發現患癌須入院割治,至今還在接受化學治療,我不得不獨力完成一向由她統籌的工作,因此延誤了出版的時間表和計畫。好在遲出勝於不出,更上一層樓的話,在我們與病魔周旋之際,更應互相陪伴共享面前的光景。多年前我曾在〈論讀詩之難〉一文中,引用過梁宗岱譯歌德《浮士德》中的〈守望者的夜歌〉:
我眺望遠方,我諦視近景,
月亮與星光,小鹿與幽林,
紛紜萬象中,皆見永恆美。
此處不妨再引用一次,並加上最後四句,藉以表達我們目前的心境:
眼啊你何幸,凡你所瞻視,
不論逆與順,無往而不美!
一九八七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