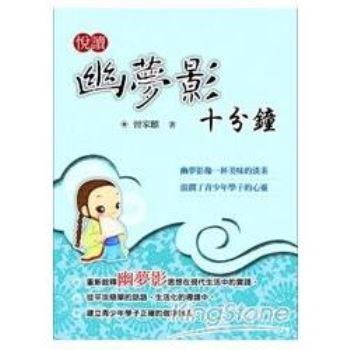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淚珠與珍珠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8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54 |
散文 |
$ 173 |
散文 |
$ 174 |
現代散文 |
$ 174 |
中文現代文學 |
$ 174 |
文學作品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淚珠與珍珠
★永遠令人百讀不厭的琦君散文佳作,重新大字編排。
★特別收入名家廖玉蕙、畢璞、黃嘉靜、陳素芳等追思紀念文章。
琦君散文作品,以最精簡、優美的文字,表達最真摯、深沈的感受,幽默雋永,深入心田。雖客居異鄉,而說婚姻、談生活,哀矜眾生可憐復可惡,檢視人性的美好與缺陷,義正詞嚴又極富人情味。寫人生況味、懷舊憶往,捕捉美好的剎那,更是如歌的行板,哀而不傷、趣味盎然;稚子情懷、慈藹之貌,一覽無遺。
作者簡介|
琦君(1917-2006)
浙江永嘉人,民國六年生。五歲開始習字,閱讀中國古典詩詞,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央大學、文化大學等校中文系教授。從古典文學過度到現代文學,她的文字被公認為最成功的典範,她的文章最為人稱道的是溫柔敦厚,悲憫人性的弱點。榮獲文協散文獎、中山文藝獎。《鞋子告狀》榮獲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此處有仙桃》榮獲國家文藝獎。著有《母親的金手錶》、《橘子紅了》、《三更有夢書當枕》、《青燈有味似兒時》、《淚珠與珍珠》、《水是故鄉甜》、《萬水千山師友情》等散文及小說、兒童文學等書四十多種,作品多次為《讀者文摘》中文版轉載,曾被譯為美、韓、日文,極受海內外讀者喜愛,也是作品入選中學課本最多的作家。旅居美國多年,返台定居於淡水,2006年6月7日病逝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