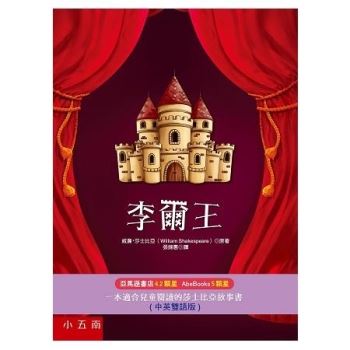大世界的雜語演出
一 本書靈感的由來
兩年前的夏天,我正在苦苦構思《上海魔術師》這本小說,信步走到大世界門口,吃到了香噴噴現煎的臭豆腐。正滿心高興著,抬頭一看,大世界關了鐵柵,落了大鎖。旁邊的人看到我一臉驚奇,就說:「破產了,永遠關門了。」
痛惜之餘,我在這本書裡重造了一個大世界,這樣的「遊樂場」,是雜語的狂歡之地,複調的競爭之所,現代性的實驗地,中國文化的符號彈射器。我的主人公,進了大世界更加鮮活蹦跳起來,他們哭,他們愛。
我相信那些望文生義懶得仔細讀書的批評家大教授,那些喜歡無中生有恨不得把煙煽成烈火的編輯,一看我這書名,就笑岔了氣。簡單的中學生知識:這小說肯定是小模仿《盧布林的魔術師》,肯定是大模仿《大師與馬格麗特》?
現成的機會:街頭惡少起鬨,不偷打一拳白不打。
前年全國報紙轟傳我的中篇《綠袖子》「涉嫌抄襲」莒哈絲《廣島之戀》。追問到底,竟沒一人如此說過。可只要一個網站開個頭,說某人說過一次,其他媒體全會跟上。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要問起先的影子在哪裡?哪個犬都朝你翻白眼。
思前想後,我索性就給嗜好這一套幼稚園式批評的人翻開底牌:這部小說靈感的源頭在何處。
我最早想到的書,是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發條橙》(Clockwork Orange)。這本書有中譯本,完全丟失了原書語言的怪味。原書是未來社會中一個小流氓自述的犯罪史,用一種英語、俄語和意第緒語的混合語,原文讀起來怪異百出,英文讀者大致能看懂,卻非常驚駭:在墮落的未來,英語也被蹂躪成如此樣子!這本怪語小說,卻是單語小說:主人公兼敘述者的語言一路貫穿。
《上海魔術師》沒有走這條路。因為我想寫一本雜語小說。
我的小說,如果有模式,那就是喬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一本無法翻譯的書,當然至今沒有中文本。語言能變形到如此程度,就舞蹈起來。葉慈問:「如何分清舞蹈與舞者?」一旦語言表演柔術,肉身扭曲起來,魅力就成為語言本身。
論者說《芬尼根守靈》依仗了西方語言多元的根,那麼現代漢語呢?現代漢語也是多源多根的。至今中國作家做的是單根追源──京味小說、秦腔小說、湘語小說、鴛蝴式小說。我在想,把現代漢語的多元多源,不朝均勻靠攏,而是向各種源頭方向拉,像宇宙大爆炸一樣飛散,情形會如何?會開拓出幾個星系?
所以,這本書,是一本複調的「《發條橙》」。
二 蘭語小說
於是有了這本語言實驗小說──讓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各說各的語言,各想各的語言,各用各的語言敘述故事。
而這幾個人物,語言風格完全不同。
猶太人所羅門「王」,說的想的敘述的,是《舊約聖經》的語言。這種風格,容易標記,但用於中國的日常生活,就有些怪異──不過現代漢語的形成,正是來自吸收怪異的外國說法。各種外語的翻譯,對現代漢語形成的決定性影響,文化史家一直沒有給與足夠重視;
所羅門的對手「張天師」,說的想的敘述的,是中國傳統江湖語言。《水滸傳》、《金瓶梅》裡的俚俗語,已經不用了,晚清民初,江湖語言卻有新的發展。我小時候熟悉的流浪漢語言,川江水手中會講故事的能人,他們說的話之生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所羅門收養的中國孤兒,「加里王子」,是個語言海綿,把舊上海流行的任何語言──洋涇濱英語、市井語、「戲劇腔」,以及養父的半外語,全部吸收混雜起來。我努力「創造」加里的語言,後來發現,這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現代漢語就是一種多元複合的語言,加里的說話方式,只是把元素重新分解開來;
張天師刁鑽古怪的女徒弟蘭胡兒,從小天天練柔術,把身子折過來疊過去,她說的想的成為變形的肉體之代言,一種只有這個人物才說得出來的「蘭語」。這個「蘭語」讓我傷透腦筋:我必須在腦子不斷讓漢語演柔術。蘭胡兒是整本小說最主要人物,《上海魔術師》基本上是在蘭胡兒的觀察和思想中流動,因此,這本小說,不可避免是一本「蘭語小說」。
加里王子和蘭胡兒是這本小說的真正主人公,這對少年少女在四年之間,痛苦地長成男女青年。由此,必然有童稚語與成人語的對立,也有敘述語言本身的長大過程。
我怎麼分得清柔者與柔術?
蘭語就是我的語言。
蘭胡兒就是我。
三 雜語之美
這是一本眾聲喧嘩的小說,是各種語調、辭彙、風格爭奪發言權的場地,自然不是《海上花》那樣的「滬語」小說,雖然上海話免不了衝進大世界來打擂台。
中國的現代化,正像現代漢語,就是各種聲音各種文化衝突競爭、對抗、雜揉的結果,哪怕勝者,最後也發現自己吸收了對手的語彙。
我說過了,我的實驗,正是想把現代漢語拉碎了來看。這個語言實驗,也是中國現代性的分解。現代中國文化的轉型,正穿行在這種「雜語」中。
說這話,不是炫耀,並非自誇我做到了現代中國作家沒做到的事,而是說,我試圖做一件中國現代作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做的事:雜語化小說。
再說一次,我不是說其他作家作品中沒有複調雜語,我是說可能(可能!)我是現代中國第一個有自覺意圖,試寫雜語小說的人。
把小說放在「大世界」,也是為了這個雜語目的。大世界,就是不讓一種演出方式獨霸,各種戲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吸引看客。你說我唱,各擅勝場,保持雜亂,拒絕合一。
究竟是雜而合一更美,還是分一而雜更美?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化中合一的因素太多,現代漢語似乎已經有標準(這不完全是好事),不合標準謂之惡搞,謂之出怪。其實,這個合一的表面,掩蓋了多源漸漸合一的流程,掩蓋了曾經有過多元並存。我把這流程放到一本書中,目的是想讓自己,讓大家看到漢語曾有的雜出之利,將來或許會有的多變之美。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大世界,我們也會再有一個漢語大世界。
四 讀者與譯者
在文化市場化的今日,我這麼做,是否逆潮流而行,是否有意讓讀者討嫌?畢竟讓大世界關門的,是無情的市場。
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文化人似乎把讀者看得過於片面了,要不就是無知群氓,要不就是手握鈔票的諸神。
其實錯了,讀者本身,就是雜語之根,他們肯定能明白,他們自己就是中國雜技與西洋魔術的兒女。讀者可以通過不同文體,分頭進入蘭胡兒與加里的世界,最後攜起手來。
此文不談小說的內容主題等等。其實,正因為這是本文體實驗小說,故事就不得不更精采一些。精采的故事,如艾略特所說,是「騙看門狗的肉」。我想在故事後販運的「私貨」,已經公開於上,敬請垂注。
當然,這就要請批評家大教授編輯們多花幾分鐘讀書,才做斷語。反正,讀者們是一如既往,會讀了書才笑幾聲,罵幾聲,或者誇幾聲。對此,我從來深信不疑。
有些批評家一口咬定,我的小說都是為翻譯而寫。對這些想當然的懶人,我已經放棄了說服他們的努力。
這本書會不會有人翻譯?我無法預料一本書的命運。不過,我能說:翻譯者,我同情你!如果你只能譯得像中譯本《發條橙》,不譯也罷。
大世界中的小世界
一
他對我說,到上海去,上海會讓你著迷。
他還說,她會喜歡你。她住在富民路的弄堂房子裡,她果然待我如自家閨女,邊挾菜給我邊說大世界那些哈哈鏡,那些坤角旦角,陳年穀子一粒粒道來。說是第一次進那兒就迷了路,人一生迷一次路值得。
她打開衣櫃,抖了抖那裁剪合身的花布旗袍,上面的樟腦香讓人感覺到韶華飛逝。我得順著那舊電車鈴聲,在那會迷路的地方下來,推開那扇厚重的大鐵門。
他們全在,等著我,一看就已等了許久:雜技女孩蘭胡兒邊上是燕飛飛,張天師站在石階上,大廳另一端是魔術王子加里和所羅門王。
所羅門王說,他做了個噩夢,好久沒有請人圓夢,要開口跟人說,卻忘了夢。這會兒他正在想那個夢,就是發生在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五年已到了,就在眼門子上。
蘭胡兒得和加里分離,他們背著困惑之極的身世之謎,在亂世一次次從死亡中逃脫,一次比一次明白,此生不能分離。
是呀,戲就要開場,故事就如此開端。
二
面對大世界的那些樓梯,我是個膽小鬼,一個人走著時心驚肉跳。很多的聲音,包括鬼聲,飄入耳朵。當我跑到大世界外來遠看,黃昏落日,站在天橋上吃著臭豆腐,他千妖百媚的上海呀,吸一口氣,香氣就鑽進我身體裡。
最後一次去,是在非典(SARS)後,鎖上了門,而且從那以後就沒有再開門,乾脆不營業。
他被拉了壯丁,輾轉大小城市,最後停留在重慶,一生沒有回來,他是我最愛的人。眾所周知他是我養父。
她是他唯一的妹妹。她生得秀氣,與小說中的蘇姨一樣不愛說話,可一說話就句句到點子上。她和他不太像,因為她是他家在饑荒時救下的孤女。
亂世之中,兩人天各一方,彼此思念。她與我說得最多的是不在人世的哥哥。
夢裡夢外,他倆用一顆普通人的心領我朝南走,棚戶區,這兒是真正的上海百姓。我成長的貧民區山城也是如此,再窮得叮噹響,入睡後還是有色彩繽飛的夢。蘭胡兒和加里有這樣的夢,他們和任何政治無關,雖然政治找著他們不放過他們。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只求生存下去。
三
寫作這小說的一年半,開始是防盜門鎖壞,叫人來修,結果弄不好,最好換掉。然後是印表機壞了,修時發現是磁頭壞了,換掉。用了好多年的音響壞了,只能放磁帶。只得換掉。冰箱突然一點也不發鮮,放進去的青葉子蔬菜發黃,也只能換掉。之間經歷的修理與買東西的種種欺騙不能回想,壞掉的未必不是天意。寫這小說,前後經過了北京重慶成都倫敦,北京香港、德國和義大利諸多城市,突如其來的命運變故幾乎毀滅了我,是精靈女孩蘭胡兒救了我。
愛你就是要不顧一切。愛你到現在才知失去你可以,不能失去自己。
說句狠話真是生不如死,死不如寫這兩個魔術師。穿過時光之鏡看見了內心冰山另一角。一個已過世法國女作家的聲音在耳旁響起:又一艘客輪起航了。每次起航總是一個模樣。每次總是載著頭一次出海遠航的旅客,他們總是在同樣的痛苦和絕望之中和大地分離。
天已暗下來,烏雲堆積。我脫了鞋,像蘭胡兒一樣,由著天性,拋開身後一切,升起帆,但願雨下得別這麼無情,閃電因為我遠行稍稍有點兒禮貌,但願向我揮手再見的養父和姨,淚水都嚥在心裡頭。
九點零十分,冰雹也來了,是我離開的時候了。
曾跟蘭胡兒和加里王子朝夕相處,現在他們年輕的氣息還環繞在左右,他們的聲音依然在夢裡出現,就是昨夜,我走了很遠的路,走得氣喘吁吁,看見了心愛的獵犬珂賽特,跟著一個粗壯的獵人,奔忙在深山裡,被追擊的狼在?叫。冰雪如鏡,映出我蒼白的臉,魔術之棒上下移動,隨她也隨我,我們會在另外一個世界相遇。
這本書是紀念我有過的小世界。上天給的東西不能奢求太多,有一丁點就該滿足,若是連這一丁點也沒有,還是應該感激。現在我感激你──不管你是一個人或是珂賽特追捕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