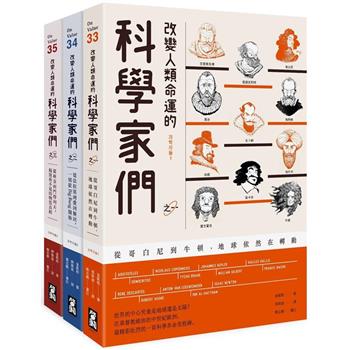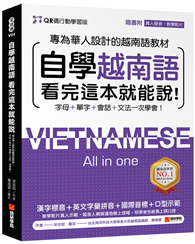一些關於段正淳的事
金庸的《天龍八部》電視劇在大陸播了又播,小說則是賣了又賣。其中蕭峰英俠豪邁,最獲欣賞,但人們並不能在現實世界中見著他;倒是段譽、段正淳及一干姑娘們的大理國,現在還可以去遊歷徜徉。
多年前,瓊瑤拍「望夫崖」,還特地把劇組拉到雲南,編了一段劇情。戲劇進行中,螢光幕上竟然打出長篇廣告詞,提醒觀眾注意:這是在大理拍的、動員了多少白族人士、演某角色者係白族少女,並請觀眾欣賞他們的「白族國語」等等。如此荒謬的播演法,足以顯示:在某些人心目中,大理是極特別的地方,所以禁不住要用這種方式提醒大家:我到了大理耶!
可惜,一般人腦子裡對大理的印象也就是如此。或者,加上個大理石吧!此外就不太曉得還有些什麼了。
這也難怪!大理立國,唐有南詔,宋有大理。可是大理國三一六年歷史,在《宋史》中卻只有寥寥六○四個字,其他資料也不多,近代之研究更是比南詔還不如,一般人感到陌生,豈非情有可原?如台灣自產遊戲經典「仙劍奇俠傳」也安排了一段南詔、大理的劇情,但那兒住的竟然是「黑苗」、「白苗」。可見時人對大理之無知,而就是金庸、瓊瑤,所述亦多可商。
大理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都是白族,更不會是苗族人。在南詔時期,王室是屬於彝人的「烏蠻」。大理時期,段氏王朝與烏蠻三十七部歃血為盟,可說是共同擁有政權。現在白族也過的六月二十四日火把節,大約就是傳習自彝人的風俗。可是烏蠻與白蠻畢竟頗為不同。烏蠻男子剃髮、拔去鬍鬚,女子穿黑衣,長裙曳地。白族女子則穿白裙,長不過膝。白族也行火葬,但烏蠻在焚屍前要先把兩耳取下,貯在瓶裡,拿回去四時祭拜,與白族不同。
另外,白族還有個特點,那就是生食。《馬可孛羅遊記》第一一七章就提到:「此地之人食生肉。不問其為羊、牛、水牛、雞之肉,或其他諸肉,赴屠市取甫破腹之生肝,歸而臠切之,置熱水摻和香料之佐食中而食。」這可不是他造謠,白族確是食生肉的民族,伴著鹽或蒜泥來吃。段正淳、段譽及他們那些女人若在,大概也是如此。
說到女人,大理國的女子中,白族是不施粉黛的,打扮之重點只在於頭髮。另有百夷,也就是俗訛為擺夷的金齒、銀齒、黑齒、繡腳、繡面各部,乃越民族之屬,今或併稱傣族。金齒,是用金片做牙套嵌在齒上。黑齒,是把牙齒染了,或因吃檳榔一類東西而令牙齒一片漆黑。繡面、繡腳則是指他們紋身。男人紋了後,拔去鬚鬢眉毛,用紅土白土傅面,彩繒束髮。女人不紋身,但剃了眉,不施脂粉,髮分兩髻,另塗彩在雙頰或額上。也有用彩繒裝飾兩髻的,稱為花角蠻。就是麗江那一帶的麼些族,女人也「終生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樊綽︽雲南志︾卷四)。這些妝扮,恐怕都與我們腦海中靚女麗人的想像相去甚遠吧!跟金庸書裡木婉清、刀白鳳等女子之插畫圖像,實在大異其趣。
至於段正淳與段譽之關係嘛,嗯,當時大理可沒這樣的父子。因白蠻、烏蠻都源於氐羌,採父子連名制。例如大理最後幾任君主,是段智祥傳段祥興,再傳段興智,兒子用父親名字的末一字連接著命名。早期幾位,則以重複的方式連名,如段思平兒子叫段思英,段正淳的兒子叫段正嚴,都重複一個字。這是他們與漢人最不相同的地方。
這其中,段思平是大理前期開國之君;段正淳的風流,卻也許是誣賴了他,他好歹也是後期的開國之君。什麼前期、後期呢?大理原先立國,頗仰賴貴族高氏、楊氏、董氏之力,但其後尾大不掉,善闡侯高升泰竟廢段正明自立,國號大中。可是他只在位兩年就病死了,遺命還政給段氏,於是段正淳就位,史稱後理國。段正淳的兒子段正嚴,在位四十年,勤政愛民,但老來「因諸子內爭外叛,禪位為僧」(《南詔野史》)。其後各王奉佛越來越虔誠,而國勢卻越來越衰,終於被蒙古大軍所滅。
段正淳、段正嚴的風流韻事不可考,倒是前期的段素興,據《南詔野史》記載,乃是個好狎妓載酒、鬥草簪花的人。而且「花中有素馨者,以素興愛之故名。又有花遇歌而開、有草遇舞則動。興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蓋亦花草之妖也」。這花,倪蛻《滇雲歷年考》說它由波斯傳來,但也有書上說是漢代有一女子名素馨,為情而死,花生墓上,故以為名,所以此花又有「情花」之稱。總之,不管如何,有段素興這樣愛花的人,才有素馨這樣奇絕的花。可惜金庸沒有在他身上做文章。
大理除奇花異草外,據說還有不少珍禽異獸。其他的也就罷了,一種鹽龍最奇。《春渚紀聞》卷四說狄青破蠻洞時,「收其寶物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筋摭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服。
這種鹽龍,不見於其他記載,不知究竟為何物。但牠吃鹽又生鹽,其實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吃的並不是海鹽。大理乃是岩鹽區,故鹽龍也者,大概只是該地產鹽之象徵,因老百姓砌灶煮鹽,正如鹽龍般吃鹽也生鹽。
而更稀奇的,是他們還以鹽作貨幣。馬可孛羅說是煮鹽後用模型做成塊,每塊約重半磅。大約類似茶磚。他們跟宋朝做生意,亦以茶鹽為大宗。
現在雲南鹽已罕見,醃製物,著名的只有宣威火腿,不太看得出當年食鹽之風。茶卻越銷越旺,普洱茶的價格俏得很。可是當年段正淳等人喝的,想必不是如今這般之茶。當年大理人採的是散茶,沒什麼製茶工藝。採了後,加上椒鹽一塊兒煮著喝而已。可是茶的貿易當時卻已甚盛。因為宋人向大理人買了茶來加工,再賣細茶給大理人以換馬。茶馬貿易,遂成了中原與大理的主要關係。
元朝以後,雲南的茶馬貿易轉向印度、西藏和緬甸,格局迥異於大理時期,大理之舊事亦漸就湮滅了。如今,藉著金庸、瓊瑤的小說戲劇,雖勾引起不少人的思古幽情,但古史難稽,大理國的故事,畢竟仍如雲霧中的點蒼山,令人難以看得清楚啊!
自由的翅膀
這兩年在大陸遊歷,屐屨所經,誌為雜文。去歲嘗承蔡文甫先生好意,刊成《孤獨的眼睛》一書。如今續有所作,輯為本書。為配合那一本,故名為《自由的翅膀》。
自由的翅膀,原是《孤獨的眼睛》中一篇文章之舊名,但起意實本諸《莊子.逍遙遊》。莊子論逍遙,取喻於鯤鵬,而命意大旨,在於說明人須「無待」才能逍遙。無待,是人無所求、無依賴,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的大自由大自在境界。此所以為逍遙,此所以為遊。
這種遊的精神,我在舊作《遊的精神文化史論》或《孤獨的眼睛》中已談得很多了,因此此處也就不必再做申述,只落實到我現在這本書上說說。
莊子描述的逍遙無待之遊,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乎無窮。」這在精神境界上說,固然如是,但我在世上遊歷,這個世俗屎溺稊稗之境、荊棘烽煙之場,卻是無法逃的。逍遙的大鵬鳥,除了要翱翔於天宇之外,同時也要一步步走過這世俗社會。
而現在這個社會是個什麼樣的狀況呢?相信讀者比我更清楚,用不著我再來發牢騷。在這樣的社會中,旅人看起來已對之無所繫念,故願自束行囊、自放於山巔水涘,不再介入世俗的經營機詐中去競逐了。可是行旅於斯世,所見所聞所歷所經,仍要時時引發我們的喟嘆。
可喟嘆者甚多,單就旅遊來看,現今就處在一個將旅遊文化產業化的時代。我們都不再能如徐霞客、王士性那般地遊了,商業體制裹脅著人,由生活領域延伸到了旅遊領域,原本應該是逸離塵囂,可讓人暫逃俗世機栝,獲得自由的遊旅活動,現已更深更緊地與資本主義產業體制結合起來,吞噬了人的自由。於是旅遊變成觀光、豐盈自我變成消費購物、叩寂寞以求音變成了縱欲狂歡、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變成了開發經營、優遊卒歲成了按行程操兵式的「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到處拍照,不然就去買藥。」就是那旅遊文學,嘿嘿,說穿了,也只是旅遊產業的宣傳品罷了。附從於其價值、依存於其體系、編納於其組織運作中,而令觀者與寫者均不自覺。
旅遊在這個時候,便不是讓人喪失了自由,丟失了人與自然、人與歷史的聯繫,而是使人去消費或消耗其自由,並消費自然、消耗歷史。
對於此等情境,我不能在理論上多所論析,因為那可能會讓讀者打瞌睡。可是我有一些具體的感受,願藉我旅遊之實例稍加描述。我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去大陸旅行,迄今近二十載,這兩年尤其住得久。遊蹤萍寄,遍及南北。又適逢大陸文化旅遊產業興起的時機,所見所感,自然稍多於常人。自由的翅膀,帶著我孤獨的眼睛,在旅中偶爾就看了這書中所記的一些事,寫了這一堆雜感,對當代旅遊文化做了個小小的批評。
感謝《中華日報.副刊》主編羊憶玫為我闢了個「書劍天涯」的專欄,按期刊登這些散文。但我四處野逛,行蹤莫測,交稿有一搭沒一搭,恐怕令她十分為難。如今,稿子結集成書,我自己再看看,想起寫某篇時在某舟中、寫某篇時在某荒村、寫某篇時又在某某旅邸,一時卻也棖觸良深。所以,嗨,不說了,各位自己看書吧!
龔鵬程丁亥春中四月半
記於台北龍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