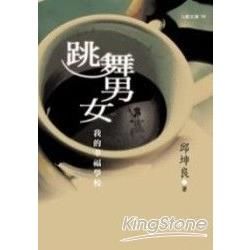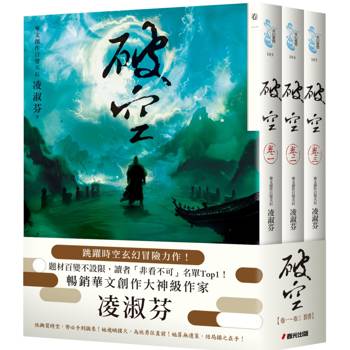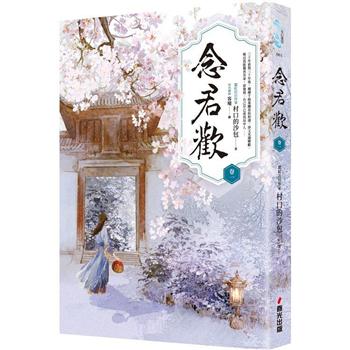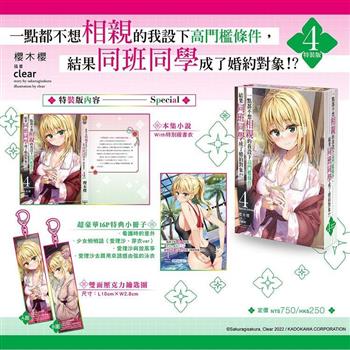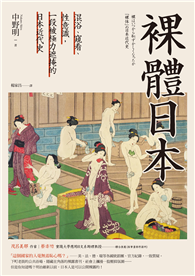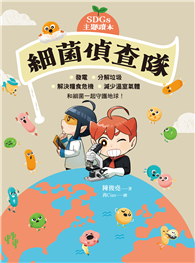幸福的所在
以往常為一杯午後咖啡而感受快樂人生,最近,午後咖啡的「傳統」價值之外,又衍生出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覺。但是,幸福在那裡,卻又難以名狀。 午後幸福感的確切時間,是從十二點三十分開始。在此之前,心情沈重,連正午都還不能紓解,而且,為了期待即將到來的幸福,更容易焦躁不安。我原來不太理會午間情緒的變化,有一天上午心情極端壓抑,下課之後突然鬆懈,竟如大夢初醒,歷劫歸來,而後我逐漸體會這種心情的轉化,也是人生小小的幸福。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所期待的,必然是極具生命價值、卻又艱困無比的光榮戰役所帶來的榮譽與滿足。其實我的幸福感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花樣,對別人不具意義,與「天降大任」更相距十萬八千里。然而,它伴隨我最新的「苦讀」經驗,讓我先蒙受壓力,再以阿Q式的「活著真好」,增加生活趣味與學習動力。 最近的幸福感源起於年前在大學戲劇系教書的我,突然被調去「做官」,朋友形容就像在路上走著走著,不分青紅皂白被抓去「做兵」……。面對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媒體生態,當官沒有什麼好得意,更談不上有何尊榮感,原預定兩年四個月的兵期,在一年四個月之後,提前退伍,比我實際服預官役的時間還短。不過,這段「當兵」的日子,仍是人生難得的體驗,可以近距離觀看光怪陸離的官場百態,增加教學與創作的題材。
結束借調,回歸校園,重新當起教授,剛好輪休年假,不但不需要開課授徒,反而當起學生,跟年輕人擠在一起,接受老師教誨。我參加的課程並非尖端科技,也不是什麼超自然潛修冥想,只是一家語文補習班開設的普通日文課程,無須任何能力條件,也不必經過入學測驗,只要繳得起錢,任何人都可以登記上課。我年紀一大把,在補習班中雞立鶴群,十分突兀。
這不是我第一次接觸日文課程,小時候生活周遭就充滿日本經驗,左鄰右舍的阿公阿婆開口閉口都夾雜日文,學校同學也經常怪腔怪調地模仿電影中的日本武士講話。三十年前唸研究所時,還修了二年的日文當「第二外語」,只是年少無知,直覺日文非常簡單,用看的、猜的,就能應付了事,終致光陰虛擲,浪費生命。多年來我的日文程度十分「苦手」,看日本資料有一大半繼續靠猜測。這幾年深知日文的重要性,愈來愈覺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多次進出日文補習班,希望能拉抬日文程度,但因年歲老大,又不用心,結果還是半途而廢。最近終於因為提前「退伍」,加上年休假的關係,鼓起勇氣,以即將進入退休的高齡,再次到日文補習班「勉強」,接受嚴苛與無情的考驗。我很清楚這應該是學習日文的最後機會了,失去這次的「勉強」,這一輩子就永遠與日文無緣了。
日文課每週五天,每天三小時,從九點半到十二點半密集上課。「同班」同學有十幾位,年齡都很小,不是大學生,就是剛從高中畢業不久的少年家,居然還有一位國中生。授課老師是一位身材微胖、膚色黝黑,長相甜美的台籍婦人。她第一次上課時,要同學猜年齡,小朋友一本認真,「四十五」、「五十」、「五十五」,像喊價般毫不嘴軟,她只是微笑地要大家繼續猜。最後問到我,我毫不猶疑地說「三十五歲」,她高興地大叫:「你猜得真準!」其實我以為她應該在五十上下,比我小不了太多,猜她三十五歲,只是基於世俗的禮貌,故意逗她開心,沒想到居然「猜」中。
這位老師為人風趣、熱心,精力無窮,三個小時的課程一下中文一下日文,偶爾又有英文與台語,唱作俱佳,滔滔不絕,進度與節奏時快時慢。有時像在為大學第一志願考生上「必勝」課,準備一堆講義,不斷補充教材,還經常為缺課的同學個別複習,「三小時吃到飽」;偶爾又有「日本時間」,天南地北,閒聊人生體驗,包括她的東京留學生活、如何對付「阿本仔」,以及第三隻眼看到鬼的經驗,她在課堂上誇張地說:「我在台灣很少看到鬼,為什麼日本的鬼那麼多?」這些話題年輕同學聽得津津有味,我卻索然無趣。不過,久而久之,三小時的枯燥課程,能藉著沒營養的話題打發一些時間,解除上課壓力,感覺倒也不錯。 我在日文課堂上反應慢,記憶力又差,常常跟不上進度,唸起課文結結巴巴,極不流轉,許多日語文型唸過幾遍,仍然記不起來,也不會活用。相形之下,這些小我三十歲的小朋友學習能力極強,老師怎麼教都無所謂,兵來將擋,一聽就懂,在他們面前,我顯得奇笨無比。我曾找出以前上日語課的筆記,上面寫得密密麻麻,似乎也曾唸得滾瓜爛熟,現在卻毫無印象,好像從未學過阿伊屋野歐。如照以往的上課習慣,這樣的課程不上也罷,早該放棄,此番卻下定決心,打死不走。為了讓自己不在密集的日文課程中窒息,我開始調節心情,發揮「移動觀點」,學習苦中作樂。
我每次上課心情沈重,壓力不小,三個小時的課程宛如三個月之久,度時如年,有夠拖磨。從九點半開始上課,就等著下課,頻頻拿出手機看時間,第一個小時熬過,小小的欣慰,第二個小時也熬過,略有成就感,第三個小時進入備戰狀態,分分秒秒地期待「階段性」使命的完成。歷經三小時的煎熬,「劫」後餘生的那一剎那,心情非常愉悅,尤其想到馬上還可以享用一杯午後咖啡,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愉悅的心情從中午十二點三十分下課開始,一直延續到晚餐時分,整個下午的生活非常充實。然而,用過晚餐之後,想到隔天的課程,心情又逐漸鬱卒,第二天早上心情更糟,中午過後才又開始「幸福」。一個普通的課程竟然產生壓力與抒放,每天心情高低起伏,有挫折,也有期待,以及百味雜陳、週而復始的興味。 從尋常事物發掘樂趣與價值,一直是我的生活方式與學習態度,即使最近幾年的教學、寫作與行政工作,案牘勞形,忙碌奔波,仍然樂此不疲。行政工作要深思熟慮,眼觀四方,耳聽八方,但不需要像計程車司機或卡車捆工,得無眠無休地苦幹實幹,也不是每天盯著電視畫面,或徹夜不眠,就可以興利除弊。就我而言,對生活、工作以及周遭人事物有所感覺,才有思考空間與創作動力,與是否負責行政工作沒有太大關係。
一位作家朋友形容我公忙之餘仍能創作不斷,在於需要一種形式,來記錄、傳遞我所關心的藝術、生活議題,只要對周遭環境有感覺,就會冒出「故事」,就會忍不住提起散文之筆。也因為這種創作因緣,所以一直到今天,都不會被官場或其他規矩給壓抑下去。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所謂「故事衝動」,但生活周遭的一點一滴都是我創作的泉源與體驗,也是幸福人生的起點。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藝術展演,甚至行政管理,一切皆從「生活」出發。任何題材皆能寫成學術論著或研究報告,創作劇本、小說、散文,或作戲劇展演;有如蔬菜魚肉,蔥蒜蔬果,加上不同劑量的佐料,就能做出不同風味的菜餚。
能夠回到「一般」官場小花臉管轄不到、注意不到或想像不到的大學校園與劇場舞台,悠然自得的思想與遊戲,彌足珍貴。短暫的官場進出,提供我更多的創作空間與思考角度,現實生活中的是非善惡都是人性的表現,不分貴賤尊卑、悲歡離合,每個人都可以做好角色扮演。縱然窮凶極惡、奸佞狹詐之徒,亦為戲劇舞台所不可或缺,觀眾也能以寬容、平常之心面對不同的Casting,「戲臺上有那款人,戲臺下就有那款人」,因為他們的存在,人間戲劇才能生動地上演。 每天辛苦上學,快樂放學,心有旁騖,日文也不會因而「上手」。但上課代表一種進步,學習本身就是生活,中老年人重新扮演學生,聽年輕人傳道授業解惑,有不少尷尬,也需要勇氣,卻更是一種幸福。隨著我上課下課的情緒轉折,熱情聒噪的日文老師,忙碌的有些無厘頭的櫃臺小姐,以及乳臭未乾、人小志氣高的「同班」同學,每個人的臉龐都閃爍有神,而原來空間狹隘、毫不起眼的日語補習班,居然寬廣明亮有如我的大學校園,成為小小的幸福招待所。
二○○七年八月
推薦序
踏歌如夢飛 王孝廉——記邱坤良與博多二三事
一、博多夜船
越過了松原,你又來看我?
可看見往來博多的夜船燈火,
可看見夜船燈火。
讓愛的夜船,趁黑夜回去吧!
若天亮將無風起浪,
流言四起、耳語四散!
在玄海那裡,浪頭一定很大吧!
我不想讓你回去,
你是難以割捨的那艘船!那艘船!
小學生邱坤良,在「去日本化致力中國化」的童年,對東洋來的演藝、歌謠,有著一種欲迎還拒的矛盾心理下,不知不覺地熟悉了這支歌。 是歌好?還是歌者好?
邱坤良以這首歌和唱這支歌而紅遍日本台灣的美空雲雀的一生,寫盡了戰後五十年來的世事流轉和人間滄桑。
為了一個虛無飄渺的童年浪漫,為了想看看博多藝妓、坐坐博多夜船……。終於有一天邱坤良輕裘緩帶,從容坦蕩飛到博多。
年輕的博多人已經不知道博多夜船。沒聽過、沒唱過,也沒坐過。這裡的年輕日本人雖然也知道國民歌手美空雲雀,但很少有人在乎她是誰,以及唱過什麼樣的歌。一切正如邱坤良博多之遊的所見所感。
畢竟博多夜船、藝妓、演歌,都是上一個世紀之前遙遠的追憶,早已如過眼雲煙。二十一世紀的新人類對這些歷史記憶,由內心到外在,都很難產生共鳴。台灣知道美空雲雀的人,不可避免地,將愈來愈少。《博多夜船》不管日語版、台語版,也已接近絕響,老一輩的日本情結終將在台灣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或許是全球化的日本時尚吧! ——〈博多夜船〉
老一輩的日本情結終將在台灣銷聲匿跡,新一代的日本情結卻仍然方興未艾。小吃店的黑輪甜不辣、西門町漫遊的狀如東洋娃娃的哈日漫畫少女,以及文藝界廣為使用的那個狀如鰻魚的「?」字。邱博士?書房,私?杜麗珍,午後?紅茶,大嬸婆?客家小炒……,你儂我儂。老兵不死,夜仍年輕,只不過是年老的藝妓,經過染髮整容,脫下和服和三弦,改穿迷你薄紗,手抱電子吉他,再度登場做鋼管之秀。
博多景物不再依舊,人事未必全非?福岡其實和台北也沒有什麼兩樣。博多的夜船依然每夜十九時出航,兩小時繞行博多港灣一周。船名「瑪莉愛勒」,日本人也不知道什麼意思。船上有碧眼赤髯的船長和廚師,有法國料理和高級紅酒,有洋琴鬼演奏《風流寡婦》之類的西洋名歌名曲。兩小時之內,可以吃飯喝酒,可以舉辦婚禮或生日祝宴。可以遠眺博多灣的夕陽落日,可以觀魚賞鳥。唯不得喚紅襟翠袖,夜宿淫奔矣。年歲已長,每日浸在歐風美雨之生活中的邱教授,如果上了這樣的博多夜船,不知是否會有「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之嘆?
二、博多山笠
七月的福岡和台北一樣熱,邱坤良出巡博多,視察文教兼宣慰僑胞。他帶我去博多川端見一個圓臉圓鼻子,綁頭巾,持將軍扇的半身老頭之後,又到附近的承天寺去看了這個老頭的墳墓和紀念碑。不久後,讀到他寫的︿這個音二郎﹀,才知道那天所見的那個貌不驚人,長相滑稽的老頭,原來是日本現代劇的先驅,而且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戲劇家川上音二郎。
邱坤良洽公之餘,能在擁擠的人群之中,追看那些:「綁頭巾,穿日式法被,下著丁字褲」的男子漢「嘿咻嘿咻」地扛著山笠奔跑遊行。參與觀察地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博多祇園山笠祭。不久後,讀到他以磊落豪宕,亮麗活潑的文字寫成的︿以祭典之名﹀。
山笠上面坐著七、八人,擊掌吆喝,街道兩旁的觀眾在這支長龍快速經過時,或鼓掌讚聲,或潑水助陣。我混在擁擠的群眾中,感覺場面雖然熱鬧、喧譁,卻仍有一股儀式的靜謐與莊嚴,聞不到台灣大祭典常見的煙硝、米酒、檳榔加上汗臭的五味雜陳。整個慶典倒彷彿在向人間正式宣告夏季的到臨,活潑豔麗的民俗色彩正以聲勢浩大的氣勢,對炎夏所可能孳養的魑魅魍魎下達驅逐令。……
從博多回來一段時間了,但是山笠祭那種令人血液為之奔流的祭典畫面,仍深深鐫刻在我心裡,未曾褪色。目睹博多祇園山笠祭年輕人參與的盛況,我深刻體會到,日本的祭典能夠超越時代的更迭,像磁鐵一樣,緊緊吸住流動的人心,並凝聚成代代相傳的集體記憶,其原因就在於日本人成功地賦予老祭典新生命,對他們而言,祭典的意義在於參與,而不在徒具形式的行禮如儀。 ——〈以祭典之名〉
我把邱教授寫的幾篇和博多有關的文章,發給學生閱讀和討論。我的學生有博碩士和幾位什麼都不是的社會賢達。他們認真的查字典,加注音,頓然也能朗朗而誦邱教授之鴻文名著。
許多學生都知道那個川上音二郎,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高中的「社會」課的教科書上。也有學生知道風華絕世的一代名妓川上貞奴。至於伊藤博文、福澤諭吉等明治勛臣,路人皆知。教科書,電視劇,鈔票上,都會長相左右,經常見面。
有學生每年夏天跟著博多祇園山笠滿街跑,有學生從初中高中時代就在大人的指導下自製山笠,參加每年運動大會般的山笠祭,也有幾個每天吃豬肉而沒見過豬走路的學生,直到讀了邱教授的以祭典之名,對於身邊山笠祭的起源、流派、人形、儀式等等,才產生了「成程成程」(原來如此)的大悟。
一個在大學教中國語的學生,討論時默默,下課後卻跑來對我說: 「哭(邱)先生怎麼會知道那麼多連我們博多人都不知道的博多歷史? 哭先生的論文非常『面白』,比王老師教我們讀的那些論文有趣多了。」 邱先生寫博多的文章讓博多年輕人覺得有趣。同樣的,邱先生寫台灣人台灣事的文章,台灣人讀起來一定更有趣。
三、博多落日
每個人都應該放鬆心情,善待自己,也善待別人。讀書這件事未必那麼偉大、嚴肅,讀書人也不一定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的老K臉孔。把讀書視同遊戲,或把遊戲也當作讀書,必能以更寬闊的角度、輕鬆的心情面對人世間所有的事物。天底下的知識不只是學校所教的學科,學生學習的也不只老師所強調的考試重點。大塊假我以文章,每個人都應該學習以天地為師,以人人為師,為自己找到更多的學習樂趣與遊戲心情。 我成長的年代,教室像電影院,寺廟、教堂、山上、海邊、街頭、馬路也像教室,尤其暑假期間,到處都是我上課的地點。…… 知識、藝術能從生活經驗中得到啟發,遊戲也能成為學習的媒介或手段。學者、藝術家怕的是一成不變、了無新意,或者人云亦云,無病呻吟,每個人的生活安排、何嘗不然。人生苦短,如果循規蹈矩,千篇一律,五十年遍嘗生活的酸甜苦辣足矣,何必要享高壽? ——〈遊戲與讀書〉
邱坤良就是這樣一個把讀書視同遊戲,把遊戲當做讀書的人,是這樣的遊戲與讀書的高明結合,營造了他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的人生,踏實、豐富而且充滿智慧。 邱坤良所書寫的台灣人台灣事,把戰後許多人共同度過的那些單調乏味,索然無趣的生活與生命,變成一個藝術的,充滿了真實內在的有情有義的人文世界。當年南方澳的荒村冷巷,鄉俚瑣事,都如南方澳的青花,充滿了新鮮活潑的生機。和邱坤良相往來的那些鴻儒白丁,民間藝人,江湖好漢和跳舞男女,也都在他書中活靈活現,歷歷如在眼前。每個城鄉,每個人物,都是一頁台灣的「真情活歷史」。
讀書與遊戲,邱坤良兩者兼俱,唱做俱佳。他的遊戲,是一種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的遊心自適之遊。無掛無礙,自由自在,一如暮春三月,沂水河畔舞雩而歸的曾點。
邱坤良的文字一如其人,自然而不忸怩作態,自信而不自誇自矜。有如鹽在水中,讀者但知鹽味而不見有鹽。有的文章,詼諧跌蕩,促狹黠慧,幽默而不落俗。有的文章則是輕風淡雲,空靈活潑,如遙村秀樹,使人彌望而不能卻。
寥寥天地,才情本少。邱坤良的文學根柢與書寫能力都是一級水平,除了是吃多了南方澳的青花魚的原因之外,或許與他這種讀書遊戲,遊戲讀書的遊之藝術精神也有關係。 台灣宰相輪換,蘇冠張戴,已經鞠躬的邱大臣,正好可以踩著自己的腳步,瀟瀟灑灑過他美好的日子。 博多的浮雲落日,也是遊子故人之情,何日坤良再來,吃殺西米,喝地瓜酒? ——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日本福岡
?本文作者王孝廉先生,筆名王璇。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日本廣島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任日本福岡市西南學院大學教授。曾以《中國的神話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信仰》一書獲新聞局「重要學術著作獎」。王孝廉既寫散文又寫小說。他的散文主題大都圍繞在中國人與日本人長久的心理糾結上,以及一些回憶的篇章;他的小說或寫古典素材,或寫今事,感性強,也具思想深度;論述則以神話為主,即使從事文化研究,他也能夠「用深入淺出的可讀性文字解釋神話的特質」。著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花與花神》、《彼岸》、《船過水無痕》等書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