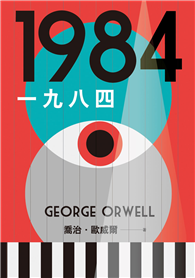時間之夢 游乾桂
當〈九歌〉出版社的素芳與靜婷找上門來,談及出書時,我開心極了。
他們可能無從想像,宜蘭老家的書櫃中藏了一長串,滿滿的,年代久遠的〈九歌〉的書,它是我大學時期,自許為文藝少年,省吃儉用加打工,積蓄下來的錢,長時間購買所得的,每一本書都有著時間印記,並且孕育了我的文學心靈。
是的,九歌該有一本屬於我的作品,他們努力促成這樣的機緣。
蔡文甫先生說:「每一位作家都該替孩子寫一本書」,我長期以來信仰的便是這樣的觀點,既然每一位作家都該與孩子一起填寫一個故事的夢,少年小說也許是個好的開始了。
用童話書與九歌結緣,事實上意義匪淺,至少看得見我的大夢。
我一直覺得自己算幸運之人,集合了心理學家、親職教育專家與作家於一身,因而看見了多面相的社會;我在醫院精神執業,專事心理治療,看見很多孩子的問題在於家長,但苦口婆心與偏執己深的父母說了哲理,有時往往等於沒說;我一身輕裝,四處演講,傳播優質的教育理念,但未必盡合人意,最後才赫然發現,最好的載體是童書,不動聲色的用一篇好故事,就可以
打動孩子的心,啟迪於無形之中。
這項發現讓我醉心於童話創作,我相信一個好故事勝過一位好講師了。
我的童話故事萌芽很早,大約在兒子三歲,女兒五歲時,為了使其好好入眠,自編的「晚安故事」便登場,少說二、三天,多者一星期,也得消化一個創意故事,長此以往,日積月累,大約也有成百近千了,故事多到自己數也數不清,忘的忘了,沒的沒了,有的根本埋入潛意識之中。
直到有一天,兒子喚醒了我的記憶,他說以前有很多好聽的故事,問我記得否,他說了幾個,替我的回憶開了一扇窗,我漸次從失憶的邊緣,把這些遺忘的故事一一增補回來,開始有了書寫的衝動。
一、二十個童話故事與少年小說的雛型,被我一一寫進電腦的檔案匣中,等待下一步的反芻消化,變成精彩的故事了。
《爺爺的神秘閣樓》便是這樣寫成的,它曾是我與兒女晚安故事的題材,本是隨意胡謅的,從木料到它會成為故事的肌理,我前前後後講了數次,二十多個回合,每一回孩子拍案叫絕,要我一講再講,我驚奇不已,原來一個小故事能吸引孩子們,猜想他們想一聽再聽,應該就是成功了。
兒子的一句話:「趕快寫出來」,讓我添了動能,把它化約成書。
我一直以為文字只是載體,但該載運什麼?我相信是道,如同韓愈所言的文以載道一般,如果文章什麼也不載運,我猜就只是一堆字了。
文字與文章有別,辭典中擺放的是字,不必我多寫,怎麼寫也不過《辭海》,但文章則不同,把一堆字巧妙的放在一起生出意義,引人反省,讓人動容,便大不相同了。
我的少兒小說,便典藏了這樣的味道。
這些年來,我一直關心環保,文明與創意等等議題,通過一支禿筆,把這些元素擺放進來,希望透過一篇好看的小說,讓孩子從中理得更多深沈的學問,並且反思人與土地,人與環境、文明、進步、科技的關係,有朝一日,成了宅心仁厚的關懷者。
我堅持一種信念,如果文章無法給人意義,那就不如不寫算了。
意義兩字在我看來一部分是關懷,在這一本書中,我透過一間閣樓,兩個小孩,一位老爺爺,一部時光機,穿梭百萬年來,尋找一種新的文明意義。
文明好嗎?
如果沒有細解,人人都說好,因為文明代表進步,但真實的情形真的如是嗎?
我們因為文明有了快速代步的車子,但有了車子之後,人就快速了嗎?
文明強調速度,但有了速度之後,人便忙碌,只是忙碌好嗎?
文明使人添了慾望,有了慾望之後,人便不擇手段,我們吃到了含有農藥的菜,具有劇毒鎘的米,以及鉛魚、病死雞……這樣的文明好嗎?
文明讓人的眼睛裡只有錢,但少了人情世故,利益眾生等等,沒有愛的社會好嗎?
文明人自比為神,可以操弄眾生,扭轉乾坤,科學成了自我傷害的利器,我從報章雜誌中得知,有一批科學家正在努力創造與人相同的機器人,這樣的文明想來可怕。
於是,我設計的一個百萬年前的文明,它比我們文明,但這個文明最後毀滅了,毀於太過文明,透過時光機,兩個文明交錯在一起,我們看見過去,想到了未來。
故事有巧意,有創意,更有深意,等著讀者用心意來解。
是的,我被友人稱做〈夢人〉。
我喜歡這樣的稱呼,我解成有夢的人,做夢的人,或者圓夢的人。
希望讀了它的人,也與我一樣,懷抱慈悲織個夢。
游乾桂寫於雪荷童話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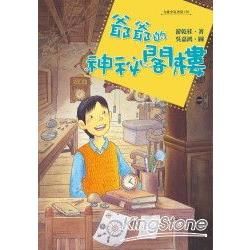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