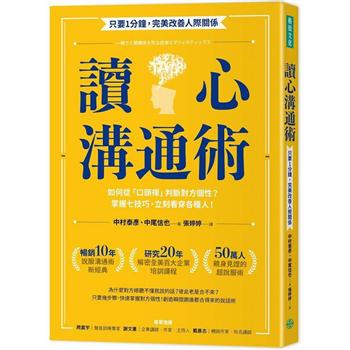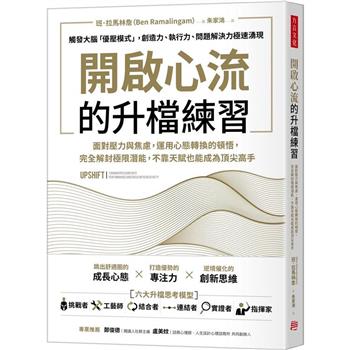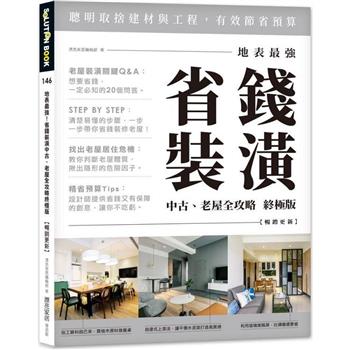評論30家 鄭明娳 (一九四九──) 鄭明娳,出生於新竹。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博士。曾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獎、中興文藝獎章、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等。 鄭明娳最早研究古典小說,對《西遊記》等經典著有專論;轉而考察現代散文的發展,在幾乎沒有人從事散文研究的當時,她埋首撰寫《現代散文構成論》四書,開啟台灣散文研究的里程碑,受到文壇及學界的肯定。她致力現代散文系統理論的建構,也研究新詩、報導文學。 本文探討當代散文的兩種「怪誕」,研究的是風格,也是一種體裁。
她先就天地宇宙及古今文獻探討「怪誕」的形成,再分從現實與虛構兩方面探討怪誕情境,上下古今舉例,重點放在五四以降,「怪誕化的散文空間重新塑造了散文作家面對時代變局的思考形態」,值得進一步挖掘討論。
當代散文的兩種「怪誕」(刪節) 壹、前言 一般認為現代散文雖然經過長期發展,但是不如小說、詩歌、戲劇一般,出現許多運動風潮以及繁多的藝術流派,同時在創意的層面上也沒有非常明顯的突破。 抱持以上這種看法的人,通常是未深入理解二十世紀華文文學中散文的豐富面貌,或者僅僅將注意力集中在抒情小品上。其實,現代散文所以造成藝術面欠缺發展、作者們在內涵與技巧雙方面趑趄不前的一般印象,最主要原因,還是在對散文性質的模糊認知,總以為散文必須出自創作者生活的主觀心靈,必須以切身的情思見聞作為素材的唯一來源,甚或在散文的內容中意圖搜捕創作者個人的傳記資料,強求散文家以「記實」的任務。
其他文類都具備虛構的特質,何獨散文不然?如果散文的敘述者必須和散文的書寫者疊合為一,自然就會限制創作的發展。自五四以降,一方面有不少散文家採取小說式的敘述,例如魯迅的《朝花夕拾》既可以當作憶舊的散文來讀,又何嘗不能視為自傳式的小說?即使是自己的親身體驗,然而透過剪裁、重組的記憶,就自然產生虛構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散文家採取了隱藏自我的視角,文本中雖然有「我」存在,「我」卻不是情節中的核心角色,只不過居於說書者的地位進行客觀的描述,像許地山等人的不少小品,都將「我」的角色退縮至不涉入事件的旁觀者視角,有時則以趨近小說的客觀敘述。
散文可以說是以現實生活感思為基礎,以切身體驗或閱歷所得為素材,重新組織而成的「創作」,並且可以揉融詩、小說、戲劇等寫作技巧的一種獨特文類,其中既可以出自生活復回歸生活,也可以自生活出發,抵達幻想與虛構的時空,更能純粹進行理念上的論辯,單就觀念本身迴旋收放。因此,以獨特的藝術觀念或美學原則匯入散文的創作內涵,發掘日常生活所隱藏的各種隱喻及內在的物象,應該是促使散文內容深化的重要途徑。
本文所探索的怪誕課題,就具備了虛構與想像的特質,非但違反我們一般對於散文日常性的認識,作者甚至以刻意違反自然,意圖顯示獨特的美學態度。 超現實主義詩歌、荒謬劇和新小說、黑色幽默小說等等潮流在二十世紀曾經喧騰一時,都包含怪誕因素在內。這種怪誕色彩(或風格)絕非單純的噱頭,時常是因為創作的意識形態衍生而成,而西方諸種現代主義與都市文化的密切關係殆無疑義。雖然怪誕風格不見得與都市題材結合,但在都市世界中成為日常的怪誕意象卻廣為當代文學作家採擷為創作內容,進而產生了自素材以迄結構上的特殊風味。怪誕風格也不限於都市一隅,我們可以回頭檢索文學和美學史中的痕跡。
在西方美學思想的發展史中,怪誕(grottesco; grotesque)一詞自繪畫與裝飾風格而來,十六、七世紀左右開始被挪用到文學風格的描述上,原意包括罕見的、異想的、恣肆的、反覆無常的事物、動作等等,後來逐漸演變為幽默、荒謬和恐懼的綜合觀念。
怪誕是一種和崇高恰巧相反的美學概念。崇高的概念,就文學藝術上的表現而言,是對自然美的終極狀態進行模擬(或者對這種不可能被任何符號所描繪的客體進行超越)。怪誕則是另一個極端,怪誕是違逆自然法則以及人類常識的,怪誕作品是特徵藝術的典型,以比例失調或不可能的組合構成的內容。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筆記體散文作品《幻想生物手冊》(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中,那些傳說中的動物即是怪誕的典型,在一百一十七則奇異的怪誕動物辭目中,包括全世界各地各時期的奇特傳說,其中包括了〈帶鍊條的豬與阿根廷其他動物誌〉、〈美國動物誌〉、〈智利動物誌〉、〈中國動物誌〉等,表示除了古代近東和素有怪誕傳說的歐洲之外,近代國家如美洲國家,遠東古邦如中國,都有怪誕動物的傳說可以編入索引。這些怪誕動物有許多擷取自文學作品,表示怪誕文學在全世界都曾經發生,當然也擁有各自的文化傳統印記。
要說明怪誕的特色,可以舉波赫士在前書中的任何一段描寫,例如〈獅頭蟻身怪物牟米可萊安〉牟米可萊安的前半身是獅子,後半身是螞蟻,牠的前代父系是肉食者,母系則是以穀類為主食的昆蟲,既然牠們是兩者的後代,必然也承受了兩者的天性,因而牠們不能吃肉,因為牠們的母系不吃肉,牠們也不能吃穀類,因為牠們的父系不吃穀類。因此牠們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
以上這則由波赫士轉述的傳說故事提供了一隻不可能的動物,獅頭蟻身的結合非但在生物學上不可能,在美學上也令人產生極不協調的怪異感受;而牟米可萊安不可能進食更是一件荒謬的事,那麼,牠豈不是一生下來就處於飢餓的死亡狀態嗎?牠的生命於是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存在,或者說唯一的意義是在嘲弄生命的價值。牟米可萊安的故事本身就令人產生一種不安感,雖然敘述故事的人以滑稽的邏輯說明了牠的詭異存在以及死亡的理由,但其中「似是而非」的論調卻像指甲搔刮黑板般,讓我們渾身戰慄。 另一個例子是波赫士從《太平廣記》中抄錄下來的種種異獸,如「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見則天下大旱」,又如「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曰軍,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這使我們聯想到「怪誕」在中國文學傳統裡──特別是筆記中的「筆記小說」,其性質多半更接近現代的札記體散文或雜文而非小說創作──其實占有重要比例,從《山海經》、《搜神記》到《太平廣記》,具備怪誕特質的民間傳統以記實的態度被保存下來。 先民們在文學或藝術中保存的怪誕風格,和宗教文化有密切關係,包含著特定的神祕主義色彩。到了當代,怪誕風格的重新融鑄,和過去的傳統有本質上的差異,通常是為了表達特殊的情況,呈現個別的創作思想,或者是為了追求復古的趣味,返身於文化傳統中不可理解的神祕性以尋求素材。
反過來看,文化傳統中的怪誕素材往往因為它們的內涵在文藝歷史中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套固定的解釋,而不再成為惡兆和奇特的事物。我們在《山海經》中看到的魚獸合體(如鮨魚)、魚人合體(氐人國)以及異類綜合型魚類(如修辟魚),至今仍然有股詭異與巫魘的神祕氣息,這是因為牠們沒有在文化史中成長為特定意義的符徵。而雷峰塔下的白蛇,卻自早期的殺人妖孽發展為女性真情的千古典範,儘管牠仍然是一條蛇精,卻是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不再是怪誕的產物,而是浪漫主義化的象徵。
沃爾夫岡•凱澤爾在《美人和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中曾經指出,怪誕只能在接受的過程中體會,但是人們仍有可能將某些結構上缺乏怪誕要素的事物說成「是怪誕的」,文化差異是造成這種混淆的主要原因。凱澤爾舉出印加文化為例,認為不了解印加文化的人會認為印加人的雕塑是怪誕的,不過對於古代印加人而言,那些被現代歐洲人視為惡魔般的雕塑,儘管展示了我們感受的「恐怖、痛苦和不可理解的驚懼」,在他們心目中卻是平凡而簡單的參照架構。
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並且理解某種事物的內容,不論它的形態如何猙獰可怕,也不會視之為怪誕;經過考古學家和博物學家近兩個世紀的研究與發掘,埋藏在地層中的「怪物骨頭」(曾被誤認為神話中的巨人骨骸)現在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恐龍,沒有人再說明那些化石是怪誕的,它們早就成為一種眾所熟知的地質史紀錄。所以,被視為怪誕的事物往往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下具備陌生與不可理解的特質。
中國繪畫和民俗版畫中時常出現的蝙蝠是一個反證。蝙蝠本身的生活特性(晝伏夜出、倒掛睡眠)以及牠們展示的「不自然」生理結構(在外形上兼含鳥與獸類的特徵),可說是怪誕動物的典型。在中國民間藝術的運用裡,因為「蝠」的字音和「福」相同,藉由這種諧音而產生的意義轉換,蝙蝠成為繪畫和建築雕飾中象徵「幸福」、「福氣」的吉祥符號;換言之,在中國人的民俗世界裡,「蝠」、「福」二字的符徵,因為發音相同,而形成了符旨的代換,於是抽象的「福」字乃能寄託在蝙蝠的形象上,使得蝙蝠圖案成為「福」的「代言者」,它不再是原本陰森而恐怖的怪誕動物,而被繪飾在年畫或者棟梁間,這卻是西方人很難接受的。到了二十世紀,在好萊塢的B級片中,蝙蝠總是和深幽而布滿危機的洞穴,甚至吸血鬼聯結在一起,當主要角色被一群自黑闇中撲來的蝙蝠驚嚇時,不僅是導演所提供的一場虛驚,怪誕的蝙蝠也是即將來臨的危機之前奏。
因此,即令在文學領域中也不例外。怪誕有其特定的結構,這種特定結構的概念在各文化領域中有其普遍性,但是對於那些內容屬於怪誕的結構卻存在著文化差異;波赫士筆下的麒麟對於波赫士本身及其讀者(西班牙文及英文讀者)而言必定十分怪誕荒謬,但是麒麟在中國的文化傳說中卻是祥瑞的仁獸。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評論30家(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華文文學研究 |
$ 405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評論30家(上冊)
賞讀詩、散文、小說等創作文本,是和文學心靈的親近對話,閱讀文學批評的論述文本,則是和先前的對話進行對話。
在這30篇精彩的評論中,從呂赫若到洪醒夫,從張愛玲、平路到朱天文,從詩壇前行代的方思到中生代的簡政珍、白靈等,評論家的筆調帶領我們深入文學作品,感受文學的內在世界。
上冊入選菁英評論家:柯慶明、陳芳明、蕭 蕭、彭瑞金、陳萬益、呂正惠、鄭明娳、何寄澎、林瑞明、應鳳凰、李瑞騰、彭小妍、廖炳惠、王德威、廖咸浩
作者簡介:
阿盛,本名楊敏盛,一九五○年生,台灣新營人,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記者、編輯、主編、主任等職,現任「碩人出版社」發行人,並主持「文學小鎮--寫作私淑班」。文學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志業,生活態度是「半醉觀浮世,將就過日子」,喜歡看人看書看山川。對尋常人常青眼相向,人生理念則是「唯誠唯善大是好,有生有活遍地花」。著有散文《五花十色相》、《唱起唐山謠》、《民權路回頭》等近二十冊,小說《秀才樓五更鼓》等,作品多篇收入高中及大學國文選教材。
章節試閱
評論30家 鄭明娳 (一九四九──) 鄭明娳,出生於新竹。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博士。曾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獎、中興文藝獎章、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等。 鄭明娳最早研究古典小說,對《西遊記》等經典著有專論;轉而考察現代散文的發展,在幾乎沒有人從事散文研究的當時,她埋首撰寫《現代散文構成論》四書,開啟台灣散文研究的里程碑,受到文壇及學界的肯定。她致力現代散文系統理論的建構,也研究新詩、報導文學。 本文探討當代散文的兩種「怪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瑞勝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10 ISBN/ISSN:9789574444977
-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36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