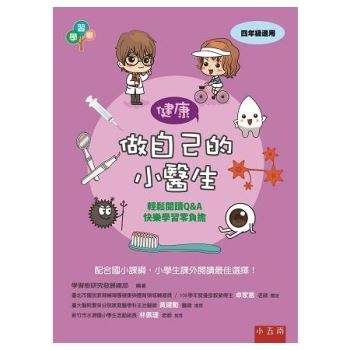剛從偏遠的宜蘭北上就讀大學,人生地不熟,有點劉姥姥進大觀園的困窘,系上知曉難處,替這些離鄉背景的鄉下孩子,選了一位學長當天使守護,讓我們得到最好的照料,天使一詞的印象由此印烙在心,我明白它是上帝的使者、守護的神、庇護者。
補習班,字面的意義是補充學習,指的是在某項才華上有所欠缺者的補救教育,印象中只補英數理化,少有其他,就因如此,我竟突兀的想及,可不可以補補道德。
在演講結束,一位小學老師與我談心,話語中語重心長,他指陳現在的教育,什麼都不缺,就缺德,意指德行真的有所欠缺,該來補補習。
於是我奇異的聯想,可否開一家天使補習班呢?讓更多人因而成為天使,書名就此確立為《天使補習班》了。
善念一直是我用心思索的主題,因為它揉合極多的元素,包括了慈悲喜捨、同理心、關懷、愛與宅心仁厚等等,當人都具備了這些人格,社會一定溫良恭儉讓,不會處處機鋒,不必小心提防。
善是一個人的中心線,醫生如果少了善念,就非好醫生,沒有醫德,眼中只有錢,則是惡醫生,用醫術殺了人,則是殺人狂魔了;科學亦復如是,以人為本者是科學家,帶著仇恨者,則是恐怖分子;食品營養學家也是如此,宅心仁厚者,會慎重研究每一種由口而入的食物,無德者,只想及眼前的利益。
設身處地是善的另一面,這樣的人才會懂得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明白父母親老邁,可能面臨的問題,需要的幫助,必須的關心,否則老無所終就是悲劇了。
日本有一本小說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作家深澤七郎的作品──《楢山節考》,描述古代日本鄉下人民生活窮苦,男人為了生存,每天辛苦工作,女孩一出生就賣給富人換錢貼補家用,只求一餐溫飽。
鄉下有個不成文規定: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紀,要由兒子背到山中等死。因為沒有多餘糧食可以負擔養育,老人下場悲慘,最後葬身山谷。
故事中的老人家阿鈴婆婆,在她七十歲的人生旅程中,從未抗拒過時代和社會加諸身上的律法與箝制,導演最後依然讓她上了楢山,認命地順從族群的安排,自生自滅終老。
這座古老的楢山,老人的墳場,早已不在了,但我卻擔心著,如果不教善念,一座新的楢山可能正在誕生中。
可惜,我們的教育仍舊只教考試、分數,把這個社會構成的最美的東西遺漏了,但是社會不善,我們如何住得安心,活得愜意呢?
知識分子常自比為習聖賢書者,可是卻常一知半解,就以孔子的儒家為例,他早在《論語.學而篇》中就清楚載明了一件事: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老夫子言明一事──做人第一,學問第二,他指陳教育最重要的責任是教做人,而今有嗎?
做人的重要不言可喻,我把它偷偷的移植進了這本書中,給友人試讀,令人驚奇的是他們全喜歡,這當包括「九歌」的編輯群,於是催促著我寫成一本書,請了很好的繪者曉勤成為繪製的夥伴,還很寬容的給了我一年的時間,讓完成的稿子沉澱,發酵出甘醇的味道,我在去年清明交出初稿,九歌總編輯素芳利用假期閱讀初稿,並且迫不及待告訴我心中的激盪,她的美言對我來說,是鼓勵,也是鞭策,更代表這一類文體的書寫是感人肺腑的。
這本書在我的百本作品之中算特別,我自己由衷喜歡,希望讀的人全喜歡,讓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運動。
我私下與編輯談到想辦一個「天使節」,讓每個當過天使的人說出快意,社會有太多獎項了,但沒有人想到替天使頒個獎,我也想做一件事,如果這本書能引動共鳴,辦個「天使寫作賽」理應不錯,讓人寫出當天使的心得。
以上純屬狂想。
我對善念的聯想並非憑空而來的,它有些出處。
保險這一行,我自陳有些偏見,心中一直不懷好意,把它視若騙術,敬而遠之,但自從遇見高許定先生之後,有了改觀,讓保險回歸原來的位置。
這個人很特別。
但特別在哪裡?三言兩語說不上來,大約是善念吧。
第一次與之見面是在南山人壽邀約我的講座中,一如往常,演講、售書、簽名、拍照、散會,他來與我閒聊,並且買下當天所有未售出去的書籍,至於做何用途我便不知了。
我驚訝莫名,但未過問,與他一起搬書上車,結束一天的忙碌。
對我來說,這樣的舉措不算少見,也就沒有深思了。
之後,我們有了來往,他偶爾帶了朋友到家造訪,又是買了一堆書,或請我赴學校演講,再買一些書,我終於忍不住問他:「幹嘛用的?」其實不用分說我都明白是送人的,但送誰呢?有的是他的客戶,有些是他的友朋,有些是學校的老師家長,他把賺來的錢一部分用在佈施一事上,算是慈善事業。
有一回,他付了錢請我去溫泉會館做一場講座,溫泉會館?是的,如假包換,我開講,吃自助午餐,會後還有健康檢查,招待的對象就是他的客戶了,每一個人都想賺錢,但這個人卻把賺來的銀子花掉。
那一次,我經由他多認識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加拿大籍的餿水先生劉力學老師,隔沒多久,高許定打來電話,一夥人登門拜訪劉老師三芝的有機農園,這一次,劉力學讓我添了許多反思,他告訴我,自己最明白房子的需要,理應自己蓋,而他真的是實踐者,房子由自己監造施工,有火力發電,也有風力發電。
有機蔬菜最是令人難忘,不知是否玩笑話,他說種好菜賣給最需要的人,重病的人先賣,有病的人次賣,沒病的人不賣。
我聽到這個「外」人的教育哲學觀與環境保育觀,令人動容不已,我發現愛台灣一詞,該由他代言,他可以為了沙灘的潔淨,與開著沙灘吉普車的橫行者對峙,家人替他捏把冷汗,他卻以為理所當然。
高許定的大夢,一直盤旋於心,有錢的話,他想從事青少年犯罪防治的工作,問我可以幫忙嗎?我明白這項工程要錢要力要土地,不知是否可成,如果能夠,我許他一個承諾,一定傾力幫忙了。
高許定說他從我身上學了許多,只是他不知,我從他身上學了更多。
思妤是另一位提點我善念的人,我們的結識還是在演講之中,從買我的書開始的。我答應《講義》雜誌做一件事,在演講中介紹它,如果因而有了訂單,便回撥一些錢進我的戶頭,成立「慈悲基金」,這項美意後來被我搞壞了,我根本不知如何「插播」這件事,總在演講時說得吞吞吐吐,很不踏實,便不了了之了,她是第一個響應者,應該也是最後一位了。
之後,她大量採購了我的書,並以一套大約三千元的數量,長時間訂書,寄給偏遠地區的學校、女子監獄、她的親友等等,我已經數不清數量多少了。
嚴長壽的嫂子是我的讀者之一,同樣在一次機緣下,買了我的第一批書送人,之後陸陸續續買了很多回,我把她視為大姊,新書出版便寄上一本,沒有料到,她竟因而再度採購一批,我明白她有買書贈人的習慣,而且不止買我一個人的書,只要她以為對社會有益的書,便出手闊綽了。
小石,是我服務於精神病院時期的友人,他像天使一樣,教我更多善念。
他的小錢常有大用,有一回,我開著車載他去北市郊區的一棟公寓,他問我可以等他一會兒嗎?
他快速下車,沒多久便出來了,滿臉歡喜。
原來他帶了救急的錢送人,公寓中住的是兩位年邁、無女無兒的老人家,靠著老人救濟金過活,以前做點小生意,還能自足自給,而今老了,貧病交加,無人可奉養,只好伸手向我的友人借了。
借?
是的,但不可能還的,可能也還不起了,他在兩老身上至少花了三、四十萬元,而他一個月的薪水也才五、六萬元,並非富者,家庭也有自己的負擔,卻又助人,保持歡喜,無怨無悔,真是不易。
我常在想,什麼樣的動能,使之與眾不同,人家是守財奴,而這些人卻都是布施者,他們都說,錢是取來用的,至於誰用都無所謂,原來如此,才能如此雲淡風輕,這件事讓我理得了一個觀念,善是可以教得來的。
身教最好,如果不成,那就言教吧,再不成,就用好書來教,這大約就是我書寫這一本書最初的意圖了。
出版社約稿,鎖定我的親職教育的書,因為好賣,但是九歌出版社獨具慧眼,發現我更適合寫散文、短篇小說,覺得我的文章中,藏著常民文化裡的真、善、美,值得與人分享。
熟悉的作家一度懷疑過我的門派,偷偷考據,說我有太極的陰柔,少林的內斂,武當的剛強,以為是旁門左道,有些老頑童周伯通的「亂流」,其實我的文體有其師承,某種程度受了大陸老派作家汪曾祺、楊絳,以及魯迅等人的影響,不寫文字,只寫文章,把它當成情感的載體,在平凡的文字中抒發真性,讓人讀了動容。
早期我閱讀汪老的作品《受戒》,便被這種說故事風格的寫法所吸引,像極了我在老榕樹下聽耆老說故事的場景,韻味十足。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那就難怪了。
楊絳的文體也很特別,看似平凡卻不平凡,一個特別的寫家,魅力獨特的引著讀者往一個有意思的方向前進,我閱讀她的《幹校六記》、《我們仨》、《洗澡》等書,與最近的一本《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直覺受益良多。
我用感性與理性兼備的筆觸,書寫我心中自以為是的美好事務──善,它一直是我信以為真的,聯結人與人之間最美的紅絲線,把原本情感薄弱的社會結盟起來,讓人懂得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這也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核心價值。
如果這本書有些價值的話,我猜是一粒等待萌芽的種子吧!我想種在每個人的心靈沃土之中。
如果這本書喜歡的讀者很多,錢賺得夠多,我還想再做一件事:買一塊地,蓋一間「人文書院」,傳遞善念與美好生活的夢想。
游乾桂 寫於閒閒居
一個人的傻笑
書寫的盡頭,將會是什麼? 這兩年減慢寫作速度,運動較多寫得較少,生活也有改變,year來臺中讀書,整理東海宿舍,準備過山野生活,山野之人要與蛇蠍搏鬥,必須有好膽量,在我眼前是新生活也是舊生活,彷彿回到外祖父的故居探險,回到生命之初始。 我在玩著嚴肅的遊戲。
遊戲是不能嚴肅的,只因不懂遊戲規則,遊戲的人總是帶點孩子氣,雖禁不起嚴肅卻也婉拒兒戲。
一系列的空間書與孤獨書長達七八年,建立流離宮殿與城市,寫到迷失在無空間無感覺中,再走過去無路矣,文字與想像俱耗盡,於是用蒙恬之筆點了一下超連結,進入異空間。 二○○七年六月在中時部落格架設網站,剛開始貼一些已發表過的舊文,反應稀稀落落,之後出國旅行,中斷蠻長的一段時間,回國後開始有人點菜,剛開始只是寫些旅遊與購物雜感之類,有人對張愛玲與個人隱私很有興趣,我先以太極拳應對,後來有人再三挑釁,那時正是《色戒》電影反應熱烈之際,涉及女作家如何看與被看的問題,我因不堪被激,端出十數道大菜,每道大菜都引起熱烈討論,有多至三百多則者,也有因事涉他人,幾度自己拆版,而成絕響者,戰線長達兩個月,留言多達兩千多。規模最大的一次論爭,雙方人馬爭論不休,逼得我出面叫停,因此認識可愛的網友如賓、羅傑、蘇非、布卡、這位太太、dash......,發現他們的面目鮮明,見多識廣,且宅化驚人,如此我也邁入宅世。
宅有層次之高低,依其中一位朋友之妙解,宅分為秋葉原系、奇技淫巧派、鴛鴦蝴蝶派,又稱sissy宅、泰宅治......,對於初入網海的我真是大開眼界。 「宅」是一種新的價值與美學,他們是新安那其主義混搭布爾喬亞風,以虛擬空間為神龕,支持左派又愛消費,講究人各有所好的「i」世代。「i」是網路代稱,卻也是去大寫之「我」,既不放棄追求自我,卻也懂得將自我小寫的重要,網路世界抵抗大寫,所以各處不同的「我」,才能真正在那裡相遇。他們也是視覺主義者,我在其中浮沉,漸漸發現,作家與讀者的分界已然失去,有些文章是被促成,也隨興寫成,直接而快速,它只是一個劇目大綱,就像江湖走唱,臺下的戲比臺上精彩,我珍惜這樣的經驗,與這些美好的互動,其中的奧妙精彩,是文字難以顯現的。
網上一日,人間十年,從九月的筆戰到十月,幾個戰友已成無話不談的朋友,有時對談從早連綿到晚,有時眾聲喧嘩,有時兩人短兵交接,就連夜半一人獨白也成,姑且稱之為田野的一種,他們作我,我作他們,我走入他們,他們也走入我。
如果沒有他們,有部份文章不會出現吧,我把它濃縮為〈沉靜的歌〉,正如某位網友所說: 講到田野,網上的交會也是一種田野吧,不同的主體在虛擬的空間上交會,偶爾也會創造出具有在地精神的所在。老師在採訪著我們,我們也在採訪著老師,這是互動加參與觀察法,於我而言更是反涉法,老師被我們的各式各樣所吸引,就好像我從老師那邊感受到的溫暖與柔軟一樣的感到驚訝。
儘管我的生命處境已經不太相同,無法接受一些觀念的感召,不過我或許還是希望坎伯那句被引到爛的話成立,至少對我們所關心的人有效: 「如果你追尋著你的福份,你便踏上了自己命運的旅程,等待著你,而你應該過的生活就是你在過的生活。當你看到了這點,你在被祝福的田野上遇見不同的人們,而他們將會為你開啟另一道大門。我說,順著自己的福份走別害怕,不管你要去哪裡,未知之門都將隨時為你敞開。」 當然對我這種犬儒的人來講,這個田野可能是個災難,其實門外可能是場風暴。或者更慘的是──根本什麼都沒有──一個存在主義的惡夢。 不過現在看起來好像門已半開著了,或許是該走走吧。
大宅門已打開,不走進也難,而且我也走了一半,也許裡面什麼都沒有,但它已改變我的文字,較直接而爽利,富於黏著性,關心的問題也有點宅:時尚與電影、空間與美食、youtube、友誼……,當一切的感情都化約成友誼,愛不再那麼絕對,連金石也化開。只剩下一個人的傻笑。 原來連嚴肅也可以化掉,這本書中還是有一些化不開的瘀血,就讓它自然呈現,新的文體也許尚未成形,但這本書會是重要的轉折。 記得二十幾年前第一次批紫微斗數,內容不記得了,只記得相士說「鈴星坐命,小人包圍,災禍之來如迅雷不及掩耳」,半輩子過去了,回想起來,有點道理,我得的現世報不算少,然而我是自己的「鈴星」,因愛追求變化與怪異之美而命運怪異,而我應該過的生活就是我在過的生活,這就是我的福份,怪不得別人,只要離遠一點欣賞,鈴星還蠻美,因為它夠怪。 所有事物離遠一點欣賞,都是美的,這一點我敢肯定;不然就比個吻再近些,讓雙眼只好閉上。
也許紫微斗數沒批到的是,當鈴星進入天涯咫尺的網路田野,那些福份跟災禍,是否也如笑聲在大風中迴盪;這麼近,那麼遠?
周芬伶二○○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