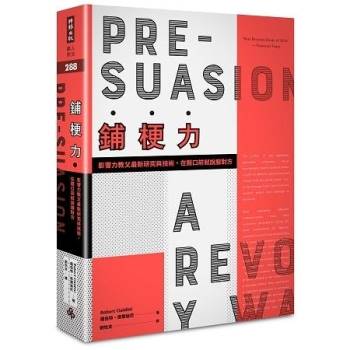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日不落家》這本散文集余光中第四本純抒情散文集。〈日不落家〉一文是本集的書名所體,與作者的〈我的四個假想敵〉前後呼應,成了他寫四個女兒成長的「姊妹篇」。〈日不落家〉儘管沒有詼諧自嘲、戲謔笑傲,卻感慨更深、滄桑更長。不但對四個女兒更加疼惜,還加上對妻子善盡慈母之職的讚嘆,因此在人倫的格局上當更為恢弘。本書特增余光中四個旅居各地的女兒所寫文章,以呼應家是「日不落家」。
本書特色
★本書是余光中的純散文集,有短到幾百字的俏皮小品〈三都賦〉,也有長逾萬言的汪洋巨篇〈橋跨黃金城〉。南非、西班牙、巴西的幾篇遊記,都敘事生動,見解高超。他如〈開你的大頭會〉之惹笑,〈日不落家〉之深情,都有可觀。
★特收錄余光中四個女兒第一次所寫回父親文章。人人常稱英國為「日不落國」,但在余光中心中,旅居各地的女兒,卻是讓他有「日不落家」之感。
作者簡介
余光中
自一九四九年開始發表文章,詩風與文風的多變、多產、多樣,盱衡同輩晚輩,幾乎少有匹敵者。一生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寫作的四度空間。對現代文學影響既深且遠,遍及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曾在美國教書四年,並在台、港各大學擔任外文系或中文系教授暨文學院院長,退休後受聘為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著有詩集《蓮的聯想》、《白玉苦瓜》等;散文《逍遙遊》、《聽聽那冷雨》等;評論集《藍墨水的下游》、《舉杯向天笑》等;翻譯《梵谷傳》等,合計七十種以上。


 2010/10/16
20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