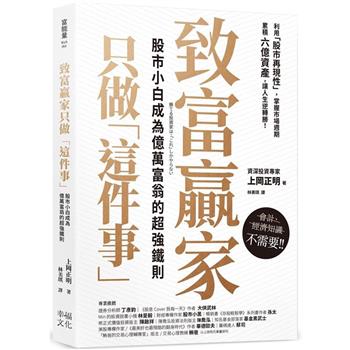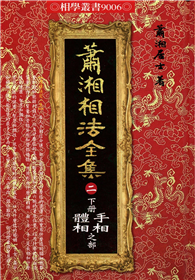文章「人間」事,得失讀友知
──寫在《沒有觀眾的舞台》再排新版之前
在五○年代,個人雖在各報刊發表若干篇小說,但在台灣出版界仍算新人。繼香港「東方文學社」的《解凍的時候》、馬來西亞曙光公司的《女生宿舍》出版後,才有這本《沒有觀眾的舞台》誕生。
當時蕭孟能先生主持「文星」書店,大手筆出版「文星叢刊」,第一批作者有梁實秋、蔣勻田、黎東方、余光中、李敖、陳紹鵬、林海音、聶華苓、於梨華、沉櫻等十位,碩彥群集,極一時之盛。因此,各界均爭相投稿;而每月均出版十本新書,打破當時零星出版新書的慣例。本書是排在五十四年七月第十七批(文星叢刊一六○到一六九號),作者依次為魏惟儀、朱夜、蔡文甫、周夢蝶、魯稚子、黃朝湖、徐蔭祥、余光中、何秀煌、劉鳳翰等十位(「文星叢刊」新書十種預約廣告見本文後之次頁)。
如此不厭其煩的敘述這段出版淵源,在說明「文星」當時獨領風騷之一斑,而時光不再,名家凋零星散,本批作品中僅有余光中、周夢蝶二位仍揮毫不輟,光芒萬丈,其餘大多音訊已杳。近報載周夢蝶在本批出版之《還魂草》,網路以高價一萬七千三百元標售成交,蔚為奇蹟。
書中部分作品在《現代文學》月刊發表,因該刊是由台大外文系出身的白先勇、王文興等小說家主編,刊用之稿件,和傳統的說故事方式不同,注重心理刻劃,採用意識流技巧,壓縮時間與空間,展現另一種真實人生,其作品被目為「現代派」。但時代遞嬗,流派早已混淆、湮沒,多年前作品現仍保存供讀友閱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楚茹在〈追求現代文學的成果〉(見二一五頁)一文中,提到他最喜歡的是那篇〈飢渴〉,認為是現代文學中「可貴的收穫」。〈飢渴〉一文發表後,有人懷疑模仿法蘭茲.卡夫卡(Frang Kafka)的〈變形記〉,但此文創作的源頭,是來自一場夢境。在睡夢中矇矓看到多年前的小學同學。他課餘愛把別人對他說的個人私密到處傳播,所以心中隱藏著極端不滿,在看到他變成硬殼蟲時便憤怒地踩他一腳。和〈變形記〉中類似童話式的人物蛻變不同;而且在發表〈飢渴〉多年後,才看到〈變形記〉的譯文,這種事後「巧合」,正好藉再排新版的機會說明。
特別要介紹研究西洋現代文學的楚茹,他在九歌譯安?波特(Anne Porter)的五十萬字長篇小說《愚人船》,出版後頗受好評,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已到達一半,但因大陸同時多人搶譯出版,他便放棄翻譯這部世界名著的工作。
因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為文推薦的還有另一位小說作家楚卿。不知是巧合,還是「文星」故意安排,在本書面世之前的一個月,文星叢刊第十六批推出《楚卿小說選》,惜他已於八十三年辭世,享壽七十有一。
藉此由重排新版之際,特追憶往事與文緣、人緣,和新舊讀友互勉。
蔡文甫 九十八年五月 於台北市
推薦序一
追求現代文學的成果
楚 茹
在自由中國,我們似乎沒「現代」的自由;凡是被稱為「現代」的,無一不受到嚴酷的非難──現代詩、現代畫、現代小說;甚至現代電影,全都成為眾矢之的。本來,在新舊交替的夾縫裡,這種現象原是無可避免的,但由於過分的偏執,老一輩的人,不肯讓年輕的一代自由去發展他們的心智,而年輕的一代,也往往抹殺了上一輩的既有成就,於是壁壘分明,聚訟不息,因現代詩和現代畫而引起的不斷的爭論,就是一個著例。但是,現代小說的作家們似乎不屑於這樣做,他們只是默默耕耘,以他們的豐碩成果,來證明他們的「現代」的確是豐富而且輝煌的。
談到小說,也許你喜歡有情節、有結構、故事熱鬧的吧!可是你得知道,看慣了《唐人傳奇》或《宋人話本》的老一輩的人,也曾對搞五四新文學運動那些憑空起筆的新小說大搖其頭。搖頭沒關係。現在我們對那種受過時代精神洗禮的新小說早已習慣,並且有了偏愛,偏愛得又反對別人來攪亂它的形式和筆法。但反對也是徒然。藝術原本就是創造、創造、創造!藝術沒創造就是死亡。
現代小說並不難懂。因為創造並不是憑空捏造。它只是將小說中的要件,以反傳統的輕重尺度來取捨,給與新的安排,並採用意識流的技巧,壓縮時間與空間,進而擴展新的時空。在語言文字方面的選擇與安排,也擺脫了習用的規律,嘗試獨創的蹊徑,使它們不只是表情達意、寫景敘事的工具,而使它本身便含有豐富的意義和聯想。它的目的,在表現赤裸裸的真實,使人對自身、對世界的真面目看得更清楚些;而不像以前那樣皮相的描繪人物,和要人物去鑽故事的框框,以及用故事來吊讀者的胃口。所以這種反傳統結構的,不重結構的結構,對於不常接觸的人,確是有點不受用。
但這種不受用的原因,除了接觸不多,基於習慣上的惰性,另外就是對於近代文藝思潮的演變,根本沒有人居高臨下的寫過系統性的介紹文章;零零碎碎有一些新理論譯介過來,也未曾引起普遍的注意。作品方面,由於銷路不佳,以致在現代文學上產生過很大影響或高度成就的作家,如喬伊斯、吳爾芙、湯瑪士?曼、卡夫卡、普魯思特、詹姆斯、康拉德、福克納、沙特等人的小說很少有人敢動筆去譯,即使譯了也很少有人敢印(編按:喬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已由九歌請金隄先生譯成平裝、精裝各二鉅冊,轟動海峽兩岸,張秀亞譯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由九歌事業群的天培文化出版)。但時代精神和文藝思潮的影響原是世界性的,我們當年的新文學運動,本來就是在這種影響之下應運而生的。今天,我們豈可守著當年的一點成果,而不思進步?
所以要求了解現代小說,主要是靠我們通力合作來消除造成隔閡的原因,而不可嗤之以鼻,那樣是無補於實際的。因為吸收外國文學的優點,和世界文藝思潮的氣息,並不是把小說中的人物裝上?鼻子藍眼睛,而只是提高創作水準,用不著太緊張,否則諾貝爾文學獎將永遠落不到中國人頭上來。
近幾年來,儘管現代小說不受歡迎,不肯故步自封的作家卻仍大有人在。文甫就是其中的一位。到這本《沒有觀眾的舞台》出版,他算是出版過三本短篇小說集了。一本《解凍的時候》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女生宿舍》是在馬來西亞出版的,都是另闢蹊徑,追求現代文學後的成果。他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讀過,甚至很多是未定稿。這本《沒有觀眾的舞台》,也是我從三四十篇小說中提供意見讓他自己選輯的。這本書我最喜歡的是那篇〈飢渴〉。它是現代文學中可貴的收穫。〈多角的玩具〉和〈貓王的悲哀〉也很不錯,其餘的也很夠水準。而且他就連取題目也別有心得,一點酸溜溜臭烘烘的味道都沒有。據說上面提到的幾篇作品,發表時都是沒有稿費的。由此可見不要錢的反而水準高些,想寫好小說的人絕不是標新立異來騙錢。有幾次我偶爾在報章雜誌見到他寫的東西,竟脫離現代小說的正途,而涉及賣弄技巧。我問他什麼道理,我說那是該打手心的。他說是人家約好了的,不可以寫得太現代。在現代文學上他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但是有些為了稿費而又捨不得放棄現代文學的立場,從而徒在人物觀點和心理描寫上不斷變換花樣,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卻並不理想。
水準高而又雅俗共賞的東西是不太容易寫的。福克納讓出版商撕毀過合約,喬伊斯沒有人肯印他的《都柏林人》,使他憤而離國,死在瑞士。為藝術而受盡磨難的作家是太多了,這種歷史也將永遠要重演。我只祝福文甫能堅持下去,創造出更高水準的作品,才不致辜負他已有的成就。
現在文星書店要給他出書,他要我寫點意見,以我們相知之深,應該是義不容辭;但我既無籍籍之名,肚子裡的墨水也極為有限,文章寫得不雅,形容也很猥瑣,連架式都擺不出來。所以這篇小文只能表示祝賀和期許! ──五十四年五月於全省首髒之區的三重市 本文作者楚茹先生,曾獲《亞洲畫報》小說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文學翻譯獎。譯有《林肯的幽默與機智》、《愚人船》等書。
推薦序二
領悟而來的思想力量
楚 卿
在沒有觀眾的舞台上底演員是寂寞的;但正因為他們不為觀眾而活動的時候,那就不盡是在演戲了。
那麼,是在幹什麼?
我不敢而且也不能用簡短的話語來回答。
人生是幹什麼?或是,幹什麼才是人生?人生什麼也不幹,所以什麼也幹得出來;或者,什麼也幹,所以什麼也幹不出來。只有一件事:──不為觀眾、沒有舞台;或者有舞台沒有觀眾而演的戲,才是屬於自己的──也許那就是所謂人生吧。
文甫和我一樣,認為人生是座舞台這句話是陳腔濫調。所以,我們兩人的小說是在解剖室裡進行的。所以,我們小說裡的人物不是演員而是被解剖的屍體──即使有的很美,有的很動人──不過,文甫比我「仁慈」,他在下刀的時候,面帶笑容,而我不是。
人生的缺陷太多,美的可能虛偽,善的可能矯飾;惟有真與不真才能定其感人的深與淺。感人以衝動的是虛偽與矯飾,只有真實的了解與認識,才能產生因領悟而來的思想力量;而這種力量,就掌握了文甫的創作心靈。
文甫的這部包括十九個短篇的集子,是繼他在香港出版的《解凍的時候》和在馬來西亞出版的《女生宿舍》之後在台刊行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對於一片錦繡,我想用不著費辭去解釋的,因為,它們已經呈獻在讀者的面前。 ──五十四年七月於省立台中一中 本文作者楚卿先生,曾獲日本奧林匹克小說獎、國軍新文藝小說銀像獎、高雄市文藝獎。著有詩集《生之謳歌》、《永恆之巒》,散文《懷夢草》,小說《長河》、《不是春天》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