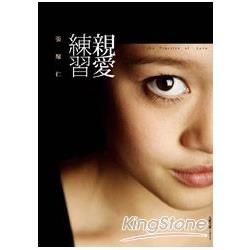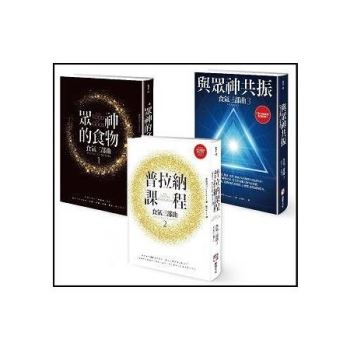似水年華,勿忘初衷 終究,我們還是來到了這樣的時光。
這樣單薄的,稍一碰觸稍一擁抱就要碎了逸散了的時光。真是怪。怎麼一個人說瘦下去就這麼瘦下去呢?我撫摸著那手,手背是扎針過度的紅腫、紫藥水,以及女性們慣常的冰涼,冰涼是醫院亮晃晃不知所終的長廊,而我們坐在盡頭,輕聲交談:「沒辦法啊,一個多月沒吃囉。」
母親說,不知道還要拖多久欸。
母親說,醫生下個禮拜才會來。
母親說:「希望不要再讓她痛苦了。」
母親說話的時候,外婆好不容易睡著了,細細的鼾聲從她好瘦好瘦的身脊浮起來,生出細細的夢,不夠柔軟也不夠溫暖的床鋪忽而膨脹、忽而陷落。下午時分,窗口湧進南方才有的氣味:揉雜了草與泥土的餳澀,一點點風,一點點這座小城偷閒的慵懶的片刻,那樣忍不住喘息忍不住呵欠,無可無不可。
眼前那塊種著甘蔗的小農地,睡著了,自顧做著它的夢。
母親說,晨起推輪椅至此,外婆還問:「啊耀仁考過(博士)了沒?」又問:「咁是要來去換個尿布,嘸等下耀仁來,無好味?」言下之意,意識猶清醒得很呢。 母親說,你外婆從年輕起就愛乾淨,愛漂亮。
母親還說,頂擺手術前,猶擱念講咁是要先去洗個頭欸。
母親說,不知她還要受多少苦?
視線裡的彼端,幾名孩子奔跑著,試圖甩開身後那隻米格魯,惹得犬聲又急又響。他們很快被追上了,笑著鬧著,逗弄牠、抱牠,一會兒又放開手疾速奔跑,反反覆覆、樂此不疲。灰淡的天空下,他們乾脆地笑,他們乾脆的笑是這個午后悠緩的夢的點綴。
多麼使人放鬆的南方。 我這麼激動著,想起從前和弟弟一同挨著外婆,一同盯住天花板那盞鵝黃色小燈,憂心虎姑婆會不會突然出現?突然間,弟弟叫起來:「阿嬤放屁!」外婆因而忘了繼續往下說,像個害羞的孩子自顧抓起被角搧著搧著。或者,要求我遞上一把裁縫用剪刀──刀口又鈍又重──邊剪邊笑:「老囉,厚皮厚樣,老囉。」
老了的外婆照例牽起我的手,照例問我要吃乖乖否?她嚷著:「啊你哪攏不轉來找阿嬤踢跎?有查某朋友不就要帶來給阿嬤看看欸?」她的眼睛瞇瞇的,看我看了好一半晌,髮絲銀灰,像這個冬季的日照服貼於額。靜靜靜靜,她握住我的手,靜靜靜靜,閤上了眼,眼前那株木瓜樹同樣輕輕顫動了一下。
外婆睡著了。 外婆睡著後,我緩緩撫摸她的眉心,屬於年歲的紋路皺擠在一塊。我不由低喚:「阿嬤──阿嬤──」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往下說了。倒是一旁的母親連忙提示:「啊你不就要講:『阿嬤,我耀仁啦,我轉來看妳啊。』」但我仍說不出口,兀自握著外婆的手,小心翼翼深怕捏碎了什麼。
於九十四歲的老人而言,就連睡覺也是一場困難了。痛。足痛。外婆呢喃。 「佗位在痛?」我不假思索,惹來母親笑罵,你外婆之前才發脾氣呢,說是佗位也攏在痛,全身軀莫爽快!
瑪麗亞見狀,盡責地按壓起外婆的臂膀,眾人因而哄將起來:「不痛啦,(母親),瑪麗亞給妳抓抓欸,不痛啦。」外婆不耐煩揮揮手:「伊,頇顢!」舅媽姨媽欣慰笑著,以為還能夠罵人不正意味氣力勃勃?於是我上前試著揉捏她的肩頸,它們變得又瘦又小,一點也不若印象中之巨大──一直以來,外婆便手長腳長,高出外公半個頭的──那一瞬,我想起照片裡還很年輕的外婆(其實也已六十好幾囉),穿在她身上的那件洋裝可真好看。
(一直以來,她在我們眼中,就是個又時髦又端莊的長輩)(再後來,某個瞬間她就老了,被瑪麗亞攙扶著面對鏡頭時,猶努力自持:「莫攝啦,歹看啦,頭毛攏沒整理!」)(再後來……) 是啊,不過幾年的時光,時光竟將我們拗折形塑成難以預料的樣子。
原本我的腦海當中,想說說關於這些年來經歷的那些:對於小說創作依然懷抱的不確定,幾段告吹的戀情,以及不斷不斷吞噬意志、力不從心的生活──或者,我還想說說,關於這本小說創作的發想、篇章的安排、瑪麗亞之於母系系譜的意義,以及那個作為敘述原型的外公家二樓,每每夜底,角落堆堆疊疊的陳舊的書籍(它們大部分是我讀中文系的表姊留下來的小說),皆發出窸窸窣窣鬼魅似的暗語……
甚至我也想說說──但這一刻,它們似乎都不重要了──也許不是不重要,而是在面對近乎蟬蛻近乎描圖紙燃燒的脆薄時光裡,該如何向世界向時間喊停?該如何將那一點一滴即將遺忘潰散的什麼加以挽回?
阿嬤。阿嬤。
兩位前來探視的師姐持續誦念著: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她們的聲音又遠又近,彷彿通過狹長而陰闇的甬道,怔忡撞見外婆更衣的那個小男孩,他看見依稀光度裡那對晶亮的眼神,它們同樣怔忡地望著他,而羞赧不知所措的老人且哄慰道:
啊過年,有歡喜否?
啊外婆,這世人您有歡喜麼?
儘管,時光已經走到盡頭了。
儘管,那掌心的溫度遲遲未嘗溫暖起來。
但我始終牢牢記得,那麼多年以前,某位師長語重心長的叮囑:「似水年華,勿忘初衷。」
那些迢遠的現在的未來的──那些,它們走進我的生命,走過我的身邊。它們走下去。走下去。在這靜靜靜靜的時刻。靜靜靜靜。
勿忘初衷。 (序言寫妥,母親來電話說,你外婆過世了。她說,你外婆這輩子最愛乾淨,所以,我幫她洗了頭、幫她擦澡、換尿布,全身弄得乾乾淨淨,然後,她就這麼在我面前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張耀仁
二○○九年十二月台北中和
推薦序
後鄉土的考掘學
後鄉土小說的崛起,使台灣文學的版圖又向前推進一步。在新世代、新勢力的行列中,張耀仁是受到矚目的一位。他所依恃的世代與世紀,是網路書寫全面到來的時期。在這無法命名的歷史階段,書寫(script)似乎已漸漸淪為歷史名詞。當他們埋首疾書,耳邊響起的不再是刷刷不絕的墨筆,而是起落有致的鍵盤。他們取得知識與資訊的速度,既迅捷又精確。他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不僅建立在廣博的書籍閱讀,也藉助於深邃的網路空間。這個世代的思維、見解、感受,已經不能以苦難的歷史來定義,也不能用迂腐的道德來規範。「新人類」、「新新人類」曾被用來形容上世紀八○、九○年代的青年,但是拿來概括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世代顯然已過於陳舊。
全球化資本主義席捲而來之際,台灣社會曾經被性急的知識分子視為後現代的到來。如果後現代一詞是依照紐約、倫敦、東京的生活標準來形塑定義,則台北的實質內容恐怕才剛剛抵達現代時期。縱然國際都會的風尚也在台北街頭可以發現,但終究都是屬於遲到的、零碎的現象。對台灣而言,後鄉土的命名可能較接近現階段的社會實相。
相對於一九七○年代的鄉土,這小小海島確實經歷過時間的淘洗與空間的改造。即使未曾遠離台灣,這島上住民也可感受到三十年來的巨變。張耀仁這輩作家擁有的鮮明歷史記憶,可能再也不是遙遠的二二八事件或南京大屠殺,取而代之的是美麗島事件、九二一大地震,甚或是八八水災。不同歷史記憶往往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誤解、猜忌、衝突。但是,對於一九七○年代以後出生的世代,族群之間的緊張與摩擦應該已大量降低,畢竟他們承擔的是共同歷史記憶。
張耀仁面對的二十一世紀台灣,消費社會已然成形,資訊多元而豐富,人際關係卻反而變得淡漠疏遠。小說集的命名《親愛練習》,是取自全書的最後一篇,似乎是為這系列作品的主旨定調,又好像是對冷感的新世紀提出忠告。肌膚之親、倫理之愛,正是這冊小說集反覆求索的主題。
這冊作品既可歸類為短篇小說,也可視為長篇小說。每篇小說各具獨立主題,小說人物卻是橫跨各篇。人物與人物之間都是有機的連繫,但情感的割裂使每篇小說的主角都處在孤立狀態。一個家庭的祖孫三代,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女傭,構成系列小說的主軸。阿公臨老的困境,必須依賴外傭的照顧;離異夫妻的怨懟,全然不能割捨親情;成長中的姊弟,吵嘴之餘又相互取暖。看似互不相干的家人,背後牽動著千絲萬縷的情感。每個角色都懷著焦渴的心,期待獲得愛,卻又不知道如何愛。希望在愛中獲得諒解,卻往往在愛中創造誤解。親愛需要練習,全然根源於此。
小說中滲入許多福佬語言,是張耀仁作品的主要特色。他的風格不免使人聯想到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第一波鄉土文學的崛起,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當時台灣受到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上海公報的衝擊,脆弱的海島在一夜之間必須承受巨大挑戰。危機感沉重壓在島上住民之際,文學氣候也在瞬息中產生質變。鄉土文學運動的釀造,在最短時間之內以最快速度巍然成形。從一九七○年到七九年,台灣文壇見證鄉土詩、鄉土散文、鄉土小說的次第問世。台灣這片土地第一次以尊榮的姿態出現在大量的文學創造裡。草根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雙軌發展,終於造就了台灣意識的高漲,從而加速使台灣威權體制發生動搖。
二十一世紀的鄉土文學,與一九七○年代的性格確實存在極大差異。台灣社會的危機感不再來自內部的威權體制,而是來自洶湧襲來全球化浪潮。兩個時代縱然都是在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但是當年的台灣仍然處於封閉狀態,今日台灣則是站在門戶全然洞開的時代。因此,一九七○年代的鄉土,多少是傾向本質論。當時的作家至少還相信鄉土是屬於高貴的信仰,意味著一種純樸、善良的價值,同時也隱喻著一種理想的寄託。
張耀仁筆下的鄉土,典範似乎煙消雲散,理想也杳然無蹤。這冊小說顯然預告,作為後鄉土作家的張耀仁就要投身介入,為新世紀的鄉土給予全新的詮釋。他的文字表現可能流露某種程度的虛無,在故事深處則暗藏了高度的憧憬。他筆下破碎的家庭背後,寓有他無限深情。菲傭瑪麗亞的登場,印證了小說家敏銳的筆觸。外勞與外傭的現象,是台灣社會捲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他們是社會學研究者的文化議題,卻罕見於文學作品。張耀仁容許瑪麗亞進入他的小說,恰可反映他細緻的觀察。更為不凡之處,在於透過監視器的窺探使外傭看護的生活細節全然曝光。窺視是對於私密的刺探,這樣的筆法恰其如分彰顯了外傭的人權問題不受尊重。
小說中的瑪麗亞,帶出更複雜的意義。她是小說中年輕主角性啟蒙的對象,也是破碎家庭生活實相的一個反射。外籍女性與本地女性以互為他者的形式出現於單數、雙數的小說裡,交替的秩序使情慾問題鑑照了文化認同與身體歸屬的差異。位於東北亞國際地理位置的台灣,可能曾扮演被殖民的角色,但是在全球化的分工下,台灣又同時扮演支配東南亞的上游國家。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是張耀仁在行文之間埋下的緊迫質疑。小說家揭發這樣的問題極為深沉,如果家庭倫理發生傾斜,則種族倫理也不可能獲得扶正。其中的微言大義,值得深思。
長期以來反殖民、反帝國的論述氾濫於台灣社會,在歷史上曾經受到傷害的記憶總是保持特別鮮明。但是,面對台灣的弱勢者,或是來自東南亞的新娘與外傭,卻往往報之以歧視與貶抑。這種文化態度也漸漸成為一種習慣模式,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小說中的女性與外傭,便是處在如此不平衡的文化生態裡。在抑揚頓挫的故事情節之間,小說的筆調特別冷靜,但是把全部小說匯集起來時,竟隱然傳出震耳欲聾的抗議聲音。這正是後鄉土小說的重要特質。
初識耀仁,是在政大校園。他以傳播學院博士生的身分出現在研究所的課堂,無論是提出問題或撰寫論文,往往都能展現非凡的格局。他的思考極富邏輯,文字則精鍊準確,留下的印象令人難忘。他的小說《親愛練習》置於桌上時,還格外強調這是一冊關於外傭的故事。他的風格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一方面挖掘內心世界的想像,一方面又利用符號的可塑性完成情節銜接。跳躍的節奏出人意外又入人意中,簡直是在預告一個重要寫手的誕生。他擅長自我調侃的筆式,也酷嗜活潑反諷的句法,不能不使人暗自讚嘆。他的人道立場與人文關懷,使淡漠的社會不致喪失溫情。請傾聽,張耀仁的聲音裡,讓人儼然發現後鄉土的姿態勝過後現代的矯情。
──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政大台文所 (陳芳明教授,文學評論家,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著有文學評論集《危樓夜讀》、《深山夜讀》,散文集《昨夜雪深幾許》、《陳芳明精選集》,學術論著《探索台灣史觀》,主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