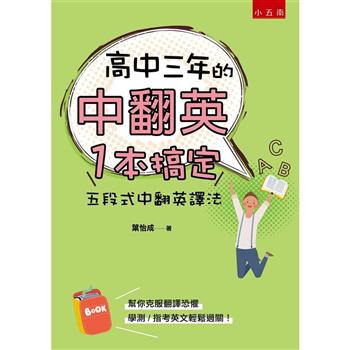精采一生:送曹又方 丘秀芷
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難
朋友們商議怎麼辦送別會,才能讓離我們不遠的曹又方走得心安。朋友說李煒希望把他母親定位於「文學家」,而非「暢銷作家」,更非通俗文學作家。我心中誇著這位外貌神似母親的李煒:真孝子!真是知母莫若子。
其實很難幫曹又方定位。也許她自己也沒法子!她曾在文章中寫自己初中二年級時(應十三歲吧)一次作文,老師出作文題就一個「我」字,一向文思泉湧的她想了想,最後只在作文簿上寫了十一個字:「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還難。」
身為曹又方諸多朋友之一,不算是很要好的。不過,想來跟她十分親近的幾位,也未見得了解她,她們太縱容她,反倒是不遠不近的我也許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較客觀也說不定。
曹又方三月二十五日凌晨病逝,而非自一九九八年就得的癌症,卻是心肌梗塞,所有報章媒體報導她民國三十二年生,她享年六十六歲或六十七歲。其實,她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虛歲正是本省人所說的「過不了九」,六十九歲。足歲則是六十七歲又十一個月。
只不過以前看她本人,看不出她的年紀。這個美人,如果不是她文章中自己寫:小四開始崇拜武俠影后于素秋,才知道她生在抗戰勝利前幾年。可是,她樣子真的一直比實際年齡小很多很多。
值得驕傲的叛逆期
自小愛表演,愛看電影,更重要的是愛看書。母親早逝,唯一的姊姊整整大十二歲,父親又續絃,繼母帶弟妹過來,當然有所高低,加上原來就古怪拗霸,她一直橫衝直撞走自己的路。
留級、逃家、記過,似乎是一個逆女壞學生,幸好喜歡閱覽群書,幸好那個年代社會中沒有那麼多陷阱,她還能不受大傷害。
「回憶成長時期的叛逆,未嘗產生一絲一毫的怨悔。因為一本赤忱,非但不會為曾經叛逆的那個我感到懊惱,甚至竟有幾分驕傲哩!」
她的「逆女」時期,今日看來未必不好,愛看課外書,小四讀《紅樓夢》,初一就讀完莎士比亞全集譯本,初二是張愛玲迷,早早投稿。最有趣的是中學六年讀台南女中常逃學沒被發現,因為全校沒人逃學,老師從不點名。所以中學的學校成績實在不怎麼樣。
她至老不認為自己曾是一個不念書的爛學生,因為她從小學到中學,已把不少文學「大家」的作品讀透了。但考不了大學就去考軍校,也循規蹈矩的讀了兩年,學校裡有不少學長已是「文藝青年」,如唯弦、隱地、劉維斌、張永祥,以及台大畢業來學校受軍訓的葉珊(楊牧)等等,應該是無形中引領她走向更寬闊的寫作之路。
軍校只讀兩年就輟學,又當一段時間的邊緣人才又考進世新夜間部。完全不同的氛圍使曹又方尋回活潑外向的自己。也在這時和一個小她很多歲的男孩子結婚,唯一兒子李煒出生後不久,她結束那短暫的婚姻。
這時已開始正式寫作,第一本書是出版於一九七○年的《愛的變貌》,以蘇玄玄為筆名。起步遲了點與她同年代女作家張曉風早已文名大揚,得中山文藝獎了。季季、蔣芸更被認為「彗星」,劉靜娟、黃娟、張菱舲、雨僧,各有風格。更別說瓊瑤爆紅,一下子成暢銷作家。
其實曹又方所以沒有立即文名大揚,主要是她很快的走進編輯台。在《聯合報》,在《實業世界》、《老爺財富》,後來又到美國編華文報《中報》,年輕時代的蘇玄玄唯一受注目的小說應是《綿纏》。把一般的詞彙纏綿倒過來,確實引人討論一陣子。
很長一段時間當編輯,扼殺了自己的寫作空間,但是也因閱稿量多,吸收各方精華。
拓荒新女性
最值得一書的是赴美前她曾和幾位女性朋友共組「拓荒者出版社」││近年曹又方對呂秀蓮還有微詞,四十年前推動新女性主義也罷,主持拓荒者出版社也好,都是幾個人共同努力的,但呂秀蓮在後來全只突顯自己一人。其實曹又方從策畫活動到總編輯,還真是盡了大力。
所以倡導「新女性主義」,緣於自小想做男孩,想掙脫女性的桎梏,所以從少女時,在男女感情的處理就是採取主動,發生得快,去得絕斷。不以為是濫情,也不後悔走過那一段。
和一般朋友(包括女性)的友誼倒是永恆。跟曹又方當上朋友,只要不是「利害」關係都能真摯永遠。她的「摯友」很多,卜大中、陳剛信、黃麗穗、邵世光、孟東籬、陳鴻、汪季蘭、胡因夢、吳淡如、張淑芬、柏楊、愛亞、朱寶雍、陳念萱、歐陽元美……。還有一些攝影家、藝術家寫不完。
有趣的是曹又方脾氣非常暴躁,大家倒也能忍受她那霸氣偏頗。她有一種人格特質,讓大家忍她、讓她,雖然不一定附和她。
趴趴走歲月
一九九八年得了癌症動了大手術,出院不久,她就戴假髮跟我們出遊。一次去竹東,一次去台東,還一大早騎自行車出去,沒回來,主辦活動的我急壞的請旅社老闆騎機車出去尋找,把已力盡的她載回來,當下我高興之餘發不了脾氣。
曹又方愛各處跑,不說她曾在紐約、舊金山工作十多年,後來回台灣主持圓神出版社出很多書,也是各處旅行。即使動兩次大手術,腹內器官去掉一半,她依舊出院就趴趴走。除了台灣,一年中總要出國三四回。
數年前,她乾脆離開出版社,搬離台北到珠海定居。和她為鄰的還有不少台灣朋友。那房子我去過,袖珍,但景觀絕佳,從落地窗可看到嶙峋怪石的小山,也可以看到海。有個阿嫂幫忙打理,不過,她也常不在家,有時去上海、北京演講;有時回台灣,回台灣住唐琪家,呼朋喚友去吃美食。
真正美食家
早歲她愛在穿著上打扮作怪,不是極短就是極長,要不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只怕還要臉上作文章。年輕時多長髮飄逸,中年後長髮挽起,整個輪廓絕美,她除了個頭稍小,那種漂亮和特殊氣質,還真少有人能勝過。
後來,她也不太注意美醜,尤其癌症化療頭髮掉光了再長出來,就一直是短髮。而且穿的衣服也有很大改變,非黑即白,偶爾有其他顏色,也多單色。
她倒是不改原先的注重吃。有些人號稱美食家,但未必吃得精緻,曹又方很少為哪家餐飲作活廣告,她也不占「白吃」的便宜 ,總是真的去點食,品嘗,付錢。也許因為她父親與夫家的公公都真懂得吃,尤其吃魚。
她愛吃魚,有段文字談「魚、吃得驚豔,際遇不多。算來是有個冬夜,在保加利亞的荒野馳車,來到一家名叫「金魚」的餐廳,點了魚,原來也不抱何等期望的,想不到鐵製的魚形容器的茄汁熬魚,連湯都喝個乾淨。」
她也記阿根廷的烤鱸魚,還有九寨溝「海子」的鯉魚,宜蘭北關的「黑毛」,基隆廟口象魚湯,台南虱目魚粥。
近年她回台,會找一群女食客去一家叫「阿英」的小小店吃魚,這家店的菜不加味精,正合她口味,「阿英」在溫州街小巷中,就在我家附近,所以每次找我去。得癌症後,很多東西曹又方不吃,尤其不吃有奶製品的東西,而吾家附近泰順街有家糕餅店做的鳳梨酥不用奶油奶粉,她最喜歡。
吃任何東西,淺嘗即止,但是有一件事,讀書,無論年輕或走過中年,嗜書如命,讀自己喜歡的中、英文書。還有寫作,倒不只有寫小說、兩性書刊,近年還寫養生書和勵志作品,最近在《聯合文學》看她寫沈從文、朱自清和錢穆,風格又丕變。想來她想朝另一種研究路線走!
別 離
只是她終就沒走脫病魔糾纏,據最後和曹又方吃飯的徐卉卉、高雷娜說:那天李煒也一塊兒用餐,然後李煒到香港開始新工作,但曹又方就住進病房。汪季蘭等人輪流去陪她,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她走了,愛亞送她最後一程。
曹又方在二○○一年第二次開刀後,年底,認為生命無多,不如生前舉辦破天荒的第一個告別式,該到的朋友都到了,那天她穿一襲黑衣,美美的,到處布置白鮮花。朋友有的哭有的笑。那時她就留言死後要樹葬。經過快七年,她一直活得好好的,朋友們還在等待下回她再從珠海回台,每次住半個月一個月,一起去看桐花,看山山水水,一起吃簡單卻美好的食物。期待她又有新題材的作品出現。
但是,她在為自己舉辦告別式後七年又三個月,心肌梗塞真正告別。
四月十二日,有個隆重簡單儀式,然後樹葬。四月二十八日,她六十九歲冥壽在老輩人叫七十,大家為她在華山藝文中心舉辦送別會。
原載二○○九年五月號第二八三期《文訊》
‧本文作者丘秀芷女士,曾任行政院新聞局顧問,現任世界女記者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副理事長。著有《留白天地寬》、《番薯的故事》等多部,並主編《風華50年││半世紀女作家精品》等書。
曹又方的尋常與不尋常 袁瓊瓊
曹又方早期叫做蘇玄玄的時候,見過她一面。
記得是在朱西甯家。不過自己腦海裡存在的那個畫面,卻是跟當年朱家現實環境的任何一處都完全不符合的。
我記得的那個朱家,大約存在於一九七五年左右。有個大客廳,靠牆一排方方正正灰色布質沙發,沙發前一張大茶几。地上躺著灰色的貓兒黃色的狗兒「們」。椅子非常多,每次去都是一群人,就搬竹椅子來坐。而朱西甯常常是非常隨性的白色汗布衫一件,遢坐在沙發裡,頭髮花白。每次看到他,他總是笑笑的,但是感覺他非常疲累。
而曹又方豔光十射。記憶裡挖出來的那塊圖像:蘇玄玄坐在一張高凳子上;當時流行迷你裙,她的迷你裙極短,右腿疊搭在左腿膝蓋上,又白又直又長的,一雙豐美的腿。穿著高跟鞋,黑色,起碼也三吋。一頭黑髮,垂直披掛,長度及腰。臉龐亮而白。
為什麼在朱家那十足樸實的環境裏,卻留下了蘇玄玄這樣一副彷彿坐在小酒館吧台前的形象呢?真不明白。不過當時的她,有那種風情。她坐在角落裏,而角落隨她輝亮。她無可非議的美麗,極美,然也極妖異。她人坐在那裡,隨即讓白天變成夜晚。
她早期的形象,我就只注視過這樣一次。再之後見到她,是十年後了。她那時在紐約。畫家丁雄泉約她和我們喝咖啡。去的地方叫「美麗華飯店」。這地方,我和管管停留紐約的時候,幾乎每次和丁雄泉見面都約在這裡。丁好像很喜歡這地方。其實跟那堂皇的名稱完全不搭,是家髒髒破破的小餐館,所有的東西,桌椅,陳設,送上來的食物,甚至侍者廚師,全都是一層膩黃。
小方桌子兩張兩張並排,像小學裡學生座位,桌兩旁卻是卡車座。我們擠著坐在座位裡。桌面上有芝麻粒和糕餅屑,端上來的咖啡裝在油光光的瓷杯裡。因為後來丁雄泉又帶我們去吃高級餐廳,一餐花了八百美金,所以我知道他來這裡,不是為了省錢。這地方於他,一定標示了某些記憶吧。
她當時寫作已改用「曹又方」。我們約在中國城會面。遠遠看見她站在路邊。她非常嬌小,讓我意外。因為印象裡一直留著她那雙長腿。冬天,她是及肩髮,戴了頂水兵帽,是那種反扣了像個大碗的那種,斜斜蓋在頭上,非常俏皮。身上一件海軍藍大衣。因為她白,那海軍藍被襯得非常華麗豔美。我後來對於海軍藍著迷了好一陣子,甚至自己也做了一件海軍藍的雙排扣大衣,跟那次印象有關。
也第一次聽她開口說話。她聲音軟軟糯糯,非常嬌氣,帶了口音。我們在美麗華聊天。丁雄泉說他的素描訓練讓他看任何一個女人,「隔了衣服都知道她全裸時是什麼模樣。」曹又方就皺眉,小小的一點點皺摺在她亮白光滑的額頭浮起,她說,用她那嬌氣的,非常嫵媚的腔調,俐落乾脆的說:「喲~~~你別理他,見到女人他就愛說這個。」
那次玩了一天,跑去大西洋城賭場,在海灘旁的木頭走道上聊天,晚上回到她住處喝茶。她屋子很小,全部布置都用白色,潔亮到妖異。她說她剛搬來時,這屋子髒的程度,地面上污垢層層堆積,她刮了三四層才見到地板原來是白色的。全是她自己動手。看到她人美美的,真難以想像她會做這種苦工。她說:「你不自己來人家不會做的這麼徹底。」刮地板就刮了一星期。
曹又方的美沒法歸類,不是任何一種。她有一種薄薄亮亮,瓷器般的輝耀感,彷彿易碎。但又有點像威尼斯嘉年華的面具,似乎象徵性大過事實,而因之有種無法磨滅的,消滅不了的東西;堅韌,而且固定。
後來愛亞常說:她是遼寧人,東北人都這樣。
好像這樣就解釋了一切。關於她那種尋常以及不尋常。
原載二○○九年四月二十日「老原腦袋裡是花園」部落格
‧本文作者袁瓊瓊女士,專業作家與電視編劇,著有散文《繾綣情書》、《孤單情書》、小說《春水船》、《自己的天空》,短篇小說《或許,與愛無關》等。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風華的印記(增訂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5 |
中文書 |
$ 175 |
小說 |
$ 179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風華的印記(增訂新版)
有人形容她是「文壇的維納斯」,曹又方卻說自己是「不斷跟自己鬧革命的人」。美麗、多情、忠於自我,連面對病魔的挑戰,曹又方都積極面對,還在大陸各地傳授健身良法,並獲讚譽。
本書精選曹又方不同時期的散文代表作。她深厚的文學根柢,增添其散文的內涵,多篇文章入選國內外各種文選,讀者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文學的曹又方」。有她在紐約的生活取景,也有面臨情感挫折時的複雜心境,還有她與文學、書本那種切不斷的革命情感。可品嚐文章之美,亦可從中體悟人生哲理,積極而淡定。
特載收錄丘秀芷和袁瓊瓊兩篇紀念文章,看見不同人眼中的曹又方。
【本書特色】
●曹又方唯一散文自選集,精選代表散文作品
●新版特收丘秀芷和袁瓊瓊紀念文章,顯現不同的曹又方
作者簡介:
曹又方(1942~2009)
著有小說、散文、雜文、兩性、心靈、女性成長各類書籍六十餘種。長期從事新時代運動及婦女運動,大力倡導心靈革命及環保運動。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作品本本暢銷,曾榮登年度出版風雲人物,十大暢銷女作家。
2001年底舉辦「生前告別式」,文壇菁英群集,勇敢抗癌,到處傳播養生防癌良方。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愛的變貌》、《綿纏》、《濕濕的春》、《天使不做愛》;長篇小說《美國月亮》、《愛情女子聯盟》;散文集《情懷》、《門前一道清流》、《寫給永恆的戀人》;傳記《靈慾刺青》、《愛恨烙印》;勵志《人生一定要精采》、《淡定.積極.重生》;兩性《下個男人會更好》、《男人真命苦》、《愛情EQ》兩卷;女性成長《做一個有智慧的女人》、《決心一生美到底》;食譜《養生防癌抗癌食譜》、《200道美食健康素》等。另有《曹又方精選集》二十四卷。
推薦序
精采一生:送曹又方 丘秀芷
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難
朋友們商議怎麼辦送別會,才能讓離我們不遠的曹又方走得心安。朋友說李煒希望把他母親定位於「文學家」,而非「暢銷作家」,更非通俗文學作家。我心中誇著這位外貌神似母親的李煒:真孝子!真是知母莫若子。
其實很難幫曹又方定位。也許她自己也沒法子!她曾在文章中寫自己初中二年級時(應十三歲吧)一次作文,老師出作文題就一個「我」字,一向文思泉湧的她想了想,最後只在作文簿上寫了十一個字:「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還難。」
身為曹又方諸多朋友之一,不算是很要好的。不過,想來...
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難
朋友們商議怎麼辦送別會,才能讓離我們不遠的曹又方走得心安。朋友說李煒希望把他母親定位於「文學家」,而非「暢銷作家」,更非通俗文學作家。我心中誇著這位外貌神似母親的李煒:真孝子!真是知母莫若子。
其實很難幫曹又方定位。也許她自己也沒法子!她曾在文章中寫自己初中二年級時(應十三歲吧)一次作文,老師出作文題就一個「我」字,一向文思泉湧的她想了想,最後只在作文簿上寫了十一個字:「了解自己比了解別人還難。」
身為曹又方諸多朋友之一,不算是很要好的。不過,想來...
»看全部
作者序
不斷跟自己鬧革命的人
曹又方其人其文
「我對自己的選擇,從不後悔。」曹又方說。二○○一年十二月,在與末期癌症奮戰三年後,她瀟灑出擊,挑戰大禁忌,用最喜歡的音樂與花卉佈置,為自己舉辦「生前告別式」,親自與親朋好友一一告別,震撼各界。
曹又方,本名曹履銘,遼寧岫岩人,出生於上海,而令她魂牽夢繫的故鄉則是青少年時期成長的台南。從台南到台北,由台北至紐約,一九八九年返台,投身出版事業,除了作家頭銜外,她也成了知名的出版人。
寫作是生命的信仰,編輯是生活的依恃,人生羈旅,曹又方行遍天涯,始終沒...
曹又方其人其文
「我對自己的選擇,從不後悔。」曹又方說。二○○一年十二月,在與末期癌症奮戰三年後,她瀟灑出擊,挑戰大禁忌,用最喜歡的音樂與花卉佈置,為自己舉辦「生前告別式」,親自與親朋好友一一告別,震撼各界。
曹又方,本名曹履銘,遼寧岫岩人,出生於上海,而令她魂牽夢繫的故鄉則是青少年時期成長的台南。從台南到台北,由台北至紐約,一九八九年返台,投身出版事業,除了作家頭銜外,她也成了知名的出版人。
寫作是生命的信仰,編輯是生活的依恃,人生羈旅,曹又方行遍天涯,始終沒...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曹又方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7-01 ISBN/ISSN:97895744470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