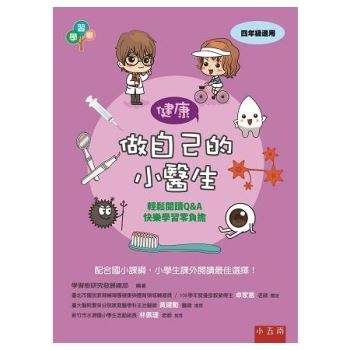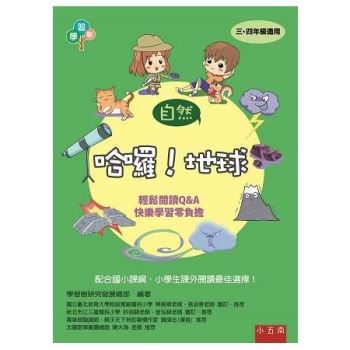廖玉蕙最深情的散文。
人生畢竟不是童話,後來常常不盡美好,甚至經常伴隨著無奈和悵惘。從四年前的大年初二起,母親沒有了後來;我沮喪傷痛之餘,開始致力為母親留下「過去」,以走出自己幾乎再也沒有力氣承擔的「後來」。
這些關於母親點點滴滴,都記錄在這本散文集中,有悲有喜,有哭有笑,感人至深。
帶母親去喝一杯香醇的咖啡,卻在暗夜裡奔回醫院;看著母親讀著自己的新書,卻老在第五十四頁之前徘徊;擔心母親沒人照顧,請外傭來幫忙,沒想到卻變成一場爭寵大戰。
回溯母親年輕時的燦爛時光,有浪漫不能說的愛情故事,還有記錄家庭用度的帳本,更有母親靈巧的手藝和精湛的廚藝。
回歸到女兒的身份,童年和媽媽的關係總是緊張,偷看媽媽租回來的小說而挨打,又因愛哭、默契不足而挨打,最終才發現自己只是想要當媽媽最鍾愛的女兒。
本書特色
★廖玉蕙最深情感人的親情散文
★全書搭配上相關照片與插圖,讀來令人更深刻
★特收錄短篇小說〈彩鳳心事〉,看散文家廖玉蕙寫小說。
作者簡介
廖玉蕙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創作有《純真遺落》、《大食人間煙火》、《廖玉蕙精選集》、《像我這樣的老師》、《五十歲的公主》、《嫵媚》、《走訪捕蝶人》……等三十餘冊;也曾編寫《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新文學選本》等語文教材多種。曾獲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及中興文藝獎。多篇作品被選入高中、國中課本及各種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