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人探戈
作者/ 章 緣
本名張惠媛,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紐約大學表演文化研究所碩士。旅居美國多年,二○○四年後移居中國大陸。曾獲《聯合文學》小說獎、《聯合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等。作品入選爾雅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中副小說精選、台灣筆會文集、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九歌九十四年小說選等。著有短篇小說合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擦肩而過》、《越界》,長篇小說《疫》,隨筆《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
老范的日腳,本不會跟台灣太太有搭界的。
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人生的軌跡相差十萬八千里,不僅是上海和台灣的空間距離,還有七十來歲及五十來歲的年輪代溝,更甭提一個是水裡來火裡去閱人無數的老克拉,一個是平凡守分溫室裡生長的家庭主婦。這兩個來自不同星球的人,卻莫名其妙被一條銀河給牽上了線。
說得好像有點曖昧。誰說一個男的遇上一個女的,就一定會有曖昧?但它還一定就曖昧,因為老范最善於營造一種浪漫的氣氛,最知道怎麼說怎麼笑,眼神怎麼勾轉,能讓面前的女士心生蕩漾,不管是芳齡二十的小姑娘,還是跟自己一樣白髮多過黑髮的阿婆。但是那曖昧也不一定是你想的那種。
老范就住在上海水城路一帶某個所謂的「文明小區」。那一帶已陸續被日本人台灣人入侵蠶食,一個個新建的高檔小區配有會所綠地和大門警衛,一間間日本居酒屋克拉部,台菜店及台灣小吃。走在水城路,他彷彿到了異鄉。唯一讓他心安的是他住的小區,多少年來維持著同一個面貌,白色的外牆風吹日晒成糞土汙黃,大門外的小塊綠地上堆滿雜物,盆盆罐罐種了些蒜苗香草,外頭停了一排腳踏車,少數人家門口停著小轎車,公共樓梯間燈泡不亮,玻璃窗破了幾塊,連長竿伸出去晾晒的衣服,也顯得面料粗糙,特別寒磣。但是這裡安靜。真的,老范每次走進自己的小區,都訝異於這裡跟外頭的差別。外頭,就在一條街之外,是那麼車水馬龍市囂不斷,一走進這裡,怎麼時光倒退了二十年,什麼都緩下來,安靜下來,不慌不忙。就連這路邊的牆草,隨風搖曳都帶著韻致。二十年前初搬來時,這裡是被人羨慕的時髦小區,老友們都還擠在擁塞汙暗的石庫門,他就搬到了這裡。他總是那個最快接受新事物,擁抱新變化的人。老友都說,小范啊小范,儂來塞,花頭經老透啊!
再怎麼物質貧乏的年代,他也能穿得整整齊齊,跟別人一式一樣裡,從領口袖口這兒那兒一點一滴翻出講究來,只給內行人看。多少個運動,他都避開了大浪頭,從沒真的傷筋挫骨,就像這路邊的草,勁風來了彎彎腰,風過了又腰桿筆直。到現在,要過七十四歲生日了,他的腰桿還是挺直的,一頭銀髮,常年穿條吊帶西褲,燙得筆挺的襯衫,擦得亮的皮鞋,挺頭挺胸走在馬路上,他老范還是很有看頭的。
說有錢,他沒什麼錢。除了這套舊的一室一廳,跟他年紀相當的老家具和即將報廢的家電,醒目擺在櫥架上的古董唱片、留聲機和老相機─不是收藏品,是他青春歲月的紀念物(沒人知道這些東西怎麼沒有在幾次運動裡給搜刮一空),此外身無長物。但是那些老東西都是有來歷的,就跟他給人的感覺一樣。如果你有機會到他小屋裡坐坐,可以聽到很多故事。他不談工作和出身背景,只愛吹什麼時候在哪裡看過的一場熱鬧,跳過的一支舞,吃過的一頓大菜。這熱鬧這舞蹈這美食,當年人人愛聽,剛從翻天覆地的運動裡熬過來,什麼主義啊黨啊建設與破壞都膩了,只想把眼前的小日子過好,一個繁華的老上海,由見證人活生生帶到眼前來,怎不教人懷念嚮往。經過數十年清湯白水的日子,新的繁華來了,來勢洶洶,沛然莫之能禦。有了新的繁華,老克拉的故事就真的翻頁進入歷史了。但是老范還腰桿筆直(歸功於多年的舞功和私人的講究),還未進入歷史,老聽眾跑了,他還能「花」來一些新聽眾,最多的就是跟他學舞的女士們。女士愛聽故事,不管是窮是富。他現在講故事總帶點懷舊的傷感,還有一絲嘲諷,以瀟灑的手勢,多情帶笑的眼睛(年輕時一雙桃花眼,現在一笑就布滿魚尾紋)娓娓道來,跟他煮的黑咖啡一樣,很香,很苦。
靠著一點退休工資,老范還是過得有滋有味。鄰居們每天看他穿著整齊,走進走出,小屋裡也不乏訪客,女客居多。同齡的人早就背駝氣衰,冬天在屋子裡孵著,湯婆子握在懷裡打瞌蟲,夏天敞開門窗,一件汗衫一把蒲扇趕蚊子,只有老克拉活得像個人,像個男人。他們總結一句,老范啊老范,路道粗,花頭多來兮。
老范的一世英名,卻差一點毀在這個姓杜的台灣太太手裡。
就跟著老范稱她小杜吧。小杜住在附近的涉外高檔小區,這天下午,她到台菜一條街來吃飯洗頭,然後到便利商店買咖啡奶精。買好後,沿著馬路漫無目的往前逛去,便到了剛整修得煥然一新的文化中心,外頭掛一長條紅幅寫著奇石展。小杜對石頭沒感覺,除非它們能發光。長日無事,她還是走進去。
一進展覽會場,小杜就後悔了,只有她一個參觀者,講解員一路跟隨。奇石都很大,樣子千奇百怪,顏色也多變,依據造型冠上名稱,太極、駿馬奔騰、蓬萊仙島,還有座八仙過海,簡直無奇不有,也不知是否真的天然。小杜想到還是雲英未嫁時去蘭嶼玩,導遊指著海邊一個有洞的巨石說叫玉女岩,當時她百思不解。每個奇石前的名牌上都有標價,動輒五、六位數。講解員看她的舉止打扮,跟前跟後特別熱絡,說奇石可以鎮邪,擺在家中增添氣派。要把這麼個幾噸重的石頭放在客廳,那客廳也不能是一般的客廳。
走了一圈,看小杜只是微笑點頭,並未對任何一塊石頭表示興趣,講解員指著一個鑲在金屬座上巴掌大的石頭,彷彿是兩個相擁的人形,一邊的手筆直長伸,要不您買個小一點的,擺在茶几上也好看。她一看,牌子上寫著「雙人探戈」。為什麼是探戈不是華爾茲?她仔細端詳。因為石頭剛硬嗎?相較於她所鍾愛的華爾茲,探戈充滿了拉扯抗衡,男女相互叫板。售價……
沒來得及問售價,講解員已笑容滿面向外迎去,門口走進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先生。肯定是什麼大買主囉?小杜不由得特別注意,沒想到來者眼睛瞟到她,竟然在她身上略停,而且微笑著對她微微頷首,一派紳士風範,然後才跟講解員用上海話說了幾句。小杜聽不清他們說什麼,但是老先生幾句話,說得講解員眉開眼笑。老先生說完本來要走,卻改變主意往她這裡走來。小杜這才發現,自己一直盯著對方,是她大膽好奇的眼光把對方引過來了。
「儂好,阿拉勒拉啥地方碰著過?」老范彬彬有禮開口了。
「我想沒有,沒見過。」小杜說。她剛捲過的鬈髮在臉龐兩側恰到好處修飾著臉部線條。
「是嗎,怎麼這麼面熟,這麼好看的笑容,我肯定在哪裡見過。」老范說。這是他最常用來稱讚女士的話,不是稱讚對方的頭髮五官肢體,是笑,是神情。再怎麼皮肉老皺的女人,也相信自己笑起來好看。
我在笑嗎?小杜暗驚,對一個陌生的上海老頭?其實,公平一點講,這個人雖然滿頭銀髮,跟老頭是不搭界的。他臉色紅潤,腰桿挺直,而且還雙眼放電。要說老頭,是家裡那個吧?
文化中心裡有交誼舞廳,下午場兩點到四點,老范常帶著女學生來跳舞。新裝潢好的舞廳,仿外頭夜總會的腔調,裝了吧檯(主要提供熱茶水)、沙發,柚木地板的舞池被擠得只餘一小塊,天花板上一個巨大如鐘的銀色轉燈,照著底下的舞客彷彿夢遊。小杜反正沒事,有個像老范這樣的地頭蛇領路,她就把三層樓的文化中心給走了一趟,跟著老范向裡頭的主任辦事員阿姨等打招呼。她發現,老范的人緣不是普通的好,那些阿姨們從領導到小職員,看到他也像那個解說員般眉開眼笑。老范總是拿自己開玩笑,讚美著對方,雖然那些讚美稱不上貼切,更不含蓄,對方總是嗔笑地照單全收。
此人是誰?新學生?也有人問起小杜。老范總是忙不迭地搖手,這位是新認識的朋友,人家是台灣人。
「台灣人哪能啦?儂吃伊勿落?」辦活動的小姐,跟老范沒大沒小地笑鬧。樓下講解員就是老范介紹給她的。那小姐一張五角臉,高高的顴骨,戴一副雙色方框眼鏡,看起來精明。她轉向小杜用普通話說,「范老師在我們這裡是最有名的老師,你要跟他學跳舞,不要太好噢!」
小杜看向老范,老范也看向小杜,兩人同時轉著一個念頭:有沒有可能?
老范討女士歡心,已經成為一種反射動作了。從十幾歲的小夥子,歷練到今天,他早已成精。在他的圈子裡,還沒有哪個女士他擺不平拿不下。就像鮮花和蜜蜂的關係,老范深信,這些盛開知名或不知名,玫瑰般嬌豔或菊花般淡雅,甚至是野花般不起眼的女人,只要是花,它就等待著蜜蜂。他老范作為一隻從不怠工的蜜蜂,出入過多少女人的心房,雖然沒有一個長留身旁,因為他不是死認一朵花的蜂,但他曾吸取過多少醉人的花蜜呵,午夜夢迴,為了自己做出的浪漫事薄倖名,既傷感又滿足。
但是這回這朵花,可不是他輕車熟路就能擄獲芳心的。這是生在台灣的花,一位台灣的貴太太。真的吃伊勿落?老范的鬥志被燃起了。老話一句,天下的花都待蜜蜂來採,這位也不會例外。
小杜被老范的眼睛,看得調轉了頭,臉微紅。這個老男人。她發現自己也像那些上海阿姨一樣,啐罵著,又高興著。
但是小杜沒有接受老范的邀請,進舞廳去跳上一曲。交誼舞可以不貼著身,手總要給人握著吧,另一隻手也能藉機在後背上做功夫。再說了,今天的鞋子不對,而且,那個舞廳有點怪。
老范天天下午到文化中心報到,每跳幾支舞,都要去外頭繞繞。那個台灣太太卻消失了。他對小李和小陳兩個學生,還是殷勤有禮,但是他自己卻感覺不到花的香、蜜的甜了。這天跳完舞,小李提議去隔街的港式飲茶喝下午茶,那裡是他們以前常去的地方,兩碟點心,一壺龍井,可以坐上半天。他託言有事要先走。小陳在旁說,不如明天去喝咖啡,有家台灣人開的咖啡館,情調蠻好,還有一種紅豆鬆餅,味道不要太好噢。他也搖頭。他像個紳士般欠身,說還是改天請兩位到我那裡坐坐吧。小李小陳微笑,再約吧。她們都喜歡去老范那裡,想著要怎麼擺脫另一個,得到老范所有的關注。
老范走在馬路上,有點百無聊賴。突然一陣香風吹來,飄來一句軟甜的台灣國語:「范老師,你好。」怎麼有人到了這年紀,講話還這麼嗲聲嗲氣?老范擺出嚴肅帶著一絲悲傷的面孔,對著眼前的這張笑臉。
「不記得我了?」小杜笑。
「怎麼會不記得?」老范說,「小杜,你這幾天都到哪兒去了?」
「哎呀,我這幾天倒楣了,全球股市大跌……」小杜住了口,沒必要跟他說這些吧?雖然覺得這個人挺有趣。
「你也炒股?」老范說,「我曉得幾支牛股,可以給你作參考。」老范不炒股,但要吹出一套股經卻是輕而易舉。
兩人邊走邊聊,不知不覺走到了老范的小區前。「我就住這兒,要不要上來坐坐,我有很多上海的老照片。」
「你一個人?」
「吾和一隻貓同居。」
「今天不行。」小杜說,「我還有事。」
老范再加把勁兒,表達自己的關心,「炒股要當心,一套牢,菜錢都沒了。」
「沒事的,我先生拿了五百萬給我玩玩……」小杜話一出口,便覺失言。這句話她常跟朋友們講,大家都被股市套牢,笑鬧慣了。
老范臉上還笑,但眼睛裡閃過一絲絕望,他不再殷殷望著小杜,好像要用眼光把她圈住,而是很快地揮手道聲再會,轉身進小區了。他移動起來像隻貓,悄然無聲。
小杜五百萬的玩笑話,把老范嚇醒了。乖乖隆地咚,他老范是吃飽了撐著,去招惹一個這樣的貴太太。恐怕連請她吃飯的錢都拿不出來。他想到十幾年前見識過的一個台灣太太。
十幾年前,那時上海跟現在可不一樣,百廢待舉,他正忙著重拾舞藝。有一回老同事們在上海最有名的海鮮樓吃飯,反正是單位開銷,大家放開肚皮吃,尤其是大閘蟹。大閘蟹人人愛吃,那時價錢還沒漲到現在這樣。總之,上海的一些好東西,大閘蟹也好,房子也罷,都被台灣香港人炒得比天高。十幾年前,一人兩隻大閘蟹,就吃得齒頰留香心滿意足,可以跟別人誇耀了。突見兩個侍者伺候著一個貴太太走來,貴太太一坐下開口就要了六公六母一打大閘蟹。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她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一刻鐘後,大蒸籠來了兩個,侍者開籠,裡頭伏著一公一母兩隻橙紅紅的大閘蟹,貴太太伸手拿來,螯腳一一折斷放在一旁,兩手一扳剝開蟹背,低頭一門心思舔吮膏黃。兩籠吃畢又來兩籠。如此這般,六籠十二隻大閘蟹膏盡黃乾,肉都啖光,蟹腳打包帶走。貴夫人走後,大家趁著幾分酒意,喚來侍者,侍者說此人每到此節,就從台灣飛來吃大閘蟹,一吃就十隻一打,蟹腳不及吃,帶回當點心,真是個蟹痴。
當時大家都搖頭冷笑,台灣人就是巴,大閘蟹要細細品嘗,狼吞虎嚥無異焚琴煮鶴。他太了解這種嗤笑了。在那個大多數人都捉襟見肘,靠著單位才能出去打牙祭的年代,這種不為擺譜只為自己喜歡的豪奢吃法,對大家造成多大的震撼,多大的威脅。這成了老范常講的故事之一。他老范也嚮往這種豪奢。如果可能,他也要盡情享用所有對他有情而他也有意的女人。一般人只吃一、兩隻,有的人可以一口氣吃一打。
可是現在,他想到這個狂啖大閘蟹的台灣女人,卻覺得說不出的鬱悶了。回到小屋,每天下午必有的點心咖啡,也無心調弄。白底黑紋的咪咪,臥在窗台邊,冷冷看著他發愁。咪咪,來,咪咪?連貓都不理他。他是個沒人要的孤老頭啊!老范把頭抵在靠窗的小圓桌上,往日的豪情銳氣都消散了。七十四了,還能花多久?他自怨自艾。
小杜的樣子清晰萬分地浮現眼前:雙排扣復古式米色風衣多麼合宜,說話時鬈髮在臉邊輕晃多少風情,她的眼睛因懷疑而生動,表情因冷淡而有魅力,小腿勻稱修長,穿著那雙美麗的短皮靴,顯得腳步輕盈。他要讓這樣的一個女人為他動心。
約她出去。去哪裡?老范不愧是老克拉,知道西餐這種噱頭,對台灣太太不起作用,人家搞不好天天吃西餐。泡高級咖啡館?他懂行情,一小杯咖啡就要五十元,還不能單請咖啡。上舞廳,那也要高檔如百樂門吧?那裡哪能隨便進去,一不小心就被扒一層皮。送禮物?那些手機鍊條、真絲巾、小荷包之類的,送送小李小陳還行,拿來送她,不讓人笑他小兒科?想來想去,還是請到自己的小屋來。他的小屋有情調,又實惠,進可攻退可守。
老范在那裡傷透腦筋,卻不知小杜的心思。其實小杜先後嫁的兩個男人,年紀都比她大得多,她比別的熟女更看得出老范是個寶。經過歲月洗滌渲染的成色,辛辣成熟卻又脆弱天真,隨時準備拜倒在石榴裙下,奉上一顆熱騰騰的心,卻又發乎情止乎禮,自嘲自謔總能化解尷尬。這樣的男伴,還真的可遇不可求。
小杜沒有多給老范一個微笑、一個眼風是有原因的。倒不是顧忌老公。老公除了生意,什麼都做不了了。有時她覺得,老公只是帶著她出門充充門面,就像讓她陪著躺在床上做做樣子。她考慮的是,這是個上海男人。她不知道這個上海老男人,會不會有什麼目的?除了她這個人以外的目的。
老范小杜的第三回合交鋒,發生在書報攤前。老范不買報,每天早上到街口的書報攤翻翻《東方晨報》,傍晚再翻翻《新民晚報》,上海大小新聞翻不出他的手掌心,這全靠跟賣報阿姨的交情。這天傍晚,老范正翻著報,聽到了那軟軟甜甜的台灣國語:「《新周刊》有嗎?」
可不是她嗎?老范喜出望外。小杜也看到他了,「這麼巧。」
「我就想著,也沒有你電話,天涯海角去哪裡尋人?」他語氣誇張地說。
「范老師找我?」小杜忍著笑。
「對,我要過生日了,請你來吃蛋糕。」
「我……」看著眼前這張笑臉,小杜一時不知如何拒絕。這個人到底想做什麼?總不會真要追求她吧?她的結婚鑽戒好端端亮閃閃戴在指頭上。手機叮噹響一聲,教她跳舞的老師發來短信,說要暫停上課,因為最近有參賽的同學需要加緊練習。小杜心一沉。
「小杜,怎麼樣,能賞光嗎?」
「好吧,在哪裡?」
「我住的小區你曉得的,三樓一室,星期五下午三點,一定要來。」老范說完就走,怕她改變心意。
一週裡的時光,老范最喜歡星期五,那是週末的開始,街上氣氛特別熱絡,人心特別自由。這是為什麼他約小杜星期五來。他把小屋收掇整潔,廁所裡換上雪白的新手巾,窗邊圓桌鋪上那條手織的白桌布,端出最寶貝的兩組咖啡杯,銀湯匙擦得雪亮。他穿上了最好的襯衫長褲,繫上一條花領巾,選了一張摩登舞曲,先就在屋裡轉起圈來。咖啡壺在爐上咕嚕嚕響,咪咪冷冷看著主人發痴。
時間到了,小杜沒有來。老范在窗邊望眼欲穿。不會被放白鴿了吧?台灣女人,他畢竟是吃不準。
三點一刻,小杜出現了。
小杜一進小區,就渾身不自在。她沒來過這種地方。危險嗎?可能。還繼續嗎?為什麼不。這幾天她心情惡劣。過去大半年來,每週都讓老師陪著練華爾茲,沒想到老師突然拋棄她了。是她自己堅持不肯參賽,老師為了賺學費拉抬知名度,替參賽學生護陣也是無可厚非。但小杜就是揮不去那種被棄的感覺。是她投入太多了?還是他太無情?
她自然倒向了另一個張開雙臂的有情人。她是不是太大膽了?根本不知男人的底細(怕什麼,難道這個老男人還能勉強她? ) 不過是萍水相逢,她沒準備出牆,也不會跟這種人出牆(好就好在萍水相逢,都五十幾了,還在等什麼?)
老范在窗邊看見小杜走過來,心開始急跳(是兩年前裝的心律調整計故障了?)。這可是他老范證明自己男性魅力的終極考驗。如果這個女人走出他小屋,還是原來的那個女人,他就要認分服老了。
小杜一進門,老范心就定了,因為她笑的樣子看起來不一樣了,帶點嬌腆,肢體動作也變得比較嫵媚自覺,這細微的變化只有像他這種老薑才能辨識。精神一振,老范恢復了原有的瀟灑風度,讓小杜在圓桌前落坐,端出蛋糕,倒了咖啡。
小杜拿出禮物,是一個巴掌大的石頭。「這尊石頭叫雙人探戈,像不像?」
老范接過來。這是那個奇石展裡的東西嗎?她肯定被宰了。這個世道,石頭都成了寶貝。他雙手捧著,點頭,「靈啊,老靈啊,謝謝儂噢,看來小杜也喜歡跳舞。」
老范說著文化中心跳舞的事,開自己玩笑,然後說了些滄海桑田的往事。他估量過,老上海的繁華不如老上海的滄桑讓台灣太太感興趣。然而,陳年往事在這斗室裡聽來遙不可及,小杜啜著咖啡,打量這狹小的客廳。這人也真能吹,她還以為這裡會是陋巷華屋,別有洞天,但她看到的只是一個老房子,一些舊東西。咖啡有點煮過頭了,蛋糕裹著厚厚一層奶油。今天不該來的。原先在這人的殷勤中得到滿足,現在只覺多餘。為了禮貌,她努力表現出興趣,在適當的時候蹙眉或微笑,並尋覓告辭的良機。
終於老范不說話了。他往椅背上靠,笑吟吟看著她。那是雙會勾人的眼睛,她避開那眼光。小杜現在很確定自己的方向。
此時,探戈舞曲響起,一掃斗室的懨懨之氣,那分明的鼓點,好像在催促著什麼。老范起身邀舞,她略一猶疑便伸出手。空間很小,他們在這小空間裡作小的蟹行貓步,作小的迴旋,停頓,擺頭,後仰。老范很會帶領,暗示動作明顯,即使她久不跳,也能跟隨。小杜逐漸放鬆了,開始感覺到那種來自老男人的安全感,沾在男人身上的咖啡餘香,混著古龍水的味道,老舊的櫥櫃,牆上泛黃的照片,褪色的沙發布罩,沙發上好整以暇舔著腳掌的貓,整個氛圍讓人像要跌進迢迢的過去。
舞入了第二曲,是她知道的老歌,白光的秋夜。沙啞的歌聲,非常老派。我愛夜,我愛夜,更愛那皓月高掛的秋夜(她停頓,她轉頭),幾株不知名的樹,已落下了黃葉(她看到秋風緊吹,梧桐凋零),只有那兩三片,那麼可憐在枝上抖怯(以為要往那裡去,誰知轉向這邊來,所有思量都不見),它們等著秋來到,要與世間離別(兩片,兩片黃葉緊緊巴住枝幹不願落下,不願落下啊!)她巴緊老范,老范巴緊她,他們要叫停時光……一曲舞畢,老范讓她朝後仰倒。她朝後看,朝後看,整個世界顛倒了,停頓了。老范將她抱起,吻住她的唇。
這吻來得意外,卻也沒那麼意外。那是個很紳士的吻,輕輕壓在她唇上。老范抱住她的腰,她感到力氣被慢慢抽掉,身體有點軟。第二個吻就來真的了,老范有著異常靈活的唇與舌,汨汨汲取如蜂直探花心。
長長的熱吻後,老范沒有下一步動作,讓她頭靠著自己的肩依偎著。小杜乖順地伏在他肩頭,軟綿綿像喝醉酒,等到清醒時四周悄然,唱片已經轉完。老范不說她也知道,這個老鬼,早就不舉了,卻又偏來招惹她。小杜抬起頭來,眼眶裡充滿淚水。
這要命的雙人探戈。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99年小說選的圖書 |
 |
99年小說選 出版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4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4 |
現代小說 |
$ 284 |
文學作品 |
$ 284 |
中文現代文學 |
$ 317 |
中文書 |
$ 317 |
小說 |
$ 324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99年小說選
主編郭強生認為二○一○年是名家以一貫的大河歷史敘述,多重引伸種種幽微的生命跡象;而新秀則有如雨後春筍般,遍地繁盛開花的年代。
因此他以最獨特的眼光,重新審視名家、新秀之作,撈捕到十五篇發出神奇光輝的美麗作品。計有李永平、李渝、蔣曉雲、黎紫書、章緣、黃靜泉等名家精采、動人小說,以及戴玉珍、周丹穎、王冠雅、林佑軒、黃麗群、葉揚、葉佳怡、黃汶瑄等各大文學獎新秀作品。
本屆「年度小說獎」由李永平的作品〈大河盡頭〉榮獲殊榮。
書末附錄年度小說紀事,為整年的文學歷史作詳細記錄。
◆ 李永平〈大河盡頭〉獲年度小說獎!
◆ 郭強生精選二○一○年最精彩的小說作品,精華薈萃,篇篇動人,讀一本等於讀遍全年最好的小說。
◆ 選入李渝、李永平、蔣曉雲、黎紫書等名家以及黃麗群、葉佳怡、林佑軒等文學獎新人,譜寫最美麗的文學盛宴。
作者簡介:
郭強生主編
評論家、學者、劇場編導、小說家,現為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曾獲多次重要文學獎項,並多次入選「年度散文選」、「年度小說選」、《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等重要選集。其中《非關男女》獲「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給我一顆星》獲「文建會劇本創作首獎」。著有《夜行之子》、《在文學徬徨的年代》、《我是我自己的新郎》等二十餘部。
章節試閱
◆雙人探戈
作者/ 章 緣
本名張惠媛,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紐約大學表演文化研究所碩士。旅居美國多年,二○○四年後移居中國大陸。曾獲《聯合文學》小說獎、《聯合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等。作品入選爾雅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中副小說精選、台灣筆會文集、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九歌九十四年小說選等。著有短篇小說合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擦肩而過》、《越界》,長篇小說《疫》,隨筆《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
老范的日腳,本不會跟台灣太太有搭界的。
井...
作者/ 章 緣
本名張惠媛,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紐約大學表演文化研究所碩士。旅居美國多年,二○○四年後移居中國大陸。曾獲《聯合文學》小說獎、《聯合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等。作品入選爾雅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中副小說精選、台灣筆會文集、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九歌九十四年小說選等。著有短篇小說合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擦肩而過》、《越界》,長篇小說《疫》,隨筆《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
老范的日腳,本不會跟台灣太太有搭界的。
井...
»看全部
作者序
華文閱讀的新版圖
文/ 郭強生
還是就先從寫小說這事說起吧!
小說實驗、創新、突破……這些詞我們聽了多少年了,到底什麼是突破創新呢?在我看來,根本沒所謂突破創新的問題。每個寫作者的生命歷程、思緒性格、品格教養、身心狀況……都是如此不同,只要是真誠表現自己的情感,專注在個人生命的完成與反省,哪可能是有任何範例可套用?哪一個寫作者不是在創新突破?(如果,他是真的被生命這檔事感動到非寫不可的話,我是說。)
偏偏有太多的作者與評論者喜歡搬出「實驗、創新、突破」的大帽子。話又說回來,在過去二十年,台灣小說好...
文/ 郭強生
還是就先從寫小說這事說起吧!
小說實驗、創新、突破……這些詞我們聽了多少年了,到底什麼是突破創新呢?在我看來,根本沒所謂突破創新的問題。每個寫作者的生命歷程、思緒性格、品格教養、身心狀況……都是如此不同,只要是真誠表現自己的情感,專注在個人生命的完成與反省,哪可能是有任何範例可套用?哪一個寫作者不是在創新突破?(如果,他是真的被生命這檔事感動到非寫不可的話,我是說。)
偏偏有太多的作者與評論者喜歡搬出「實驗、創新、突破」的大帽子。話又說回來,在過去二十年,台灣小說好...
»看全部
目錄
郭強生 華文閱讀的新版圖 ......009
章 緣 雙人探戈 ......019
葉盈孜 街 ......035
周丹穎 漂流之家 ......047
李 渝 待 鶴 ......083
王冠雅 洗 禮 ......121
蔣曉雲 探 親(節錄) ......135
李永平 大河盡頭(節錄) ......171
林佑軒 女兒命 ......187
葉 揚 阿媽的事 ......201
黃靜泉 白棺材 ......217
戴玉珍 溪 砂 ......237
黎紫書 生活的全盤方式 ......255
黃麗群 卜算子 ......277
葉佳怡 窗 外 ......301
黃汶瑄 六...
章 緣 雙人探戈 ......019
葉盈孜 街 ......035
周丹穎 漂流之家 ......047
李 渝 待 鶴 ......083
王冠雅 洗 禮 ......121
蔣曉雲 探 親(節錄) ......135
李永平 大河盡頭(節錄) ......171
林佑軒 女兒命 ......187
葉 揚 阿媽的事 ......201
黃靜泉 白棺材 ......217
戴玉珍 溪 砂 ......237
黎紫書 生活的全盤方式 ......255
黃麗群 卜算子 ......277
葉佳怡 窗 外 ......301
黃汶瑄 六...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3-01 ISBN/ISSN:978957444757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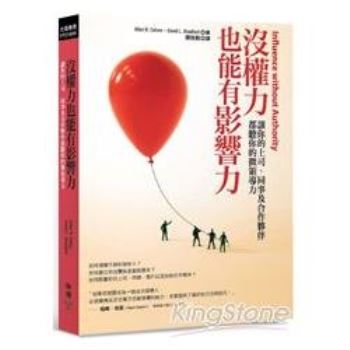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