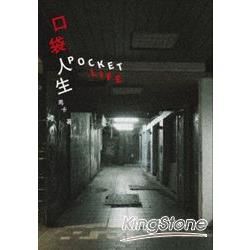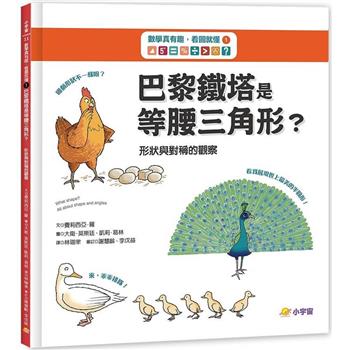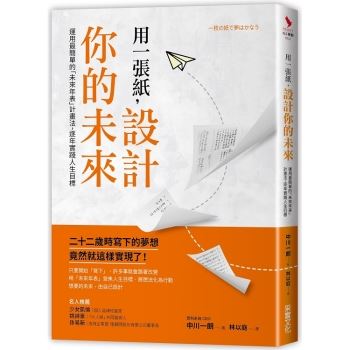名人推薦:
名家推薦
小說家、導演 小野:
這是一本讓讀者讀起來感到很矛盾的小說。作者透過小說中的人物的獨白常常諷刺這個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所欺騙的虛偽荒謬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其實是:「上帝是一隻狗,牠一放屁就形成了一個世界,也因此我們的世界是臭的。」小說中的人物非常討厭那些經常說著人生大道理的衛道人士,或是宣揚人生光明面的傳道者,可是他們自己也不停說著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而且說得理直氣壯。
小說中的人物很討厭自以為知識淵博滿腹經綸的人,可是小說中卻又不斷提到一些世界級的大作家的作品,卡繆的《異鄉人》、巴爾札克的《驢皮記》、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馮內果的《貓的搖籃》、《第五號屠宰場》、卡夫卡的《蛻變》、紀德的《偽幣制造者》、毛姆的《人性的枷鎖》、果戈里的《死靈魂》。彷彿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愛讀書的文化人。這就我說的矛盾,甚至有點矯情。
我就是在這樣抱著負面的、不以為然的、懷疑的心情下往下閱讀這本小說。漸漸的我感受到這本小說不是寫實主義的,它是超現實的,是表現主義的,是象徵主義的。這樣解讀後所有的懷疑都轉化成了好奇往下閱讀。如果這本小說轉換成影像的話,它應該是用高對比的光線來烘托整部作品那種怪誕荒涼的氣氛,它不會有太多的長鏡頭,它會用大特寫逼迫我們去聞聞那些死亡後的屍臭,或是自殺後人體流出的骯髒東西,或是被切得見骨的傷口裡的蒼蠅的幼蟲,是的,作者連處理死亡的狀態都用了許多慘不忍睹的畫面,讓死亡都是那種飽受凌虐後的不得好死。
有人問蔡明亮說為什麼他的電影總是那麼絕望陰慘荒蕪,他的回答好像是說唯有讓作品呈現出人類可能面對最絕望的真實後,才能了解光明和希望。他說他的作品其實是積極光明的。
或許,這部小說想呈現的東西也是這樣吧。不過這樣說,似乎又在講大道理了。
小說家、名主編 季季:
書名契合結構,每一小節都像個口袋,裝著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故事,以及探到口袋深處都不一定看得清楚的人性糾結。
這些口袋大小各異,作者藉一個年輕女子遇難三個年輕男子涉嫌的弔詭,像電影分鏡般一幕幕展開故事。主場景在臺北「卡繆咖啡館」及其樓上的小套房,延伸場景則遠至中國大陸與歐洲、非洲;探討主題是死刑存廢,延伸議題則包括殘障與人道,跨國企業與貧窮、暴力,性向與謊言,文化美容與文學經典,以及外遇、賣淫、政治等等。多重階級與多重文化論述不斷碰觸交錯,可讀性高,但部分議題與論述超重,展現作者以小搏大的意圖,似也有意挑戰讀者的眼力與耐力。
小說家、出版家 陳雨航:
企圖很大,討論人類生存、道德、性、罪惡等問題,提出許多可思考的角度。對人們固定思考以及成見等也有針砭意圖。
有當代社會的戲劇性情節,聳慄的、前端的思想作為,還有寬廣的時間和場景︵從臺灣到非洲︶,展現了作者說故事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常用西方︵少數東方︶名作小說加以點評,這些看法不囿於定見,令人莞爾。
是一部西洋式的中文小說。
「九歌二○○萬小說獎」總評
不爽症—看見臺中,也看見臺灣 季 季
一部怎樣的小說,值得獎金二○○萬台幣的獎勵?
所有的文學愛好者或研究者,可能都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最可貴的文學本質是創作,從來沒有統一的標準。即使文學獎設有反覆討論與多次投票的機制,最後得出的也只是最大公約數的結果;未必能讓所有人滿意,也未必所有人都不滿意。每位評審委員的文學素養不同,品味、見解各異,自然會出現偏愛與偏見的落差;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世代,這個現象同樣存在。至於獲獎者及其作品,能否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那是文學獎結束之後的另一個問題。
創下同類文學獎最高獎金的世界紀錄
如果純以獎金而論,歷史悠久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最高(一百四十六萬美元),惟其性質較偏重累積性成就。名家如托爾斯泰、易卜生、波赫士等人卻都沒得過該獎,可見院士級評審也一樣有所偏見與偏愛。
至於獎勵單部小說的文學獎,目前以都柏林市政府一九九六年創辦的「都柏林IMPC文學獎」獎金最高(十萬歐元,約四百一十萬台幣)。英國曼布克獎也備受矚目(五萬六千英鎊,約二百六十八萬台幣)。一九○三年設立的法國龔固爾獎,獎金僅五十法朗(目前為十歐元);與龔固爾獎聲望相當的費米娜獎甚至沒有獎金,但二獎均地位崇高。美國的福克納文學獎,獎金一萬五千美元;國家書卷獎一萬美元;普立茲獎七千五百美元。日本的芥川獎與直木獎,獎金均為一百萬日幣(約三十五萬台幣)。中國大陸的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老舍文學獎,近年獎金均提升至五萬人民幣。二○○六年開始頒發的香港「紅樓夢獎」,獎金三十萬港幣。二○○七年開始頒發的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獎金一百萬台幣…。以上這些獎,都是為了獎勵已出版或已發表的作品,獲獎的最大效益是作家聲望與作品銷售量的提升;其延伸效益往往比獎金效益更為可觀。
在全球著名的文學獎中,僅有一九七五年設立的「海明威獎」是獎勵尚未發表的作品,獎金七千五百美元。「九歌二○○萬小說獎」性質與「海明威獎」相同,但獎金高出八倍以上,創下同類文學獎獎金最高的世界紀錄。可惜,它只頒發一屆。
獎金的光芒,迷失了部分寫作者的初衷
「九歌二○○萬小說獎」,是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先生為了慶祝該社成立三十年而創辦。因為獎金高且只頒發一屆,二○○七年一月宣布徵文辦法就備受全球華文寫作者矚目,二○○八年三月截稿共收到二百一十二部參賽作品。但公佈徵文至截稿時間僅一年多,參賽作品水準參差,那一次的決審委員決定「首獎從缺」。蔡先生對此結果深感遺憾,立即宣布再次徵文,於二○一○年六月截稿,收到一百五十六部參賽作品,十三部進入決審。我們五個決審委員(小野、施淑、陳雨航、彭小妍與我)因而備覺責任重大,去年十一月中旬收到作品至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決審會議,兩個多月裡埋首「苦讀」了十三部作品近兩百萬字。
閱讀的樂趣之一是自由。已出版的長篇大多經過編輯把關,我們讀不下去可跳過幾頁或束諸高閣;對於未發表的長篇,我們卻無法享有這樣的自由。評審的先期責任是被作品裡的每一個字綁架;必須耐心且細心的貼身於字裡行間,才能讀出其中的優缺點,同時作些筆記註解重點。
那兩個多月的「苦讀」,我時常陷入「這是哪一國文學?」的困惑。「全球化」大浪不斷推擠,年輕的作者們跟著虛擬浩瀚的網路流行,寫了不少以外國人名為主角,看起來像西方小說,但人物與背景又曖昧不明。也許他們想跟隨「文學全球化」的腳步,卻首先失去了中文小說創作的「文學主體性」。
同時,我也感受到「二○○萬」獎金的光芒,似乎使得部分參賽者迷失了寫作的初心。為了角逐這項高獎金的榮耀,他們確實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的汲取西方暢銷小說的模式,或是大量編造離奇荒誕的故事情節,以為添加麻辣就能出奇制勝。有兩位作者把故事場景設在倫敦的精神病院;有一位則拉到北愛戰爭,從倖存的反抗軍後代寫到性侵、逃亡、亂倫與精神錯亂;有一位甚至把國共內戰期間周恩來的諜報員如何在重慶滲透到蔣介石身邊,寫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又如何滲透到台灣的蔣介石身邊…。大時代、大主題、大事件、大場景,著墨如此之重,格局似乎不小,然而,它們都落選了;因為這些作者不止迷失寫作的初心,也和其他落選的作者一樣,都有寫作基本功不足的問題。除了最普遍的多不勝數的錯別字,還包括敘述情節與時代背景不符合邏輯,而且無法觀照全面,常出現小說人物的名字或身分前後不一等缺失。他們確實很會編故事,但故事在小說裡只像人身的骨架,如果沒有細密的血肉鋪陳,小說的生命就顯得薄弱且乾澀,突兀而索然。另外,敘述文字與人物對白沒有區隔,有些敘述文字甚至平鋪直敘猶說明文,缺乏小說語言的節奏與層次;這也是網路世代寫手的普遍問題。
字數與內容的高難度考驗
一部長篇應該多少字並無準則,從十萬至五六十萬不等,隨各人才情與題材而異。九歌這項徵文,字數雖只限十~十五萬字,對部分寫作者仍是高難度的考驗。他們原先構想的故事骨架也許只是五六萬字的規模,為了達到徵文規定的字數,只好以AB對照組或上下兩部曲的方式編造更多荒誕的情節,並且賣弄許多從網路移植來的偽知識、偽理論;好像作者本人無所不知,而其筆下人物都是理論大師,使得這些拼貼或混搭的小說好像灌了水;虛胖,鬆垮,蛇足,四處都有閱讀障礙。最後入圍前四名的徐嘉澤《詐騙家族》、周立書《口袋人生》、陳栢青《小城市》,也和其他未入圍作品一樣,多少都有類似問題。我們五個委員在決審會議時已分別就此提出意見,請主辦單位建議作者刪改補強。日後出版時,相信將更精練可讀。
首獎作者張經宏,謙卑一如勤勞的「拾穗者」
說了這麼多的「烏鴉心得」,重點來到獲得首獎的《摩鐵路之城》。作者張經宏今年四十二歲,是台中一中國文老師,近年連得時報小說首獎,高雄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葉石濤紀念獎」,倪匡科幻小說首獎;寫作經歷不算短,作品不多但成績可觀。最難得的是他不為流行所迷,至今保有樸實的寫作初心,始終默默的沉穩寫作,才能把《摩鐵路之城》經營得結構明晰,文字、層次疏密有致,敘述邏輯與敘述觀點也緊密交織,情節前後契合而形式完整;沒有前述幾部那些缺點。更可貴的是他不好高騖遠,謙卑一如勤勞的「拾穗者」,低頭俯拾腳下行過的生活素材,使得全書的小說語言能夠精準反映當下年輕人的詞彙,也能貼近一般庶民的用語。
《摩鐵路之城》的故事背景在二○一○年的臺中市。這個早年被稱為「文化城」的都會,原本以綠川垂柳、中央書局及楊逵的東海花園知名,近數年竟演變為以黑道拚鬥、夜店大火與汽車旅館名震全台。小說的主角吳季倫,從沒見過母親,九歲時父親又因車禍去世,從小由經營雜貨店的伯父母照顧成長。高二下不想再上學後,他搬離疼愛他的伯父家自謀生活,先後在餐廳與汽車旅館打工。全書以單一觀點敘述,從吳季倫的十七歲眼光掃瞄他周遭的一切動靜;小說起首之句即以象徵性語言切入汽車旅館的場景:
我一直很想打噴嚏,只是很想。從傍晚開始,在我頭頂上方的每一朵雲擠在另一朵身上,一起窺看它們底下的這個地方,幾萬樁同時在進行的不可告人的鳥事。…
這家汽車旅館佈置精緻,有假山、瀑布,「二十幾幢房間就藏在彎彎曲曲的庭園造景後面」,噴泉四周還有桂花小徑,草坪上映照著石燈籠光影。「我」每晚安排好那些「好像打算來這裡辦一場雙修法會」的男女後,最喜歡的事情是得空在庭園裡散步:
這大概是我一天心情最平靜的時候,那種安靜讓我有辦法想點比較深刻的什麼,關於大人們常掛在嘴邊的未來、夢想,以及作為一個人是怎麼回事的問題。這些在白天的學校裡從來沒出現過的,居然在這個每扇房門後面充滿交配氣味的鬼地方,讓我跟這些問題碰到面,說來還真有點不可思議。…
至於那個讓他讀不下去的學校,吳季倫是這樣自我調侃的:
那個鬼地方的一切讓我覺得虛透了…。也許過不了多久,會有專業醫生給這種症狀下一個清楚的病名:『不爽症』,而這個病症被記載下來的第一個案例,就是我。…
張經宏採取穩健的寫實手法,讓現實與回憶這兩條主線穿插無數支線,藉著學校(教育),餐廳(食慾),汽車旅館(情慾)等場景,描摩了吳季倫及其同齡層的少年浮動,以及臺中這個城市被黑道、色情蔓延的複雜身世。由於在學校任教,他對校園氣氛、學生行為、老師與家長言行的觀察格外細膩,敘述的語氣也特別活潑生猛且富幽默感。在吳季倫的眼中,同學是「鳥蛋」,老師是「龜蛋」;以下這段對「龜蛋」的描述尤為傳神:
最常找我麻煩的是個比我矮了一個頭,滿臉痘痘,三十幾歲的女龜蛋。她教國文,我們班導。如果你上過她的課,你就知道為什麼我會討厭上學,聽說她還是學校的紅牌。高一課本剛好選到一篇小說,就是那個憨孫買了一條魚要回家孝順阿公,結果半路上魚掉了,祖孫兩個吵到快要打起來的故事。女龜蛋先是自言自語,這對祖孫在幹嘛,一條魚有什麼好吵的,如果是一頭牛不就要拿刀互砍。更天真的是她說這故事在提醒我們,東西寄送回家要找一家好一點的宅配公司,又花不了多少錢,不然搞砸了就會吵個沒完沒了。…
這位女老師還拿出一疊寫了五十種魚名的講義要學生注音,修辭,連成語等等;為省篇幅不多贅述,只希望寫〈魚〉的黃春明看了以上這段不要生氣,會心一笑就好。—原來我們的文學作品,是這樣被國文老師導讀的;但願全國只有一個這樣的老師。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島嶼浮世繪
小說的尾聲是旅館老闆要出來選市議員,突然發現吳季倫未滿十八歲,惟恐這個違法事實成為競選對手攻擊的目標,立刻請他轉移陣地去餐廳做服務生。在汽車旅館只工作三個月的吳季倫,在餐廳的油膩吵雜裡仍然懷抱著一個遙遠的夢想:
也許有天我會買下一間有庭園造景的汽車旅館,打算把它改建成氣質出眾的聊天學校…。
他希望這個聊天學校,能讓苦悶或者迷惘的人在那裡得到紓解。這個自我救贖的主題,和《麥田捕手》裡的中輟生霍頓的夢想遙相呼應:
有一群小孩在麥田裡遊戲…,除了我以外沒有其他大人。我就站在懸崖邊,守望這群孩子,如果有哪個頑皮的孩子跑到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孩子們都喜歡狂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往哪裡跑,我必須適時捉住他們,我只想當麥田裡的捕手。
教育,黑道,色情,並非新鮮課題,任何城市都有,只是問題輕重有別。《摩鐵路之城》是張經宏向《麥田捕手》作者沙林傑致敬的作品,所描摹的背景雖是臺中市,卻也浮顯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島嶼浮世繪,讓我們看見臺中也看見臺灣。而心裡存著「不爽症」的少年吳季倫,其實也是當下許多徬徨少年的縮影;他們的內心在不爽之中一定也懷抱著一個自我救贖的夢想。
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