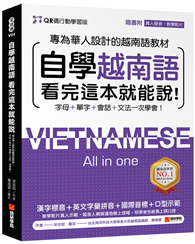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 九歌200萬小說獎首獎得主張經宏精彩短篇小說結集。
◇ 收錄11篇不同主題小說,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倪匡科幻獎等得獎作品,展現小說多元而迷人的閱讀深度。
宛如小說魔法師般,張經宏以樸實簡單的文字,揮灑魔幻寫實、虛擬情境等小說技法,或溫馨嘲弄,或悲憫傷懷,直探生命的真實,檢視生存的困境與迷惑。
以食物為題材,〈早餐〉中配料簡單,卻讓人鼻頭發酸的飯糰;記憶是虛構還是寫實,為什麼〈蛋糕的滋味〉回想起來卻不再甜蜜。從城鄉到都會,寫台灣老阿嬤的〈壁虎〉,斑斕神祕的民間信仰中掩映出老人內在的孤寂,而〈吉屋出售〉則以生動的語言展現市井小民充沛的生命力。從寫實到科幻,〈出不來的遊戲〉在虛擬中真實點出現代人的沉迷與逃避。
閱讀張經宏的小說,看見小說的無限可能,鄉土與神祕、傳奇與寫實,每一篇精彩的故事,都是現代人生活的實境。
作者簡介:
張經宏
生於1969年,台中人,台大哲學系畢業,台大中文所碩士,現任職台中一中。曾獲教育部文藝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倪匡科幻小說首獎等。並以《摩鐵路之城》獲九歌200萬小說獎首獎。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家小野、甘耀明、林文義、季季、郝譽翔、陳雨航聯合推薦
【推薦序】驀然回首的人生碎光 甘耀明
小說家對一座都市最大的敬意,是徹底地奪取她的貞操,而後公布過程。這也可換算成女性主義的說法,徹底奪取他的童貞而後張揚。當然,小說家不是真的幹了此事,而是有能力穿透人慾表層──看似貞操與童真的扭捏表象──直抵人情糾葛的暗潮,然後張揚出來。關於繁縟無比的人際摩擦,莫過於都市,人們處處留下了痕跡。小說家永遠是最後抵達與離開現場的人,卻以有別於記者、法官、道德家、宗教家的專業態度,還原過程,其細膩的描述手法與內容,好像他早已預知此事。
面對台中市的貞操與童真,台灣的小說家們太客氣了,他們花較多的時間與力氣在台北市或高雄市。偉大的城市,必然有深厚的小說對應。台中生活圈有值得書寫的小說題材,但是作品不多,這跟現代台灣文化發展與地方政府的態度有關。所以,張經宏拿下九歌兩百萬小說獎的《摩鐵路之城》,乃是對台中最大的敬意。文學不該以地域分優劣,或是捐棄。但是,對於我居住十餘年的都市而言,《摩鐵路之城》中描述的台中市光景,引燃了我未來對此城書寫的熱情。
《出不來的遊戲》並非張經宏新作,是多年來短篇小說寫作的集結,屬《摩鐵路之城》的「前傳」。這本書與《摩鐵路之城》的劇情沒糾葛。然而,所謂「前傳」,是通過這些作品的鍛鍊,張經宏逐漸提升小說技巧與火候,鋪出了一條通往「摩鐵路之城」的道路。此書無論在筆法、題材與類型多元,是張經宏多年來磨筆的砥礪石。在無法探知作者情意之下,我只能就「同行者」的身分感受:砥礪而產生的鋼鐵般火花,明滅有時,孤獨時常,但是唯有透過火花的照亮,暫時指引,才能穿過「少作」的荊棘之路。
與刺探《摩鐵路之城》的升學教育與青少年教養所使用的旁觀筆法,《出不來的遊戲》給我較多閱讀上的溫度。從母子之情〈早餐〉、父子之情〈蛋糕的滋味〉與〈清秋〉、祖孫之情〈壁虎〉,甚至延伸到家族糾葛的〈澄清湖之旅〉、〈家庭訪問〉,張經宏不愧是寫小說的經驗老手,筆法簡約,餘韻無窮。他處理這些家庭關係的價值對抗或妥協,無論矛盾或無解,線路並不十分複雜,而且力道掐得六分,四分留予讀者冷暖自知。這是他的強項功夫。
這幾年來,台灣的文學獎繁多。台灣年輕作家的起步,幾乎是從短篇小說獎之路招搖的、沉重的、無感的拿著獎盃跑出來,即使不去討好評審,也常因為拗肘勒腿,好符合各樣的比賽場地與遊戲規則,屢屢限制自己拳法,失去完整的攻擊力。如何忽略《出不來的遊戲》沾染了「文學獎之惡」的氣息,似乎很難,甚至聯想到這是文學獎得獎的拳譜。然而,張經宏這幾年的短篇作品,不單是這本集子的篇數,《出不來的遊戲》絕對是他精挑細選的光芒之作。關於這些年輕的光芒作品,不單是鋼鐵般火花而照亮荊棘之路,也充滿了城市的人生碎光。
這碎光難免讓我想起,每當騎車從特三號道路或中港路下大度山時,夕陽在台中盆地的餘光爍返,有如高度蜜軟的雲夢大澤蜃影。閃爍光芒可能來自高樓窗光、不鏽鋼水塔、移動車輛或高鐵快速竄過的反光。過不久,夕陽消失,更黑更濃的夜讓整座城市的霓虹夜色大放光明。
光芒,來自每則餘暉、每盞夜燈,潛藏挫敗、糾纏或溫暖的故事,可能是此書〈吉屋出售〉那年輕的房屋仲介的溫良眸光;或是〈香蕉‧蜘蛛‧猴〉,鄉土魔幻般迷人且穿越歷史的香蕉葉澤光。現在,他們共存在這海島上最大的盆地內。這些驀然之碎光,刻意注視,長久等待,反而是等待果陀的戲碼,卻經常在不經意回首時瞥見。
目前隱居在台中大雅區的張經宏,住在自己蓋的磚房老厝,庭院種滿了各種植栽,屋外盈繞著稻葉反光,更遠的地方矗立家庭式的鐵皮工廠。他是土生土長台中人,對此城農業時代的前身,到工業、商業、建築業、特種行業的變形金剛階段,有最道地的體驗。他對此城市的陸續書寫,是對她的偉大敬意。猥瑣、不滿、讚許、幹譙、容忍與愛,都是與土地最好的對話。這是我期待張經宏書寫的原因,也很榮幸在此盆地與他相遇,更無比祝福他的新小說集出版了。
名人推薦:名家小野、甘耀明、林文義、季季、郝譽翔、陳雨航聯合推薦
【推薦序】驀然回首的人生碎光 甘耀明
小說家對一座都市最大的敬意,是徹底地奪取她的貞操,而後公布過程。這也可換算成女性主義的說法,徹底奪取他的童貞而後張揚。當然,小說家不是真的幹了此事,而是有能力穿透人慾表層──看似貞操與童真的扭捏表象──直抵人情糾葛的暗潮,然後張揚出來。關於繁縟無比的人際摩擦,莫過於都市,人們處處留下了痕跡。小說家永遠是最後抵達與離開現場的人,卻以有別於記者、法官、道德家、宗教家的專業態度,還原過程,其細膩的描...
章節試閱
早 餐
1
靠近學校外牆的那條街,我們叫它「早餐街」。從校門左側延伸過去的商家騎樓,起碼超過十家,每天早晨,總是擠滿學生與家長。其中包括我的媽媽。
漢堡、土司、炒麵,各種食物的氣味,飄散在早晨陽光的街道中,媽媽總是把車子停在這些攤子的對面,要我在車上等。
煎漢堡肉加洋蔥、烤土司的香氣,像在幫它們的老闆搶生意,一陣一陣撲到面前。
實在是人太多了,有一次老闆弄錯,排了將近二十分鐘,才買到一個漢堡加一杯奶茶,進校門已經遲到了。
媽媽向門口執勤的教官說明原因,教官看了我一眼,放我進去。
走進教室,同學已經在寫考卷。
導師走到我的座位前面,用尖尖的指甲敲了桌子兩下,叫我站起來:「你以後這麼晚來,就站到走廊上寫考卷。」
我一邊聞著抽屜裡漢堡肉加洋蔥的味道,一邊把那張數學考卷寫完。
鐘聲響起,那塊原先烤得熱烘烘的漢堡早就冷掉,潮潮黏黏,咬在嘴裡軟軟的,稠稠的番茄醬酸得牙根顫抖,整塊麵包就像超大塊酸鹹味道的口香糖。
回到家,老師已經打過電話來,媽媽也沒說什麼。
第二天,她比平常早叫醒我,開在路上的車子似乎沒睡飽,紅燈時老是壓到行人斑馬線。
跟別人家比起來,我們兩個都起得晚,媽媽沒有時間先買好早餐。我不喜歡吃冷掉的食物,蒸過的、微波過的,還有福利社的麵包與涼麵,我都不喜歡。
她有時問我,看到別人家的小孩在車上吃早餐,會不會羨慕?
「神經。」我繼續背我的英文單字。
一些單字拼錯了,illusion,少了一個L,她會笑我真偷懶,把一個L吃掉,或說,我的英文怎唸得那麼像日本人?或者說,怎麼沒看見我在背國文?然後車子就開到學校附近了。
有時候媽媽說,真的,早上叫了我好久,可就是喊不醒。她也不想這樣,實在每天工作到很晚,早上要那麼早爬起來,真是辛苦的事。
「可是,」我說:「妳送我來學校,回去就可以睡了啊。」
然後她就會說還要去買菜、聯絡客戶、批貨、送貨、收會錢,回家還要幫我摺棉被、洗衣服、燙衣服等等,到最後就說,要不然你自己起來上學好了。
「好啊。」
可是她從來沒讓我自己上學過。
有時我們比平常早一點到,那幾攤前面,擠滿買早餐的學生與家長。
車子再往前一點,有一攤的招牌,用紙箱背面寫著「阿婆飯糰」,掛在攤子前面,一個客人都沒有。為了節省時間,母親說:要不就買飯糰?
攤子後站著一位老婦人,動作很快,不用一分鐘,媽媽已經提著豆漿和飯糰,轉頭向車子這邊走來。
手中握著一顆棒球大小、感覺硬梆梆的米糰,實在沒有什麼食慾,有點想把它當棒球,從窗外丟出去。
吃吧。媽媽說,阿婆知道這是給我兒子的,還特地捏大顆一點,她捏的飯糰可是有五十年的功力喔。
第一口,幾乎都是米飯,有點硬,帶點花生油的香氣,嚼了幾下,嘴裡甜甜的,又咬一口,才吃到一些餡料。豆干粒、酸菜、肉鬆、油條、花生粉,普通的食材,在嘴裡像是好幾道菜的享受,才吃不到一半,車子已經開到校門口。
另一半,總是在早自習結束後,一邊抄同學的作業,一邊嚼完。
冷掉的飯糰,一樣好吃,沒有麵包冷掉後,像泡了水,口中糊成一片的噁心感。冷的米粒咬在嘴裡一樣有彈性,粒粒滋味分明,與配料搭配得恰到好處。
很奇怪,一粒比饅頭小的飯糰,彷彿有無窮的能量,一整個早上都不會餓。
同學們早餐吃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垃圾桶裡的紙盒,一看就知道是誰丟的。
下課時間,大家還會把早餐拿出來,一起分著吃。
那咬到一半的飯糰,還被同學消遣過。
「喂!誰要吃飯糰?吃了變飯桶的飯糰?」
沒有人要吃。
可能是飯糰被捏成一坨白白的米球,外面用一個小塑膠袋套住,看起來很俗吧。
中午,同學還會用吃剩下的團膳,把空心菜、肉屑加筍片捏成一球,大聲嚷:「飯糰王吃的」來取笑,然後當成棒球在教室裡丟來丟去,玩累了,就丟給校工養的小黃吃。小黃吃得津津有味。
他們又取笑說,學校裡跟我最像的,就是那隻小黃。
後來的早晨,當媽媽向飯糰攤子走近,阿婆的笑容跟聲音,立刻響亮地漾過街道:「早啊!」好像她就在坐在我旁邊,跟我說話。
有時揉捏飯糰的她,遠遠望向車子這邊。她是在對我笑吧。
媽媽每次買完走回來,都說阿婆告訴她,今天給的又比昨天的大。
「那今天是像柚子那樣?還是西瓜?」我會這樣笑她。
有一天,媽媽問,每天吃飯糰,會不會膩?
「哪有人過這麼久才問的。」
媽媽沒說什麼。她應該清楚,我的回答就是表示,我習慣這樣的早餐吧。至於喜不喜歡,我也說不上來。
她常笑我脾氣真怪。自己喜歡什麼不知道,不喜歡什麼倒是很清楚。
我們去買衣服、買鞋子,她習慣先問:「不喜歡嗎?」
要是沒有反應,就是可以買的意思。這樣子買東西,其實花不了太多時間。
每天早上,我都是用腳輕輕一踹,關上車門,背著書包,右手飯糰加豆漿,揮揮提著袋子的左手,跟母親說再見。
早 餐
1
靠近學校外牆的那條街,我們叫它「早餐街」。從校門左側延伸過去的商家騎樓,起碼超過十家,每天早晨,總是擠滿學生與家長。其中包括我的媽媽。
漢堡、土司、炒麵,各種食物的氣味,飄散在早晨陽光的街道中,媽媽總是把車子停在這些攤子的對面,要我在車上等。
煎漢堡肉加洋蔥、烤土司的香氣,像在幫它們的老闆搶生意,一陣一陣撲到面前。
實在是人太多了,有一次老闆弄錯,排了將近二十分鐘,才買到一個漢堡加一杯奶茶,進校門已經遲到了。
媽媽向門口執勤的教官說明原因,教官看了我一眼,放我進去。
走進教室,同學已經...
作者序
【後 記】
這是一部遲來的小說集。年輕時的我讀過文學科系,也曾想像有朝一日可以成為一個作家,但那時的我既困惑又孤獨,周遭認識若干跟我有著相似心靈品質的人,雖然這些人的生活態度少有讓我滿意,但在平庸的我的眼中,他們個個身懷絕學深藏不露,使我很樂意與他們結為朋友。有趣的是這些高人都沒什麼創作慾望,這使我在他們面前,只好乖乖放下自家的破掃帚,低頭拂掃腳邊的塵屑。
那幾年我認真地修了一堆奇怪、如今全無記憶的課,尷尬的是教室裡的知識無一能解決我心裡不斷滋生的疑慮。還算明白的是,如果那時我提筆寫作,要嘛大膽刨挖、牽拉些自己想的或四處找來的種種困惑,叫啊嚷地向世人宣告「我就是這樣的人」;要嘛裝成一個深思熟慮、看懂人生的斯文神棍。前者我不敢,後者我沒那本事,就這樣一路混到近四十歲,才斷斷續續吐露些不怎麼成熟的習作。
為什麼我會開始寫作?這得從六七年前的工作談起。彼時我剛進入一所公立中學服務,除了國文,我被指派任教「文學鑑賞」、「現代文學」兩門課,幾次被天真的學生問到「怎樣寫作才會得獎」?於是乾脆來設計兩堂「文學創作與文學獎」的教學單元,順便處理這批莫名其妙的問題。課程結束了,不見那些來問的學生有何動作,後來我把課堂上丟出的稍加修改後寄去參賽,沒想到結果還算可以,〈早餐〉、〈吉屋出售〉、〈家庭訪問〉諸篇,都是在此一前提之下寫出來的作品。當初無非想告訴學生:即使生活經驗貧乏如我者,也可以透過觀察、記錄等功夫,慢慢找到可以挖掘下手的地方,久了也能弄出一兩篇還算像樣的東西。
在〈吉屋出售〉裡,不難嗅出我觀察到的周遭許多生活的空間都離了人味。這部分我在《摩鐵路之城》又發揮更多。這讓我想到,如果我們長期在這樣的空間裡讀書寫作研究,會不會生產出來的東西,根本沒什麼「人味兒」?而像〈早餐〉、〈蛋糕的滋味〉那樣的作品刊出後,曾被若干讀者質疑其「文學性」濃淡的問題,我也不知該如何回答,有趣的是這類作品被轉載的次數卻相對地多,這讓我想到,會不會某些人口中的「文學性」,或許只是他想證明個人的品味?
此外我漸漸明白了:在這個紙本的發表空間愈來愈缺乏的年代,「得獎」才稍稍讓你的創作有被看見的機會(網路發表也是一條管道,但對於習慣紙本閱讀的人來說,在電腦桌前掃拂落葉的觀看方式,不免有虛浮之感)。雖然我已無法像年輕的學生那樣,以為得獎與自我之間必然產生值得執持或驕矜的什麼,好供創作的人自我陶醉,而且也看見:得了獎,才有被批評、被認同或被誤解的機緣,這些都是好事。對於我的學生來說,他們也很喜歡老師得獎,那代表全班又有好東西可吃。如果還有人想問這方面的事,我的經驗是,盡量少看別的得獎者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專注地呈現自己想寫想說的就好。
到了近四十歲才來創作,看來我是個晚熟的人,這或許可以給仍在創作之途上踟躕的學生一些些啟示:慢慢來就好。而我所知道的創作者裡,有一個到了四十多歲才踏上寫作之途。他是我很喜愛的一位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
至於〈清秋〉所寫的主題,則是以前輩畫家廖德政的一段青年經歷為主。幾年前蒙廖先生親自題耑贈書,無以為報的我,遂以他為主角而完成此一短篇。小說的焦點關注於畫家棄醫學藝的心理轉折,與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畫家之父廖進平先生當年因二二八事件失蹤,幾年後畫家將思父之情寄託於創作〈清秋〉,這幅畫作日後不僅獲得省展特選主席獎,亦為美術史上之傑作。德政先生於音樂藝術的涵養亦深,儘管彼時的外界風風雨雨,他內心裡仍有個非常完整的,但凡真正的藝術家都會去滋養守護的無人能剝奪的空間。我懷著虔仰的心情靠近那裡,寫了〈清秋〉。因為用小說的方式呈現,與史實比較有出入的是:〈清秋〉應該是畫家在台北居處完成,小說則將其構思的靈感移至神岡老家。又小說家呂赫若亦有一短篇名作,題為〈清秋〉。
有個朋友告訴我,上一代幾個出色的本土藝術家呂泉生、廖德政、林之助、呂赫若都出自葫蘆墩一帶,這塊豐饒富庶、非常宜於人居的淨土,多年來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可惜長年開發下來,並沒有使得天獨厚的此地出現比較高水準的公共建設品質,反而淪為派系角力掠奪的爭戰地,那些曾經被藝術家以彩筆歌頌的美麗大地,如今只能進到美術館的特藏室才得以睹見。而新聞裡動不動冒出地下水被汙染、公務員大剌剌花費公帑出遊的瀆職事件,有不少就出自此地。我在寫作此類小說時,心裡經常浮現這樣的思索與矛盾: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寫?
所以,當我近日看到一則比賽的新聞,內容大約是歡迎各校景觀學系的高手,以台中一座土地公廟為改造對象,參賽者各憑長才馳騁其對祭祀空間的發想與規劃,我心裡異常欣喜。土地公廟,以及環繞著祂的水田樹蔭,在物質貧乏的年代,曾經在許多人的童年記憶裡吹過一陣一陣徐徐的涼風,那種自然的撫觸是多麼地飽滿而豐潤!不知我這樣說,有誰還能呼喚起心底曾有過的微風光影?我甚至懷疑,缺了那種感受的人,要他憑空吐露創造的豐美與真摯的情感,無異於緣木求魚。如今一座座廟宇隨時代的變遷而塗得華麗五彩,原先的泥土地因貪圖方便而糊上堅硬的水泥地面,景觀上搞得比日本的神社還要摩登,卻也使得居民失去了樹蔭下悠閒沉思的良緣。在某種程度上,這類空間的喪失,可以說是此地人們對於心靈某些根源性情感的集體喪忘,而缺了療癒空間的人們,只好再次花錢遁入電梯大樓裡的精神商談室,或冷氣籠罩的各種時髦養生教室。
我在〈壁虎〉裡借了一點奇幻手法寫出那個孤獨的幻象,背後寄寓了一些些盼望,何時我們能再找回那個與天與地一同呼吸、單純飽滿的祭祀與祈禱之情?人與自然的疏離,是人必然得跟自己疏離的前兆吧。
正因為現實裡的我居住在這樣一個愈來愈嘈亂荒蕪的鄉間,這個期盼於我來說,便有了真實力量的推湧。
小說寫得好或不好,自有專業的批評標準。「這太扯了,」有個教授讀了〈找茶記〉:「偷電纜線偷到被電死,哪有這麼離譜的小偷?」也許他不知道的是,我的取材全來自報紙上剪來的社會新聞。當然,這有可能是我寫得不夠好。
但凡人們創作出來的一切作品,包括小說,有如自然界的花落花開,時間不對,知音難覓,儘管它是那麼多文字意念串成的東西,早了一步晚一步,左偏一步右一步,就沒人看見,而又一次如草葉上的晨露消溶於空氣之中。為了多一些些能被看見的零點幾秒,只好將自身充塞於不斷製造的宣傳、節目裡,這是我們的時代啊。
回想十幾年前的我還在私立學校服務,每天忙到昏天暗地,創作這回事想都沒想過,哪裡知道從私校放出來竟然有餘裕寫作。我常在想,若這麼多終日對學生指指點點,聲稱要幫他們找到自己舞台的老師們,能把自身潛藏的能量釋放出來,不知改革了一二十年,補習班卻愈開愈多、參考書愈賣愈貴的我們的教育,它的面貌會不會真的很不一樣?
張經宏 於二○一一年十一月
【後 記】
這是一部遲來的小說集。年輕時的我讀過文學科系,也曾想像有朝一日可以成為一個作家,但那時的我既困惑又孤獨,周遭認識若干跟我有著相似心靈品質的人,雖然這些人的生活態度少有讓我滿意,但在平庸的我的眼中,他們個個身懷絕學深藏不露,使我很樂意與他們結為朋友。有趣的是這些高人都沒什麼創作慾望,這使我在他們面前,只好乖乖放下自家的破掃帚,低頭拂掃腳邊的塵屑。
那幾年我認真地修了一堆奇怪、如今全無記憶的課,尷尬的是教室裡的知識無一能解決我心裡不斷滋生的疑慮。還算明白的是,如果那時我提筆寫作,要嘛大膽...
目錄
推薦序:
驀然回首的人生碎光 甘耀明 002
早餐 009
吉屋出售 021
家庭訪問 041
澄清湖之旅 067
香蕉‧蜘蛛‧猴 093
蛋糕的滋味 123
恭喜發財 145
找茶記 165
清秋 187
壁虎 209
出不來的遊戲 225
後記 247
推薦序:
驀然回首的人生碎光 甘耀明 002
早餐 009
吉屋出售 021
家庭訪問 041
澄清湖之旅 067
香蕉‧蜘蛛‧猴 093
蛋糕的滋味 123
恭喜發財 145
找茶記 165
清秋 187
壁虎 209
出不來的遊戲 225
後記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