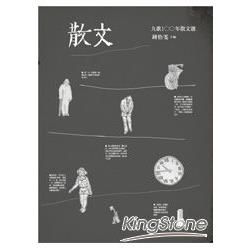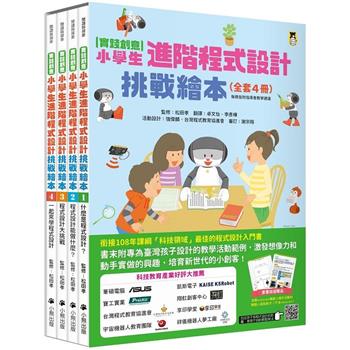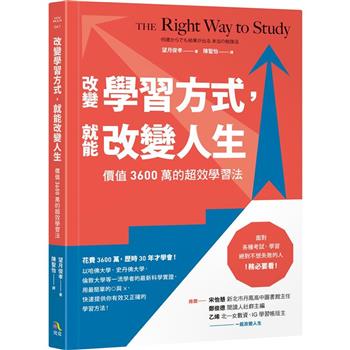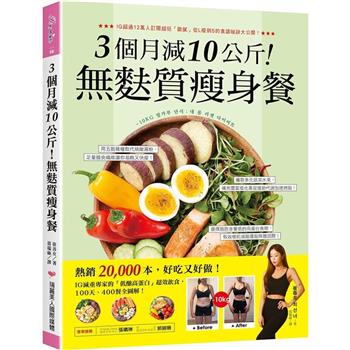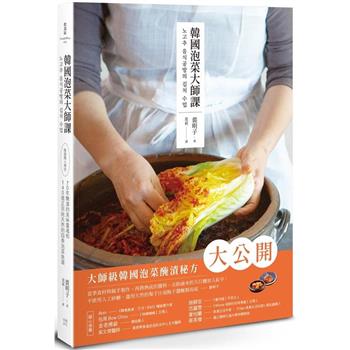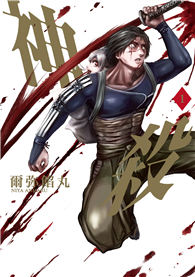◇年度散文獎由周芬伶〈美女與怪物〉獲得。
◇鍾怡雯以學者的嚴謹與作家的細膩,剔選民國100年最精緻美好的散文作品,篇篇動人,讀一本等於讀遍全年最好的散文。
◇特邀2012書籍設計大賞「金蝶獎」圖文書類銀獎、文字書類榮譽獎雙棲得主黃子欽為全書設計,呈現出散文的橫切面。
年度散文選是時代的切片,它是軟歷史,敘述了時間刻度內此時此地的生活,人們的所思所感,不論多麼抒情多麼個人多麼微小,它都具有時代意義。
《九歌100年散文選》風貌獨特,主題越界,手法創新。以旅行為題材的既有朝「外」敘述地景的典型遊記,也有於行旅中向「內」思索的心靈獨白。而飲食書寫則兼備懷舊與知識,更將人情事理融於美文之間。另外還包括環保、人物、親情……等內容,顯現豐富多元的散文面向。
書中收錄簡媜、龍應台、林文月、阿盛、余光中、蔣勳、雷驤、王文華、劉克襄、亮軒、蘇偉貞、廖玉蕙等名家的作品,俱一時之選。還有演員林青霞的清新小品,同時蒐羅文壇新生代言叔夏、張耀仁、吳宗霖、吳億偉、吳妮民、林育靖、吳柳蓓、林怡翠、黃信恩、吳鑑軒、吳睿哲、楊富閔等人的創作。老少齊聚,年齡分佈超越一甲子,作家類型涵蓋小說、散文創作者與學者,交織出欣欣向榮的百年散文盛景。
100年「年度散文獎」得主是周芬伶,入選作品為〈美女與怪物〉。主編鍾怡雯認為:「她擅長寫人生的黑暗,或者心靈的陰暗,然而也會幽世間一默,或者嘲諷自己。今年入選的〈美女與怪物〉是她在《雜種》一書裡形塑的怪咖美學,美和怪是一體之兩面,美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創傷。」
全書精選五十三篇100年度最好看、最精緻的散文。書末附錄年度散文紀事,為整年的文學歷史作詳細記錄。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鍾怡雯
現任台灣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豢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陽光如此明媚》,散文精選集《驚情》、《島嶼紀事》、《鍾怡雯精選集》;人物傳記《靈鷲山外山:心道法師傳》;論文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經典的誤讀與定位:華文文學專題研究》;翻譯《我相信我能飛》;散文繪本《枕在你肚腹的時光》、《路燈老了》;並主編多種選集。
鍾怡雯所著散文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首獎、聯合報文學獎首獎、星洲日報文學獎首獎及推薦獎、新加坡金獅獎首獎、海外華文文學獎首獎、華航旅行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及梁實秋文學獎等。
章節試閱
★ 年度散文獎
100年「年度散文獎」得主是周芬伶,入選作品為〈美女與怪物〉。主編鍾怡雯認為:「她擅長寫人生的黑暗,或者心靈的陰暗,然而也會幽世間一默,或者嘲諷自己。今年入選的〈美女與怪物〉是她在《雜種》一書裡形塑的怪咖美學,美和怪是一體之兩面,美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創傷。」
周芬伶 美女與怪物
美女與怪物常是一體之兩面,美女常配野獸也是真的。
因為長得美而被當寶貝一般看待,這已脫離正常;也因長得美受到種種特別待遇,這更是不正常,到婚嫁年齡,一家有女萬家求,最後不是挑最好的就是挑到最壞的。因為美麗也是一種資產,會引起貪念,遇到懂得疼惜的,可以一直美下去,遇到不懂得疼惜的,沒幾年就憔悴不忍看。有個學妹長得美心性又好,丈夫也是才貌雙全,去了幾年異國,美人變白髮魔女,國外生活想必十分艱辛。另一個嫁給豪門的美女同學,剛開始很痛苦,大家庭規矩多,婆婆愛擺架子,後來她靠自己走出自己的路,說服丈夫搬出來,越老越順心,越老越美。
美一旦變成工具被支配,就不美了,我很少看到從小美到老的,倒是看到很多美女因為變醜而精神失常的。
幾個姑婆長得美又嫁得好,把我們家道帶到鼎盛。爸媽生了幾個好看的女兒,當然也想如法炮製,只是女兒都很叛逆,才第一個依煤妁之言挑中的好門戶,不久就解除婚約,爸媽受到莫大打擊完全放棄女兒的婚事,我們自己挑的都是一般般,家庭環境多不好。
只有三妹好些,美國妹夫出身法律世家,她本想可以過著戴珍珠項鍊穿皮草的生活,沒想到他是信仰清貧思想的左派,家裡連銀器都不准買,只注重精神生活,什麼都學一點,妹妹因此跟著奮發上進,念了兩個學位,彈一手不錯的鋼琴,還有自己的畫室,這比珍珠項鍊和皮草強多了。而我根本沒挑,怪人都會來報到,像我這種沒自信的塌鼻子,只跟怪物有緣。
姑婆中只有五姑婆沒嫁,聽說愛上的是外省人,硬被家裡切斷,總總不快樂讓她對家人充滿怨恨。
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衣服是自己設計自己縫製,穿得像《魂斷藍橋》中的費雯麗還戴手套,到處逛街買東西,找朋友遊玩,送她們昂貴的禮物。
散文★ 名家之作
廖玉蕙 我的媽媽嫁兒子
那年,鄉下的堂哥病逝,母親扶病前往弔唁。
浩大的排場過後,大夥兒聚坐吃散宴。我陪坐一旁,幫母親添飯布菜。同桌俱是母親的晚輩,對她執禮甚恭。母親座位的另一邊,是一位看來年紀不下於她的長者,同著低沉的聲音和母親切切說著些什麼,散宴吃到尾聲時,他忽然激動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包來遞給母親,母親推拒著,不肯拿。那人情辭懇切,幾近哀求地說:「請汝一定要收起來,我這陣比較做得到,阮的幾個囡仔攏在賺錢了!汝如果不肯拿,我心肝會極艱苦咧!」
母親也非常堅持,不停地重複著:
「汝免這樣客氣!汝生活快活,我就極歡喜了!」
看我露出狐疑的表情,母親為我介紹:
「看是恁駝仔伯的細漢後生,汝要叫阿坡仔兄。」
母親回頭跟男人說:「這是我的細漢查某囡,極大漢時,才會走路的那個。」
那男人一聽說,慌忙搖手說:
「毋免!毋免!叫我阿坡就好!恁媽媽自少年就極照顧我,是我一生的恩人。這只是一點點的意思,汝就勸伊收起來,這樣,塞來塞去,歹看啦!」
紅包最終是收了?還是沒收?至今記憶已然模糊。只記得阿坡仔兄用親的語氣跟我說:
「以前,汝不會走路,常常坐在車衫的車仔上,看恁阿母做衫,極乖咧!我每次轉去舊厝,你的嘴極甜,常常阿坡仔兄、阿坡仔兄一直叫。」
時光忽然被拉回到古早的歲月,因為不知如何應答,我感覺有些不自在,只能咧著嘴傻笑。
駝仔伯,我是還留有印象的,他的大兒子阿城我也還記深刻,甚至後來阿城娶的媳婦阿蔭仔嫂及他們的三個小女孩都還記得。至於什麼時後冒出這位阿坡,我是完全茫味無知的。小學那年,我們從鄉下老家搬到較熱鬧的小鎮後,駝仔伯還常來探望母親;幾年後,就聽說他積勞成疾過世。
駝仔伯往生時,我約莫正上初中,已經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童,偶爾會從父母的交談中爬梳一些人際。印象裡,駝仔伯過世前就將之前攢下來的少許存款,拜託媽媽保管。因為阿城和太太阿蔭都是不善營生的人,駝仔伯唯恐他們三兩下就花光積蓄,所以,請託母親代為保管,加以節制。
阿城每回拿錢,都需要出示正當需求才能過關。當時,我就覺得媽媽好有權威,可以主宰別人取用明明是屬於他自己的錢財。何況,阿城還比媽媽多了兩歲,卻得怯生生地來跟母親申請經費;在我的理解裡,母親應該是一位極受信任的人,否則,誰放心把錢交給別人保管。
散文★ 文壇新星
言叔夏 白馬走過天亮
民國一百年許多人都結婚了,包括怎樣也想不到的劉若英。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身旁的同志友人們說唯一可能結婚的女性對象就是劉若英,「大概是因為她看起來非常淡薄的樣子吧。」我對劉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國中時代的〈為愛痴狂〉,土黃色墊肩大夾克的她在MV裡徹徹底底地燒了一把吉他。我還記得那是第四台剛開始普遍的時代,有一個頻道從半夜三四點開始就會陰魂不散地輪播著每天幾乎一模一樣的MV清單,沒有主持人也沒有任何旁白。這份清單大概以一個月左右作為週期會定期更新,大約是加入了每月新進榜的歌曲。有段時間,我總是在起床趕第一班公車上學的五點鐘時間,會反覆地聽到這首歌。
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奇異的年少時光。我所住的那個小鎮在離任何學區都遙遠的地方,於是小學一年級起我就學會了在擠滿眾多高年級學生的公車上突圍拉到下車鈴的求生技能。國中以後,母親讓我去上位在市區的教會學校,這個技能的規模於是被擴張到更大。我記得上課的第一天輪到自我介紹,當我說出自己畢業的小學時,台下的一個同學非常認真地說:「你一定是第一名畢業的吧。」她用很誠懇的語氣對我說:「要不然怎麼可能進我們學校。」
我知道她沒有別的惡意,但這段話裡我只聽到兩個部分:她用「你」來稱呼我,用「我們」來稱呼自己。「我們」當然包括未來的「我」,可是卻無法化解當下的我站在台上的那種困窘。我下意識地抓緊了制服裙子的皺褶,不知道該將自己的手腳擺放在哪裡。下了台以後我發現那裙子變得更皺了,而且沾滿了白色的粉筆灰,後來一整天除了被點名和上廁所的時間以外,我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動也不肯動。
對那個學校的人來說,我所來自的地方對他們而言無異是甲仙或都蘭之類的地名。我沒有邀請過任何人來我家,也沒有同學提出過放學後一起去補習班做功課的邀約,整個中學六年,我都過著獨自搭乘公車上下學的生活。從我家到學校的通勤時間大約要花上一小時,公車會從繁燈夜景的城市一路蜿蜒爬上大坪頂,繞過山區而下。我總是無聊地對著窗外刷過的景色發呆。車廂的人漸漸稀少了起來,公車搖搖晃晃地,從城市漸漸駛離,常常一不小心就使人陷入了瞌睡之中。冬天的天色暗得極快,在一本搖著搖著就幾乎要從膝上掉落的英文課本裡醒來時,四周已是荒瘠暗黑的山野。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的我非常喜歡那樣甦醒的時刻。天花板上老舊的日光燈管白晃晃地,像水族箱般地壟罩著整個車廂。周身稀少的人們看起來都那麼孤獨,一個個散落在藍皮座椅的角落裡;他們有人像是水鳥那樣地垂頭睡著,有人蜷起身體緊挨著鐵皮的車廂耽坐,腳邊堆放著一個好大的旅行袋,他要去什麼地方?要去那裡做些什麼?我想不出這班夜車能抵達一個更黑更暗的地方了。
★ 年度散文獎100年「年度散文獎」得主是周芬伶,入選作品為〈美女與怪物〉。主編鍾怡雯認為:「她擅長寫人生的黑暗,或者心靈的陰暗,然而也會幽世間一默,或者嘲諷自己。今年入選的〈美女與怪物〉是她在《雜種》一書裡形塑的怪咖美學,美和怪是一體之兩面,美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創傷。」 周芬伶 美女與怪物美女與怪物常是一體之兩面,美女常配野獸也是真的。因為長得美而被當寶貝一般看待,這已脫離正常;也因長得美受到種種特別待遇,這更是不正常,到婚嫁年齡,一家有女萬家求,最後不是挑最好的就是挑到最壞的。因為美麗也是一種資產,...
作者序
逆時代之流而上──百年散文選序
文/ 鍾怡雯
1.
上回編年度散文選是二○○五年,今年再接編匆匆六年已過,相同的是,主編序都開筆於大年初一。我的生活沒有必然的休息日,閱讀既是工作也是娛樂。工作和娛樂貼得太緊絕非好事,那讓我產生一整年都沒休息的錯覺。編年度散文選的這一年來,我確實每天都在工作,當然也可以說,我每天都有娛樂。
今年的編務特別困難,工作的感覺比娛樂大些。選文以平面媒體為主,排除了漫無邊界的茫茫網海,仍然讓我在編選過程中左右為難,在取捨之間踟躕。為什麼?我反覆問自己。究竟是什麼讓這本散文選遲疑許久才定案?
也許,現實和我的想像頗有落差。
我的散文繪圖其實非常廣,舉凡雜文、純散文(文學性散文)、報導文學、小品文、傳記、書信、日記等敘述性文體均是選文範圍。散文歷經從雜文、美文到純散文的變化進程,事實上,就現代散文史的發展脈絡來看,散文,並沒有所謂「純」散文,或者被誤讀的「美」文──一種獨立於時代之外的文學範式,被視為純粹的審美客體──散文從來就跟時代有密切的關係,以現代散文史的角度觀之,它跟直面現實的雜文始終暗通款曲。因此,年度散文選是時代的切片,它是軟歷史,敘述了時間刻度內此時此地的生活,人們的所思所感,不論多麼抒情多麼個人多麼微小,它都有最小的時代意義。然而,我總以為散文可以不必那麼「純」,周作人建立的抒情傳統早已成為散文的主流,我希望散文可以更原始一些,更駁雜一點,更「不像」散文,修辭的技術層面之外,它可以像論文具有論述和批判的功能。
原來以為可以選入一兩篇論點精闢,文字可讀的社論,以彌補雜文的缺憾。然而我讀到的社論果真以「論」為主,文學的質感大多不是重點,缺乏情感的潤澤,太乾澀冷硬,離散文畢竟遠了些。散文原來是這樣一種麻煩的文類,濫情不行,沒感情也不行;質木無文不行,過度修飾也不行。都說散文自由,卻常常自由過了頭,它的邊界太寬鬆,接近文學原料的體式很難規範。在白話文學史的源頭,散文以文類之母的方式出現,它是新思想的傳播文體,同時肩負著建立現代文學美學範式的責任。梁啟超文界革命的第一要務,便是散文語言革命。當散文成為研究對象,就常常讓人陷入困境。散文選難,難在這裡。
書信和日記就更少了。最精彩的書信和日記必然是私密文件,無法公開。秘密是好看好讀的關鍵,能公開的多半不會是典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動人而悲壯,然而涉及家國民族也太公領域,太政治正確了些。自然寫作可視為進化版且具時代意義的報導文學;傳記寫得再感性些,就成為憶故人的抒情散文。小品文沒有缺席,純散文是大宗。大體而言,這本散文選仍然很傳統,因為作品如此,選文者宜如實呈現。沒有一本選集是完美的,缺憾是必然,何況選集多半體現了編者的主觀和偏見。每編一部選集,我這樣安慰,或者提醒自己。就像文學獎評審,換了評審,得獎名單可能會大洗牌。
說到文學獎,它是我的第二個疑惑。今年讀了特別多地方文學獎得獎散文,不得不說,台灣的文學獎實在太多了,多到泛濫。地方性、財團法人、宗教或者什麼性質令人眼花撩亂,名堂記不起來的文學獎。平面媒體的發表空間有限,文學獎本來是新人練筆或出頭的管道,它絕對具有正面而積極的意義。然而這幾年來文學獎已經泛濫到了應該檢討的地步。按常理推論,文學獎的蓬勃應該代表文學創作能量的勃發,實驗的前衛的推陳出新的,被主編們埋沒掉超越時代眼光的佳作,應該在這些百花齊放的文學獎裡出現。我應該掘得到寶,不論是寶石或璞玉。
事實不然,而且比率非常低。文學獎只是假象。散文獎項生產三到六篇散文,我很懷疑,真的有那麼多寫作人口嗎?文學獎究竟是把餅做大抑或稀釋文學?又或者,這是全民寫作的年代?然而文學從來不會是什麼全民運動(除了寫作,全民有很多比寫作這件事能夠做也做得更好更值得鼓勵的),除非我們把文學規範打散,從頭再來。更何況全民寫作是非自發性,被動的寫作狀態之下產生,有點命題作文的意味,跟地方文學獎一樣,背後太多跟寫作無關的政治或商業思考,以為這可以讓文學大興,無疑把文學過於簡單化。文學的生產過程非常複雜,絕非單一外力可以速成。真要鼓勵創作,不如辦幾份雜誌報紙,增加發表園地來得實在。地方文學獎多的是面貌模糊,聲口一致的親情散文。地方政府、參賽者,乃至評審全都應該反省。
2.
歲末年終,一年的閱讀工作即將結束之際,讀到季季〈不要臉的人之告白〉,不禁大喜。終於有人掀底牌了。這篇散文雖然溫文沒火氣,然而觀點犀利,處處說中要害。跟季季一樣,我是「站在臉書門外,無意芝麻開門」一族。改寫托爾斯泰的話,上臉的人理由只有一種(寂寞難耐哪),不上臉的人理由有千百種。季季說不要臉的生活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能有這樣的反省,大概都要歷經手寫到電腦的世代,歲數有一些了。這個族群曾經迷戀過紙本和書本,對手工業仍然眷戀,對網路仍有警覺。成長於資訊時代的小孩,恐怕很難理解不上臉要如何生活。
小姪女沒學會走路,話還說不清呢,就會用手指操控i字頭的玩具,小手在ipad上翻頁的熟練架勢令人咋舌。這些3C世代,他們哪有什麼選擇題?因此,他們要如何體會蔡珠兒〈我好土〉一文所說,把惡地變成肥土的艱難,並且還能從土性領悟人性?「好土」在廣東話裡帶有落伍,跟不上潮流之意,這時代大家都上臉去了,誰要下土?網上也能種菜不是嗎?
然而寫作確實需要腳踏實地的生活,逆(潮)流而上的勇氣。這是個需要安慰和呼朋引伴,害怕孤獨和被遺忘的時代;需要不斷有人給讚,活在虛擬的年代。寫作者最不怕的應該是孤獨和寂寞,也應該要有被遺忘的準備。我不明白天天在網上結黨閒聊,隨時有人敲老被干擾,要如何靜心寫作,或者思考?或許有人天賦異秉吧。「不要臉」的堅持是一種生活態度,作為百年散文選的開端,具有逆流而上,不與眾合流的宣示意味。應該理直氣壯宣示,我很土。
散文確實也來自生活。這句話太寬泛,說了等於沒說,然而自有對網路時代的感嘆。或許會有那麼一天,網路經驗會覆蓋生活體驗,我們可以模擬真實的生活,複製如假包換的人生,以及情感。雷驤〈糞餅〉的農業時代經驗;朱天衣〈新天新地〉攜貓狗逐野地的鄉野墾荒;劉克襄〈濕地的蝦猴〉實地考察蝦猴生態史,反石化的呼籲;楊澤〈大地震──一個小男孩的見證〉小男生飽受的驚嚇,被大地震震壞的童年。總有一天,這些來自人跟生活產生的火花,都將成為歷史。那時,我們可能要編的是「年度雲端散文選」(多麼詩意的書名)。
有些時候我們會特別意識到時間的行走,在生死相交,季節推移的瞬間,在全然孤獨又無助的時刻。散文需要向外索,也要向內求。生命經驗可遇不可求,然而靈視則必須成長於絕境和孤獨,置於死地而後生。宇文正〈聲音也會老的〉發現手術只能力挽有形之肉身,抽象的聲音或者眼神,是無法回春的。聲音一老,人就老了。她曾經擁有一段奇特的經驗,一邊陪癌末的媽媽,一邊在股市當記者,擁有大量自己的時間,每天可以回家彈楊琴唱歌。「極樂世界」時期的孤獨狀態,讓她領悟到聲音會老的秘密。呂大明〈生命的衣裳〉寫生命的遲暮。生命是襤褸的衣裳,然而只要活著,就必須努力縫綴。散文以西方而古典的意象鋪排而成,浪漫而唯美,以詩筆寫生之艱難,也寫生之堅韌。徐國能〈夕照樓隨筆二則〉則在陽光如熾的盛夏寫無所不在的死亡。他觀察垂死的蜜蜂,感受生之衝擊,在死亡身上體會靈魂和肉身的存在。又或者無法安靜的躁動春日,在蹉跎時光的遺憾中,捕捉到渺茫而悵惘的思緒。這篇散文安靜而憂鬱,寫法非常徐志摩,寫法傳統又極為現代,是嶄新的「徐」氏風格。
3.
今年的散文選非常特別,幾乎無法以主題歸類。即便勉強分類,旅行、飲食和懷舊這三大類型也都有了混雜跨界的風貌,跟前幾年清晰可辨,單一主題式的寫法相去甚遠。至少我在編九十四年散文選時,它們各就各位,撈過界的很少。
成英姝〈男人與沙漠〉、余光中〈黃山詫異〉、蔣勳〈薩埵那太子捨身詞虎〉、張瀛太〈深山色狼〉以及董成瑜〈夢與夜宿機場〉均可歸入旅行文學。余光中〈黃山詫異〉是很典型的遊記,山水行旅筆筆分明,旅行是朝「外」看,把個人縮到最小。相較之下,其他四篇向「內」望的比例增加。成英姝〈男人與沙漠〉寫新疆沙漠賽車手活在當下的熱情,挑戰險惡的勇氣,卻也同時寫自己的愛情觀。蔣勳〈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只有起始時的「麻線鞋」和結尾跟旅行有關,餘則寫佛經啟示。張瀛太〈深山色狼〉寫在中國某市場買威而剛,生猛爆笑,可是我們連這市場的名字都不知道。董成瑜〈夢與夜宿機場〉的書寫空間在機場,不像「正宗」的旅行文學。然而機場經驗確實是旅行的一部份,這種平凡的題材最難寫,必得恆處孤獨,心靈異常敏銳,才能透視平凡,才能在夜宿機場時,發現過境大廳竟似非洲大草原,兩三百人的打鼾變成兩三百隻獅子的草原大合唱。
飲食散文亦然。王盛弘〈大風吹〉寫童年的零食,同時寫故鄉的人事,說是飲食散文也行,懷舊散文亦未嘗不可。張曉風〈山寨版的齊王盛饌〉則同時兼有飲食和知識散文之趣,從炒雞腳趾頭(雞跖)開始,上溯古籍,下及唐宋詩,考古兼嘗味。飲食散文至少在兩三年前是高峰,今年似乎「退流行」了,它變得低調圓熟些,向旅行、憶舊靠攏,或者成為散文的配角。
今年收入了幾篇精彩的親情散文,張讓〈好一個女子〉、阿[女烏]〈夢中的父親〉、廖玉蕙〈我的媽媽嫁兒子〉、吳晟〈不合時宜〉以及吳均堯〈身後〉。其實不太願意把親情散文的標籤貼在〈好一個女子〉上,那會狹化這篇佳作的視野。此文固然是憶故人記舊事,對母親這個角色和職責的反思,則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重點。張讓以歐巴馬浪漫勇敢的母親和兇惡高傲的虎媽對比,充滿思考的熱情,和批判的力道。她認為虎媽是中國文化裡的糟粕加上美國式自戀的最壞示範,一針見血,讓人喝采。〈好一個女子〉本來是寫母親,卻又岔出去談親子教育,左右開弓再打壞母親的示範,讚美自己母親的不凡。張讓以知性散文見長,思考是她的長項,寫最親近的母親,筆調既近又遠,既親又疏。好一篇散文。
4.
有兩文不得不提。一是林青霞〈瓊瑤與我〉,一是馬任重〈上課睡覺的女人〉。林青霞主演過許多瓊瑤的電影,由她摯筆近身寫瓊瑤和瓊瑤的電影,最精彩的電影史筆莫過於此。〈瓊瑤與我〉同時寫成長和母親,以及瓊瑤的愛情。多條線路均以瓊瑤為軸心輻射出去,層層疊疊,卻是條理分明。〈上課睡覺的女人〉是個九二一受災女人的悲傷故事。馬任重是社區大學老師,他的課堂有個學生是專門來睡覺的。這女人在九二一地震時失去先生和家人,因此長期失眠。教室讓她覺得安穩,讓她放鬆,也只有在教室,她才能入睡。初讀這篇散文很震撼,久久無法平息。作者的文字很平淡,然而故事動人,它令我印象深刻。九二一的創傷並沒有消失,只是未被持續發掘,或者,被善忘的社會遺忘了。
今年新人的表現亮眼,他們或者初試啼聲,或者已經出版過一兩本書,得過一些獎,然而均是可期待的散文新筆。這張名單包括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張耀仁〈讓我看看你的床〉、吳宗霖〈髒話練習曲〉、吳億偉〈鼻音〉、吳妮民〈週間旅行〉、林育靖〈佛像店夫妻〉、吳柳蓓〈陪姪女一段〉、林怡翠〈耳環〉、黃信恩〈熱臀記〉、吳鑑軒〈陰毛〉、吳睿哲〈龍蝨的眼睛〉,以及楊富閔〈壞春〉。這批新力軍,為散文選增添了向榮的新氣息。
年度散文獎得主是周芬伶。近幾年來她筆耕最勤,質量俱佳,散文風格迭有變化。她的散文狂熱而勇敢,節奏快,善於自剖也剖析他人。她擅長寫人生的黑暗,或者心靈的陰暗,然而也會幽世間一默,或者嘲諷自己。無論是《蘭花辭》(2010)或《雜種》(2011),都足以獲得年度散文獎。今年入選的〈美女與怪物〉是她在《雜種》形塑的怪咖美學,美和怪是一體之兩面,美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創傷。
感謝入選的所有作者,感謝你們給我一年的工作,以及娛樂。
逆時代之流而上──百年散文選序
文/ 鍾怡雯
1.
上回編年度散文選是二○○五年,今年再接編匆匆六年已過,相同的是,主編序都開筆於大年初一。我的生活沒有必然的休息日,閱讀既是工作也是娛樂。工作和娛樂貼得太緊絕非好事,那讓我產生一整年都沒休息的錯覺。編年度散文選的這一年來,我確實每天都在工作,當然也可以說,我每天都有娛樂。
今年的編務特別困難,工作的感覺比娛樂大些。選文以平面媒體為主,排除了漫無邊界的茫茫網海,仍然讓我在編選過程中左右為難,在取捨之間踟躕。為什麼?我反覆問自己。究竟是什麼讓這本散...
目錄
主編 鍾怡雯 序
01 季 季 「不要臉的人」之告白
02 張曉風 山寨版的齊王盛饌
03 簡 媜 在街頭,邂逅一位盛裝的女員外
04 龍應台 我們的村落
05 言叔夏 白馬走過天亮
06 張耀仁 讓我看看你的床
07 成英姝 男人與沙漠
08 沈宗霖 髒話練習曲
09 吳億偉 鼻音
10 吳鈞堯 身後
11 林文月 散步迷路
12 阿 盛 萍聚瓦窯溝
13 徐國能 夕照樓隨筆
14 吳 晟 不合時宜
15 張 讓 好一個女子
16 吳妮民 週間旅行
17 阮義忠 抽屜裡的浪花
18 鍾文音 骨肉
19 陳 雪 迷魂記
20 楊 澤 大地震─一個小男孩的見證
21 余光中 黃山詫異
22 蔣 勳 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
23 林育靖 佛像店夫妻
24 雷 驤 糞餅
25 陳芳明 十年之約
26 宇文正 聲音也會老的
27 朱天衣 新天新地
28 吳睿哲 龍蝨的眼睛
29 方秋停 耳鳴
30 柯裕棻 太平洋的浪
31 曾郁雯 三支酒瓶
32 林怡翠 耳環
33 王文華 現在是最好的狀態
34 吳鑑軒 陰毛
35 馬任重 上課睡覺的女人
36 林青霞 瓊瑤與我
37 蔡珠兒 我好土
38 張瀛太 深山色狼
39 黃信恩 熱臀記
40 劉克襄 濕地的蝦猴
41 亮 軒 人未約,黃昏後
42 王盛弘 大風吹
43 吳柳蓓 陪姪女一段
44 蘇偉貞 內在描繪──關於鄧雪峰老師
45 朱宥勳 救援投手
46 呂大明 生命的衣裳
47 歐銀釧 新竹故事包
48 利格拉樂‧阿[女烏] 夢中的父親
49 楊富閔 壞春
50 廖玉蕙 我的媽媽嫁兒子
51 林文義 雙桅船
52 周芬伶 美女與怪物
53 董成瑜 夢與夜宿機場
散文記事 杜秀卿 100年散文記事
主編 鍾怡雯 序
01 季 季 「不要臉的人」之告白
02 張曉風 山寨版的齊王盛饌
03 簡 媜 在街頭,邂逅一位盛裝的女員外
04 龍應台 我們的村落
05 言叔夏 白馬走過天亮
06 張耀仁 讓我看看你的床
07 成英姝 男人與沙漠
08 沈宗霖 髒話練習曲
09 吳億偉 鼻音
10 吳鈞堯 身後
11 林文月 散步迷路
12 阿 盛 萍聚瓦窯溝
13 徐國能 夕照樓隨筆
14 吳 晟 不合時宜
15 張 讓 好一個女子
16 吳妮民 週間旅行
17 阮義忠 抽屜裡的浪花
18 鍾文音 骨肉
19 陳 雪 迷魂記
20 楊 澤 大地震─一個小男孩的見證
21 余光中 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