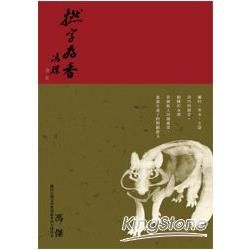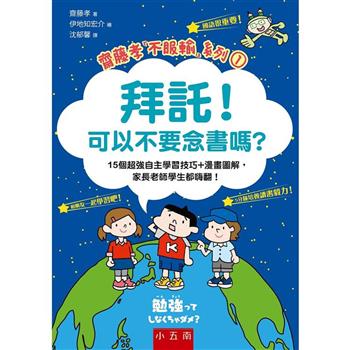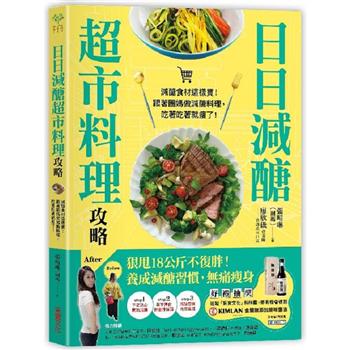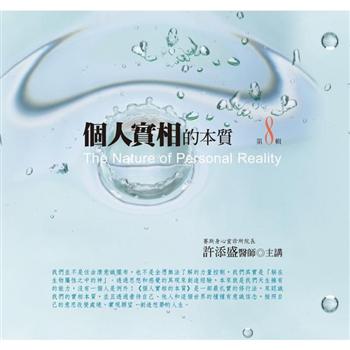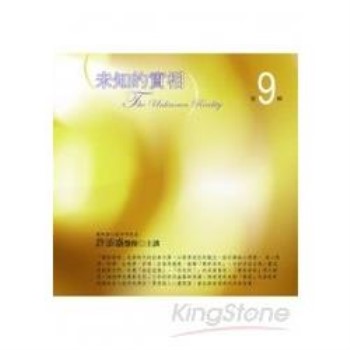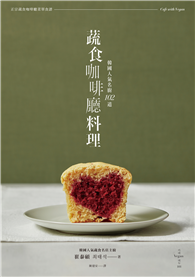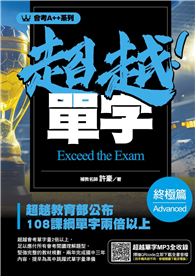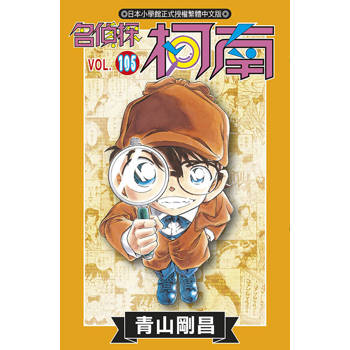第一帖◎土語匯
〈打 豁〉
是說閃電。
只有鄉村的閃電,才配稱得上「打豁」。城市裡的閃電是不能用的,品質不好,還得去付昂貴的電費。
鄉村的烏雲像驢群一樣,灰濛濛而來,又灰濛濛而去。這一團團灰驢們,先是在天空散步、啃草,後是交頭接耳,交流思想,再是聚攏合併,然後,才在天上開始任意馳騁。驢腿間的最好距離是:疏可跑驢,密不透風。像齊派的篆法。
久旱的禾苗在下面都靜靜地蹺著腳,呆望著,等待一場雨水的滋潤,內心喊渴。像你當年在六樓下焦急期待情人跫聲的那種心情。
大地頓時開始熱燥。
忽然,這個動詞就出現了,在北中原大地上,在天地連接之處。它是寫在天上。光的根鬚。
──打豁!
彷彿佈滿大樹白色透明的根條。這是永遠不曾重複的閃電。世界上的閃電每一條都是不雷同的。原創的閃電。
那是誰把烏雲扒開一個大口子。挺傷心的。打開豁口,讓關閉了整整一個夏天的情感此時盡情地釋放出來。
如你面對久別失散的情人,伏在肩頭,該去失聲痛哭。
〈砍 刀〉
從小我就這樣稱呼螳螂。
在北中原鄉村流行的昆蟲排行榜中,最能獲「風度獎」的,我認為首推的一員,就應該是螳螂。雖小,卻端著大架。
秋天來了,鄉村的鳥兒們一一起自大地,都忙著去田野抒情,糧食入倉,鄉村詩人忙著去寫蹩腳的憫秋詩句。只有它,螳螂,高高地站在禾梢之上,從容站立,不可一勢。它敢與最後來臨的秋霜對峙:
二目圓睜,揮著一方大砍刀,立在秋風裡,活脫脫一副關老爺相。
那個年代,我正在鄉村寂寞地習畫,描摹一本鄉村版的《芥子園畫譜》。因為有螳螂的出現,我才感悟,發現齊白石畫中,最妙靈之處,就是有一種鄉土性情永遠在貫穿,他可是個一輩子充滿「地氣」的農民性情的畫家。
而其它「洋派」的中國畫家,骨子裡就沒有這種東西。如劉海粟、如林風眠、張大千、徐悲鴻這另一類大師。
儘管後世有稱齊璜「滿紙村氣」之譏。
在那些小品冊頁中,常會有一隻土生土長的螳螂,從容地扛刀出場,像要在《三國演義》中〈單刀赴會〉。那是一齣鄉村的折子戲。
只聽鄉村一面如滿月的銅鑼清脆地一響,月光的聲音便簌簌滑落,又一響,讓我忍不住得去翻看下一頁。
第二帖◎草木劄
〈曼陀羅‧孫二娘配藥〉
我小時侯稱它“山大麻子”“山茄子”。在我眼裡,比其它草們更有用途的是:它那一團團毛刺刺的果實可以堵住鄉村縱橫交錯的老鼠洞。像《水滸》裡一種叫狼牙棒的冷兵器。覺得會讓鄉村鼠王一籌莫展。這種童稚之舉只能使鼠們更堅信向下的努力,紮根深處,深達地心,不會從根本上去達到遏制的作用。
在我們村四周、田野或壟頭上,時不時地站滿這種威風凜凜的曼陀羅,讓鼠們探首,遠遠地望著。交頭接耳,敬而生畏。
高達三尺,莖直粗狀,開著漏斗般的白花,像是一出“告鼠白皮書”。
那花名就叫洋金花。我初次聽到姥爺說這稱呼時,覺得像喊一位鑲金牙的女人。個高。燙髮。
村中的隊長叫黑老包,據說,早年是從山東菏澤那邊逃荒過來的。一個異鄉人能在本土村中當上“首腦級別”的人物。除了本村的民主程度外,還可見其人的聰明。黑老包有個習慣,每到支氣管喘息發作期間,就采下洋金花,曬乾,搓碎,放在煙斗中當煙吸,說可治急喘。有一年我們割草歸來,在路上相遇,他友好地讓我嘗試一口。我狠狠地吸了一下,一股幹苦之氣浸入喉嚨。嗆住了,我忙把煙斗轉讓給他。
因為珍惜,他還怕我多吸呢,順勢就說:“是不能吸多,吸多會中毒的。”
他說得有道理,可能是經驗之談。
三十多年後,我從一個河南同鄉大植物學家吳其濬編的《植物名實圖考》中看到它的面孔:“曼陀羅,人食之則顛悶,軟弱,急用水噴面乃解。”這段文字詭秘,說它是一種背景與身份複雜之花,需要解密。
關於曼陀羅,江湖上還藏有一個天大的秘密,我現在道出來,也不算破了江湖規矩:一位鄉村醫生告訴我,蒙汗藥主要成份就是曼陀羅加工製成。它是古代最經典的麻醉劑。
這藥在宋人傳奇小說裡經常以不同面目出現,是那時俠客們手中必備的流行之物,與二戰時期國際間諜隨身攜帶的消音手槍、現代女士小姐隨身攜帶的口紅、高官汙吏常帶的壯陽春藥一樣:都屬於流行與時尚物。
《水滸》裡被孫二娘、朱貴們麻翻的魯智深、宋江、戴宗、徐寧這一類江湖人物,說到底,其實都是被我們鄉村的一棵棵達三尺之高的曼陀羅麻翻在地的。一日之內,不得動彈。
“著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腳水。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裡?這家恁麼好酒!”施耐庵是這樣紀實的。
不是酒好醍醐灌頂,而是酒罈邊隱藏著一棵常在黑暗深處發笑的曼陀羅。李時珍叫風匣兒,花白,鮮亮,在交叉的毛絨絨綠葉上,花朵穩穩坐著,依然像一朵巨大漏斗。正頗有心計地設著一方小小陷阱。
第三帖◎鄉村譜
〈地理志〉
趕鵝
這個村名就叫趕鵝。曾經是動詞不是名詞。如今靜止而不走動。
《滑縣誌》上載,米國兩位使臣為唐王進貢寶鵝(米國屬中亞,繞道河南,肯定是借公款旅遊。馮考),路經大潭,就是我老家高平鄉馮潭村附近,在潭中浴鵝。鵝浴後,得靈氣竟騰空而飛,兩位使臣急急追趕,追到此地,鵝就從這裡上天了,天在這裡有個小縫。這地方就叫趕鵝。
趕鵝村和我父親從小生活的馮潭村相連,地頭連著地頭,草根交纏著草根。父親割草時會經常到那村。這邊的青蒿伸到那邊的傳說裡,地下一條蘆根連著兩村。編傳說者肯定考慮到地理比例。
外出了近半個世紀年,父親終於回來。葉落歸根。在相鄰的土地上,父親的墳如今座落那裡,沉寂,無語。小土丘像當年教我寫字時的一方硯臺。和母親靜歸大地。燒紙時看一眼對過,田野裡一片迷蒙。
妹村
舜帝賜董父為豢龍氏,居韋城,到夏時,封劉累為禦龍氏,地址還是居韋城。韋,當年的一個國家符號。
韋國就是現在我小時候生活的留香寨北面的妹子村,《詩經‧鄘風》裡有“爰采唐矣,沬之鄉矣”。因諱“沬”字,改為妹子村。我們簡稱叫妹村,發音卻不是mei,姥姥姥爺發音miao,卻叫“妙村,”這裡至今還用此音。不知是否古音?
有一年看到譚其驤先生編著的西周地圖,在我故鄉的地方,就標明“沬”,當為衛都。
豢龍氏善養龍,他從事的恐怕是中國最氣派的服務工種,現在清華畢業也分不到此項工作。不玩則已,要玩就玩大的,這不同於養驢養馬養珍珠鼠,那可是專門養龍啊,只有非凡的奇人才可從事操作,當今世界最大富豪比爾蓋茨頂多經營個電腦。
我就考證,養龍場地就在當年我家杏林附近。多年來,看了那麼多無用有趣的閒書,我一直不知道龍是吃素還是吃葷以及它的營養結構。但我知道妹村親戚家的人都愛吃杏,吃留香寨的麥黃杏。
妹村有一家親戚,每到杏熟時節姥姥就帶著我姐按時去送杏。最早的麥黃杏熟時,每年都送滿滿一柳籃子。經過河門頭、牟家倆小村,走七裡半土路就到。鄉路邊種有打瓜,開著黃花。不動聲色。
桑村
以我家舊房為中心,劃弧計算,桑村離我村十來裡,舊縣誌上說“古衛有桑間濮上之地。”“桑間”就是桑村鄉一帶,古時這裡桑樹成林,該村恰在其間,就叫桑村。這樣說一點不牽強。
嚴肅的歷史對我的故鄉這樣評價:《禮記》和《漢書》裡稱“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這些資料來自官方權威,讓我覺得“桑間濮上”始終是一個貶義詞,說的都是靡靡之音,在主旋律前面自豪不起來,和我少年時代偷聽敵臺裡的鄧麗君歌曲一樣。繞梁三日。我衛地的先人風流多情,都善寫愛情詩啊。看看《詩經》裡的“衛風”就知道,衛風大多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刪掉的作品。
大片桑樹在《二十五史》裡生長,泛綠,泛紅,消逝。留下幾棵。那村裡有人制桑叉農具,經常麥收前到我村來賣。我姥爺打麥場時說:這桑叉是桑村人熥的,好使。
桑村還是本土某一時期一個敏感的政治符號。在北中原印象裡,貫穿有一種晴雨錶的氣息,當年一位大人物的祖墳半夜被扒了,說是風水從此被破,便幹不成事。政治更迷戀迷信。
學堂崗
我父親在世的一年,我倆騎自行車到過那裡一次,去弔唁村裡的一個我該叫姑夫的親戚,回來路過學堂崗,父親說,去看杏壇吧。
歷史上稱這裡“平廣突兀,近崗土皆赤色。”相傳孔子周遊列國在此講過學,故名“學堂崗。”涼亭裡有一通杏壇碑,後人記載這裡是“孔子設壇講學之地,四子言志之所。”那是《論語》裡著名的一段“抒發我的理想。”
我們這裡至今還把學校稱作“學堂,”古風猶存。
孔子述而不作,我也只好把文寫短一些。草莖一截。
落陣屯
子路和我在一個縣裡工作,只是中間有兩千年的時差。
子路在我現在居住的長垣當過首位縣令。18歲我一次進城,看到過縣政府舊樓上有一“子路治蒲”的舊匾額。充當了政府的一方帽沿。今縣令當以古縣令為豪。
子路後來在衛國被蒯聵所攻,身負重傷。子路臨死前也要把頭纓扶正,他喜歡風度,需要形象工程。傳說在這裡落陣死去,後人紀念,這個村就叫落陣屯。名字一直就這樣叫下來。
前年我騎車到北郊“散車,”看到公路上牌子標明竟是“羅鎮屯。”一問,原來縣裡有一位領導說是原名不好聽,新時期要開發經濟,不祥,就改為這個新名。
這是一個地理細節,卻幹了一件點鐵成石,弄巧成拙的事情。我對人說,不祥?北京不是還有公主墳嗎?
當今政府官員以為自己什麼都瞭解,揮揮刀,咯嚓一聲,果斷,一下子就把歷史的睾丸割斷半個。斷口處敷上時代的水泥。譬如當代所謂的經濟開發。
張三寨的桂陵之戰
少年時回家,走五十華里路。騎一輛自行車從這裡路過,再穿過林河、葛村,最後到達留香寨。就看到姥姥在村頭早已站著,等待。
歷史學家考證,張三寨是春秋戰國著名的“桂陵之戰”遺址。“圍魏救趙”的成語就來源於這裡的某一片瓦下。遺址社會上大多數人不一定知道,但是現在肯定有大多數人都在使用“圍魏救趙”之計。譬如情場、官場和商場上的聲東擊西,圍你救我。
成語與我無關,我是擦著成語的邊沿繞道而行。自行車碾過的土地裡,一定有箭、戟、鏃、折蹄的馬、風聲、銜枚之聲、銅鈴之聲和孫臏的陰謀。還有這零散的成語。
從張三寨穿過時,每一次我都沒有見過孫臏和龐涓,只見到十字路口一個打燒餅的,使用木炭。臉色亦如木炭。每次我會賣十個草爐燒餅,夾牛肉,要給我姥爺帶回。
燒餅上的芝麻像戰國年代黯淡的星星。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撚字為香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文學作品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撚字為香
★有文有畫,均由作者親手創作。
散文大家王鼎鈞曾讚馮傑的書畫:一揮參化育,眾卉出精神,無複池中物,驚為天上人。
馮傑以文字走村串巷,用曼妙詩意的筆觸,集文畫為一體,記錄那些消失在時光流裡的陳夢舊事,如同季後拾穗般地摭拾已漸淡忘的鄉村語彙。
他細心地打撈,梳理那些沉澱民間的元素,延伸大地繁茂的華木草本,構築一方只屬於他自己獨有的「紙上北中原」。獨特的創意,從方寸之中瀰漫出濃厚的文化氣息,讓冊頁之間飄散芬芳,重返人間的草木情懷。
全書共分解析在地詞語的「土語匯」、探究花草根葉的「草木劄」、細數鄉里情事的「鄉村譜」等三輯。簡潔又幽默的文章,書寫對自然的依戀、對大地的感恩、對鄉土的鍾情,同時佐以形式別致,親自繪製的插圖,再現鄉土文化的魅力,於消逝的語境裡尋找閱讀的喜悅和溫馨,喚起我們每一個人現實世界中仿若前世的記憶。
作者簡介:
馮傑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當代作家,詩人,畫家,是大陸作家中獲得台灣文學獎項最多的作家。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宗教文學獎、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在海峽兩岸出版有兒童小說集《飛翔的恐龍蛋》、《冬天裡的童話》、《少年放蜂記》;詩集《一窗晚雪》、《布鞋上的海》、《中原抒情詩》、《討論美學的荷花》;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九歌出版社)、《泥花散帖》(印刻出版社)、《一個人的私家菜:說食畫》(聯合文學出版社)等。
章節試閱
第一帖◎土語匯
〈打 豁〉
是說閃電。
只有鄉村的閃電,才配稱得上「打豁」。城市裡的閃電是不能用的,品質不好,還得去付昂貴的電費。
鄉村的烏雲像驢群一樣,灰濛濛而來,又灰濛濛而去。這一團團灰驢們,先是在天空散步、啃草,後是交頭接耳,交流思想,再是聚攏合併,然後,才在天上開始任意馳騁。驢腿間的最好距離是:疏可跑驢,密不透風。像齊派的篆法。
久旱的禾苗在下面都靜靜地蹺著腳,呆望著,等待一場雨水的滋潤,內心喊渴。像你當年在六樓下焦急期待情人跫聲的那種心情。
大地頓時開始熱燥。
忽然,這個動詞就出現了,在北中...
〈打 豁〉
是說閃電。
只有鄉村的閃電,才配稱得上「打豁」。城市裡的閃電是不能用的,品質不好,還得去付昂貴的電費。
鄉村的烏雲像驢群一樣,灰濛濛而來,又灰濛濛而去。這一團團灰驢們,先是在天空散步、啃草,後是交頭接耳,交流思想,再是聚攏合併,然後,才在天上開始任意馳騁。驢腿間的最好距離是:疏可跑驢,密不透風。像齊派的篆法。
久旱的禾苗在下面都靜靜地蹺著腳,呆望著,等待一場雨水的滋潤,內心喊渴。像你當年在六樓下焦急期待情人跫聲的那種心情。
大地頓時開始熱燥。
忽然,這個動詞就出現了,在北中...
»看全部
作者序
有一次,與梁實秋先生聊天,論到時下報紙副刊散文寫作之拉雜冗長,毫無警拔醒目之處。梁先生笑而不答,講了一個故事。
話說抗戰時在重慶北碚雅舍,物資十分緊張,梁先生因為在國立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和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較有能力在假日請同仁好友來打打牙祭,菜色換來換去,老是在辣椒豆干炒肉絲,或紅燒辣子雞塊之類的家常小吃中打轉,不過每頓必以他的拿手絕活,蘿蔔排骨湯,做為壓軸,只見大家夥呼嚕而上,吹吸而光,湯鍋迅速見底,歡迎寫在臉上。
有一位客人臨走時,好奇的問梁先生說,別人的蘿蔔排骨湯,也喝過不少,但...
話說抗戰時在重慶北碚雅舍,物資十分緊張,梁先生因為在國立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和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較有能力在假日請同仁好友來打打牙祭,菜色換來換去,老是在辣椒豆干炒肉絲,或紅燒辣子雞塊之類的家常小吃中打轉,不過每頓必以他的拿手絕活,蘿蔔排骨湯,做為壓軸,只見大家夥呼嚕而上,吹吸而光,湯鍋迅速見底,歡迎寫在臉上。
有一位客人臨走時,好奇的問梁先生說,別人的蘿蔔排骨湯,也喝過不少,但...
»看全部
目錄
冰塊擊流星(序) 羅青
第一帖◎土語匯
後晌
打豁
砍刀
雲磨
栽嘴
支愣
井畔涼水
老鴰枕頭
龍抓了
老母豬
翻嘴
雨住了
下眼皮腫
抖毛兒
雨汗
吃杯茶兒
水馱車
得拉著
肉
黃葉
鵝毛大片
結記
掌
扯淡
拋撒
漫地
形易
叉火
早辦
徐顧
格地地
乾噦
突碌
鱉囔
搉人
紅脖雁
光棍兒
扒查
囫圇葉兒
口
拱地牛
風掀
跩
斟到
嬔
第二帖◎草木劄
對草的另一種闡釋
「花生裡有曹操」帖
一棵草的重量
樹上垂掛的聲音
坐在羊背上的小人
曼陀羅.孫二娘配藥
狗的版本
菟絲子,如愛的纏綿
香附的記憶.地下暗香
茅,落在時間最深處的雪,可以療傷
草垛的...
第一帖◎土語匯
後晌
打豁
砍刀
雲磨
栽嘴
支愣
井畔涼水
老鴰枕頭
龍抓了
老母豬
翻嘴
雨住了
下眼皮腫
抖毛兒
雨汗
吃杯茶兒
水馱車
得拉著
肉
黃葉
鵝毛大片
結記
掌
扯淡
拋撒
漫地
形易
叉火
早辦
徐顧
格地地
乾噦
突碌
鱉囔
搉人
紅脖雁
光棍兒
扒查
囫圇葉兒
口
拱地牛
風掀
跩
斟到
嬔
第二帖◎草木劄
對草的另一種闡釋
「花生裡有曹操」帖
一棵草的重量
樹上垂掛的聲音
坐在羊背上的小人
曼陀羅.孫二娘配藥
狗的版本
菟絲子,如愛的纏綿
香附的記憶.地下暗香
茅,落在時間最深處的雪,可以療傷
草垛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馮傑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4-01 ISBN/ISSN:978957444834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