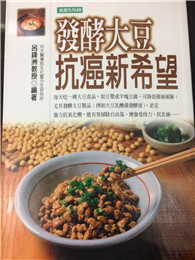作者序
我們心中,都有一枯一榮的樹(節錄)∕林清玄
輝煌,或是荒蕪之心
夜裡,我在丹東散步,沿著鴨綠江。
已經是秋冬之交,江面上漂浮的不是鴨,而是滿天的寒意。
丹東是少見的夢幻之城,隔著鴨綠江,這邊是中國,那邊是北韓。
在我散步的這邊,是人口超過兩百萬的大城,處處高樓大廈,燈火輝煌。尤其是沿著江邊,因為風景優美,蓋了許多大飯店,也聚集了許多商家和餐廳,丹東人喜歡到江邊吃飯,沿著江邊散步。
但是,那種美好的感覺,只要往江邊對岸一瞥,就立刻熄滅,令人感到驚悚了。
對岸是一片荒蕪與漆黑,只有徹骨的寒涼,沒有燈光,也沒有人聲、更沒有笑語。
每隔一百公尺就有一座守邊境的崗哨,連崗哨也沒有燈,在深沈的黑暗中,彷彿是一塊一塊的墓碑。
鴨綠江沒有想像中寬闊,尤其是冬季枯水期,江面只有十幾米,彷彿幾步就能跨越。咫尺天涯,卻是巨大的鴻溝,想要從北韓跨到中國,隨時都可能被射殺。
「從中國到北韓,容易多了,不必走江面,走鐵橋,五分鐘就到了。」丹東朋友說:「到那邊吃個飯再回來,價錢只要中國的十分之一。」
我看見那鐵橋了,僅容一部車通過,中間各設一個崗哨,中國這頭,鐵橋像是嶄新的,漆得黑亮;北韓那一半的鐵橋,年久失修,一片鏽蝕。
「那個國家窮到連邊界的油漆也買不起。」丹東朋友說。
一條江,分隔兩個世界;一條橋也切割成兩個世界。
我想起這幾天都在江邊的餐廳吃飯,餐廳是中國老闆開的,僱用的卻是北韓少女,還留著很強烈的鄉土氣息,老實可愛,她們一早從北韓用卡車載來,晚上再以卡車載回,早晚點名,管制很嚴。
她們工作的薪水,是由中國老闆直接交給北韓政府,自己根本領不到錢。
但是想來中國工作的人很多,主要是每天能呼吸自由空氣,見見世面,就是最好的報酬了。
我曾在歐洲、中南美洲,跨過許多國家的邊界,像是中國和北韓落差這麼大的邊界,卻是第一次遇到,一個國家必須以枷鎖、以射殺、以凌虐來防止人民出走,想來是可悲而蒼涼的。
呼吸著沒有邊界的清涼空氣,想到不只是國家,個人也是一樣,住在同一條江邊,有的人心中輝煌,有的人內心荒蕪。
荒蕪的人,完全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只好固守黑暗。
有輝煌之心的人,不怕流動、不怕變化,不怕上上下下進進出出,他能無所畏懼,因為他一直與美好、光明同行。
飄落的秋葉,比春花更艷紅
藥山禪師和兩個弟子在山道上散步。
禪師指著山上的兩棵大樹,一棵已經枯乾了,一棵正欣欣向榮。
他問道吾:「枯者是?榮者是?」
(是枯乾的對呢?還是欣榮的才對呢?)
道吾:「榮者是!」
(當然是欣欣向榮才對呀!)
藥山說:「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
(你看這個世界多麼清楚,世界就是這麼光明燦爛的!)
他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
雲巖:「枯者是!」
藥山說:「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
(你看這個世界多麼清楚呀!世界就是如此枯乾平淡,沒有多餘的枝葉呀!)
藥山又問剛跟上的第三個徒弟高沙彌:「枯者是?榮者是?」
高沙彌說:「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
(枯乾的任他枯乾,欣榮的任他欣榮,我只是靜觀,我不介入。)
藥山說:「不是!不是!」
公案到這裡就結束了,其餘的讓我們參。
為什麼不對呢?到底要如何才是對呢?
年輕的時候參這個公案,如墜五里霧中,到知天命之年才恍然大悟,人不應該只是靜觀,應該有感有情有靈有性,與天地一起枯榮。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甚至只是一株小草,也能探知生的消息、死的神秘,枯是榮所伏,榮是枯所倚,在枯榮之間,不能無感!
禪師本來就應該善感,否則不會覺得悟之必要,也不會寫詩偈、立公案、留語錄,更不會「大悟十幾回,小悟數百回」了。
作家本來就應該善感,否則不會在平凡中見奇絕,在不可愛中發現可愛,在不可能時創造可能。
榮是生命中的希望,對善感的人是好的。
枯是生命中的淒涼,對善感的人也是好的。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在楓林與晚霞中,觀見了,在寒霜裡即將凋零的楓葉,有一種生命的艷紅,比二月的春花還要紅,還要攝人的眼目。
愛春花者,必愛秋葉。
枯也榮也,同一體性,生命善感,必能體之。
我們的心中,都有一枯一榮的樹,成功與失敗比肩,挫折與順境相容,歡樂與憂傷並蓄。
在曲曲折折的人生,在起起落落的境遇,看的不是某一個定點,看的是我們怎麼體會,看的是我們如何觀照,看的是我們往何處追尋!
林清玄 二○一二年夏日 外雙溪清淳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