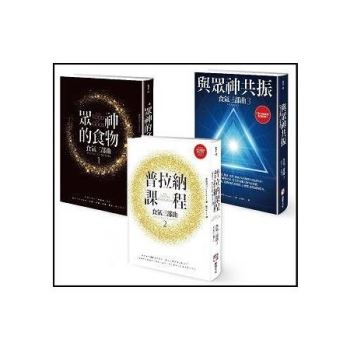視病猶親
擇時
大姑走了。
前一晚,表哥曾打電話給父親討論醫療處置,但大姑不願去醫院,逕顧交代後事。
據說晚餐還坐起來吃了一些,隔天清早,瑪莉亞準備替她梳洗時才發現她已離開,而手腳猶溫。
我想大姑定然刻意挑撿這樣的時分,當眾人熟睡,悄然抽身,讓最後一幕是純靜安詳的告別,儘管不捨。正如一直以來嚴明守分又溫婉體貼的她。
我深信那是她的好意,如同常聽到病患家屬說的:是病人自己選擇的時刻。
「媽媽不喜歡麻煩別人,所以挑我們都不在旁邊的時候走。昨晚我陪她到三點多,才去休息一下……」「二哥剛好回來,爸爸最掛念他,見過最後一面爸才放心嚥氣,也算沒有遺憾了。」「奶奶特地選星期六,全家人都在,陪著她走完最後一程。」……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劇碼,我們卻賦予共通的結論。
以及那些超乎預期的堅持或陷落。百歲人瑞在最疼愛的孫女出嫁前三月診斷癌末,兩個月後病況嚴重,我與護理師暗忖最多再一兩星期,老奶奶以其生命韌性,居然漂亮出席婚宴。陳叔是我照顧最久的安寧病人,鼻咽癌雖無法治癒,但控制得宜,唯耳聾腦鈍,連同住的媳婦都不認得,後來媳婦懷孕,陳嬸百般憂心,陳叔吃穿盥洗都需打理,已暈頭轉向,如何再照顧嬰兒?產前那月,陳叔鼻血耳膿忽然加劇,幾日便走了,料理完後事,恰迎接長孫到來。
一位出家修行的好友常說:每一個發生都是最好的。我沒能接近她豁達的境界。關於死亡,關於失落,我無法奉上「好」字。只是在百般不好萬般不願中,我還是說服自己:大姑為了所愛的家人,選好時辰,好好地走了。這樣想,沉痛似乎減輕了一毫克。
怎麼會是她
表姊問我:胰臟癌第四期,還能活多久?胰臟癌在癌症當中預後不佳,第四期也就是有遠端轉移的最末期,我雖不是腫瘤科醫師,但一般醫學常識已足夠判斷,平均不超過一年吧。
是她的朋友。「怎麼會是我?」生病後第一次見到表姊,她劈頭就說。表姊這位朋友長得漂漂亮亮,個性活潑開朗,卻不曾結婚,始終獨力工作,獨立生活。如今每兩星期要去做一次化療,她並未讓公司知道病情。表姊問她:繼續上班感覺比較好嗎?原來她也想休息,可是怕錢不夠用。
「她怎麼會得胰臟癌呢?既不抽菸,也不喝酒,生活規律,茹素多年,更離譜的是去年健檢才做過腹部超音波檢查無異狀,胰臟癌指數也正常。」表姊不解。胰臟位居腹腔隱蔽位置,易被肝腸阻撓影響超音波判斷,而癌症指數更無法保證什麼。我並費勁說明癌症成因之複雜。目前證實菸酒及油膩飲食與胰臟癌有關,但不曾吸菸難道沒吸過二手菸?葷素並不代表含油程度,餐飲店的素食烹調為了口感及飽足感,油脂和添加物往往超出葷食;還有許多未釐清的致病機轉……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染色體,決定未來大半的健康狀況,例如某些型態的乳癌及大腸癌有家族性傾向,若是天命如此,往往再多努力也是白搭。但大部分不那麼強勢的疾病基因,還是端看你如何保養,食衣住行育樂都有關係,縱使父母患高血壓、糖尿病,若能清淡飲食、規律運動、保持身材,也有倖免的機會。總之所有的疾病,要不就先天不良,要不就後天失調,要不就兩者兼具。這樣的結論實在是廢話。
怎麼會是她?但當醫師無知或無能的底線即將被觸碰,還是會搬出這套疾病成因金三角──體質不全,生活習慣不好,環境不佳。
視病猶親
外科教授的母親中風住院,腦部缺氧影響吞嚥功能,插上鼻胃管,內科醫師囑咐禁止由口進食。教授來探病時買了一碗粥,說母親如此清醒,又喊肚子餓,沒道理不讓她吃。第二天,她便因嗆咳造成吸入性肺炎。
特等VIP也不見得能得到最好的醫治,他們會被安排到幽靜隱僻的套房,擁有卓越齊全的醫療團隊,或許成員有三五位醫師,開會討論用藥,腫瘤科醫師建議施打甲抗生素;腎臟科認為甲藥會危及病患腎功能;感染科提出:病患發燒和癌症本身有關,非尿道發炎……。沒有共識的醫師,誰都擔待不起萬一的風險,因此你退一步我讓三分,處置配方不過是拼湊各方意見,互相牽制妥協而成。
阿姨每回向我諮詢她的疑難雜症,我總支支吾吾,與我對病患侃侃解釋模樣大相逕庭。面對親愛的人,我實在無法用「體質」、「環境」、「與症狀和諧共存」等推託之語搪塞。
澳洲從事安寧照顧多年的靈性大師來台演講,述說了許多令人鼻酸掬淚的真實案例,聽眾問大師如何能長期面對悲傷痛苦的病人及家屬,傾聽並付出同理心而不至崩潰?大師回覆:只因他們不是我的親人。
所以我未曾將「視病猶親」定為目標。我更無法像早年來台的傳教醫師蘭大衛的妻子那樣,切下自己的肌膚,供病童潰爛傷口補皮之用。
話說回來,大部分病人都明理,行醫這些年,我極少碰到病患要求醫護人員把他當自己家人照料。他們所渴求的,不過是醫生能將他看作是「人」,有血有淚,有尊嚴有價值,還有一個清清楚楚的名字。
聾啞夫妻
實習那年,在內科病房認識一對聾啞夫妻。那丈夫因中風後遺症反覆住院,小他二十多歲的妻子隨侍在旁。夜裡偶有些不適,護士會請值班醫師處理。我到病床邊,啞妻便指指丈夫的肚子,再抱著自己肚子、弓起身,告訴我他是腹痛;或者裝出咳嗽的樣子,再比比丈夫。
後來我離開內科,按時程表繼續婦產、小兒、外科實習,偶在院內碰見他們,啞妻總開心與我招呼。
兩年後我輪值急診,有日聽見隔壁床簾內傳來主治醫師的聲音:「病人骨質疏鬆太嚴重,才會經你一按摩就折斷肱骨。你是他們的鄰居喔?那你跟他們解釋說:手斷了,要住院。」說罷便拉開床簾離去。站在最裡頭的啞妻抬頭正好見到我,高興地跑過來摟著我跳,右手在眼前來回移動、表演哭泣表情,好心鄰居則像闖禍的孩子般低著頭直道歉。護士看到這情景,吃驚問是否病人為我的親戚,我告訴她是從前照顧過的患者。她似乎卸下重擔:「妳會手語吧?那就麻煩妳說明了。」隨即拉上床簾,發出唰的一聲。
我走到病床邊,拉過啞妻,用右手圍著左臂繞一個大圓代表石膏,然後豎起大拇指,拍拍胸,請她安心。啞妻再度抱了抱我。
簾外人聲雜沓,機械音此起彼落,逼逼叭叭,鏗鏗鏘鏘……我卻感覺急診室比聾啞夫妻的世界更加沉默。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天使在值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2 |
散文 |
$ 205 |
現代散文 |
$ 205 |
文學作品 |
$ 205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使在值班
醫師並非萬能,但是當醫師努力以自身的專業救助病人時,醫師與病人之間相互的信任和託付,便散發出如天使微光般的自然奇妙力量。
因為安寧領域服務的醫護人員,往往特別有愛心、耐心,林育靖選擇了安寧居家服務,她日日面對生死這個既嚴肅又沉重的課題,常自問自省,摸索行醫的方向與真諦,在他人生死交關當口,體會生之可喜與死之尊嚴。走出冰冷的白色巨塔,林育靖依然以細膩的心看世界。與父親的私密對話,因寵物的過世而不捨,百看不厭地欣賞自己孩子的相片……諸多生活細節,並未因為披上白袍而失溫。
從病房、值班室到自己的家庭,林育靖以女醫師的溫柔、為母者的堅韌,理解患者的病痛,傾聽疾病之外的心事。並透過醫者的眼睛與文學的筆觸,褪去艱深的專業知識陳述,為緊蹦的醫病關係尋求解套;她時而俏皮,時而感傷的寫人性與人情,令人會心更令人深思。
本書特色
★ 繼侯文詠、歐陽林之後,以女性醫生作家的角度,溫馨、幽默的筆調書寫醫者與病患間的情事。
★ 多篇文章列為醫學系討論課程之指定閱讀教材。
★ 作品曾獲2011年行政院健康好書悅讀健康「兒童及青少年健康」讀物。
作者簡介:
林育靖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畢業,現為家庭醫學科與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散文作品發表於各報刊雜誌,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南華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入選年度散文選,文章列為醫學系討論課程之指定閱讀教材。
章節試閱
視病猶親
擇時
大姑走了。
前一晚,表哥曾打電話給父親討論醫療處置,但大姑不願去醫院,逕顧交代後事。
據說晚餐還坐起來吃了一些,隔天清早,瑪莉亞準備替她梳洗時才發現她已離開,而手腳猶溫。
我想大姑定然刻意挑撿這樣的時分,當眾人熟睡,悄然抽身,讓最後一幕是純靜安詳的告別,儘管不捨。正如一直以來嚴明守分又溫婉體貼的她。
我深信那是她的好意,如同常聽到病患家屬說的:是病人自己選擇的時刻。
「媽媽不喜歡麻煩別人,所以挑我們都不在旁邊的時候走。昨晚我陪她到三點多,才去休息一下……」...
擇時
大姑走了。
前一晚,表哥曾打電話給父親討論醫療處置,但大姑不願去醫院,逕顧交代後事。
據說晚餐還坐起來吃了一些,隔天清早,瑪莉亞準備替她梳洗時才發現她已離開,而手腳猶溫。
我想大姑定然刻意挑撿這樣的時分,當眾人熟睡,悄然抽身,讓最後一幕是純靜安詳的告別,儘管不捨。正如一直以來嚴明守分又溫婉體貼的她。
我深信那是她的好意,如同常聽到病患家屬說的:是病人自己選擇的時刻。
「媽媽不喜歡麻煩別人,所以挑我們都不在旁邊的時候走。昨晚我陪她到三點多,才去休息一下……」...
»看全部
目錄
輯一 百分之一的差別
同名不同性
非常空窗期
等你到了我這年紀
禮尚往來
妹妹穿耳洞
百分之一的差別
鼻鬥言
大開殺疥
寵物之死
寫真人生
佛像店夫妻
輯二 女醫師值班室
醫生聽話
葬式後
行醫的人
必也正音乎
抗,癌
一樣素養百種人
乖寶寶印章
女醫師值班室
感性保健品
不能說的秘密
診斷練習曲
奉茶
戒菸
急中生智
尿,遁
春蘭
多活一天
耐心面試
自然難返
母親節的情感收放
贖
善終
輯三 視病猶親
臨終信仰
人生父母養
神明的旨意
真面貌
無知的權利
飛越邏輯的藥價
醫科哪一科
視病...
同名不同性
非常空窗期
等你到了我這年紀
禮尚往來
妹妹穿耳洞
百分之一的差別
鼻鬥言
大開殺疥
寵物之死
寫真人生
佛像店夫妻
輯二 女醫師值班室
醫生聽話
葬式後
行醫的人
必也正音乎
抗,癌
一樣素養百種人
乖寶寶印章
女醫師值班室
感性保健品
不能說的秘密
診斷練習曲
奉茶
戒菸
急中生智
尿,遁
春蘭
多活一天
耐心面試
自然難返
母親節的情感收放
贖
善終
輯三 視病猶親
臨終信仰
人生父母養
神明的旨意
真面貌
無知的權利
飛越邏輯的藥價
醫科哪一科
視病...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育靖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10-01 ISBN/ISSN:978957444846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