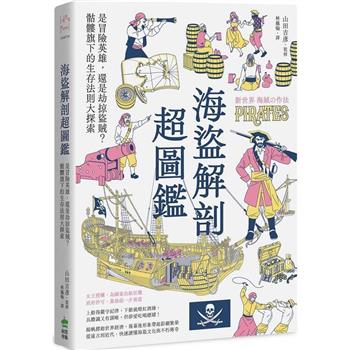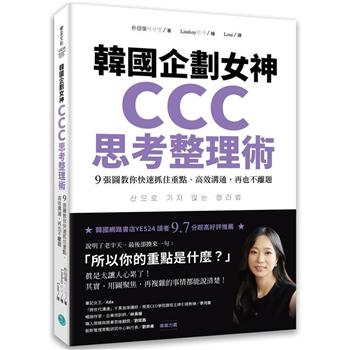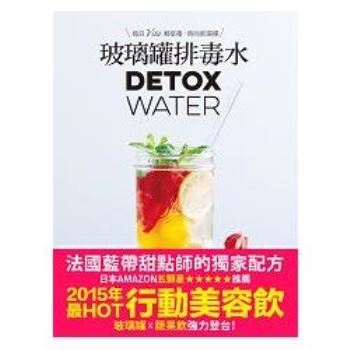「就因為世界在標準化,人們才渴望補玉山居。」
.入圍2012年中國影響力圖書評選候選書目
.嚴歌苓親自改編電視劇,改編版稅為中國史上最高
癱瘓的億萬富翁叱吒商場、心狠手辣,卻又為何心碎憔悴終至絕食?
一個夢想成為灰姑娘,從小村子到沿海大城市做代工的美麗女孩,命運能對她多殘酷?
昔日的連長與美麗的女軍醫,兩人中間橫亙著一場輕於鴻毛的死亡,成了他們心上永遠的疙瘩。
一個人在大城市裡沉沒是悄無聲息的,卻都能在「補玉山居」尋到一丁點兒心靈的慰藉。
位於北京近郊山村中,小小的農家民宿「補玉山居」宛如世外桃源。老闆娘曾補玉憑著高超的經營手腕,吸引了大城市中壓抑的人們湧入此地,花錢買自由和解放。人們在此塑造全新的自己,和真實生活拉開距離,圖個暫時的喘息;任憑精明伶俐的老闆娘如何慧眼識英雄,也看不穿一張張假面下驚心動魄的來歷。
作家、毒販、精神病患,三教九流在這個舞台輪番上場……嚴歌苓幽默犀利的筆鋒,寫出小人物的史詩、大時代的縮影。
本書特色
★ 嚴歌苓在台睽違四年的最新作品,轉而關注當下,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此書透視當代中國社會,為變遷中國的縮影。
★ 延續嚴歌苓一貫人性刻劃的功力,情節更扣人心弦,筆鋒也多了些以往少見的幽默犀利,畫面感則更強烈,不讀到最後完全無法猜到結局。
作者簡介
嚴歌苓
一九五八年出生於上海,先習舞,再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九○年獲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獎學金,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美,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攻讀英文文學寫作碩士。
多部小說如《少女小漁》、《天浴》、《白蛇》、《金陵十三釵》屢被改編為電影。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長篇小說分獲聯合報長篇小說評審獎、中國時報百萬小說評審獎,被譽為「今天華文創作最細膩敏銳的小說家」。近期名著有《第九個寡婦》、《無出路咖啡館》、《海那邊》、《一個女人的史詩》等多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