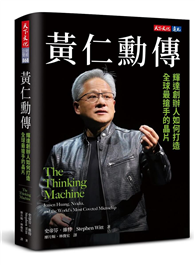老爬蟲的告白
面對著稿紙度過半生,寫作對我而言,不是行業也是行業了,有時候認真去追想,我為什麼成為一個專業作者的呢?說來是非常荒謬,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小時候我喜歡聽說書、看野台子戲,沉迷到廢寢忘食的程度。有些比較知名的說書人,都在茶館裡設有固定的場子,聽書的人可以泡盃茶,翹起二郎腿,大模大樣的坐著聽,說書的人每說到精采之處,就停頓下來,由他的助手端著盤子請賞錢,通常一個晚上,都要收上兩次錢。我去聽書,既不泡茶,又不給賞錢,完全是白聽,一看到有人端盤子請賞,就退到門外去,等他收完了錢再回轉來。有些流動的說書人,總是揀著逢集的日子,在街頭巷尾找一場空場子,口沫橫飛的說起來,而聽的人既沒茶喝,又沒座位,大都蹲在自己腳跟上,手托著腮,癡癡迷迷的聽下去;凡是有人說書的地方,總少不了我就是了。
至於看戲,我可看得多啦!山東戲、河南戲、江淮小戲、黎園的大戲,加上唱道情的,唱大鼓的,唱小曲的,打蠻琴的,甚至巫童巫婆行關目,我是有戲必看,白天聽的看的,都帶到夜晚的夢裡去,常常幻想自己也是書中和戲裡的人物,當然是什麼武曲文曲、青龍白虎之類的星宿臨凡嘍。
在聽書看戲之外,我還迷著聽人講古記兒,不論是悲的、喜的、恐怖得使人脊背發麻的,我都喜歡聽,每天夜晚,要是不聽一長串的故事,簡直就睡不著覺。
那些民間藝術和傳說故事,給我的影響是深鉅的,它使我充滿了歷史性的幻想,總脫不了忠孝節義、離合悲歡那種調子,而且把自己也放在裡面,扮演一個自己屬意的角色——當然是主角了。
後來,發現家裡的藏書,裡面附有插圖,我雖然看不懂文字,但繡像人物卻看得出是誰來,尤其是說書人說過、戲台上演過的,便更熟悉了。為了想探究書裡究竟寫些什麼,我對認字塊兒的興趣愈來愈濃,沒入塾之前,我已經從文盲變成粗識文字,能夠吃力的啃書了。我最初所啃的書,從三皇五帝到清末的通俗演義類的作品,差不多都看過,尤其對唐宋兩個朝代的演義,特別熟悉,有人說:「唐書步步錦,宋書朵朵花」,表示它們精采熱鬧,我當然是喜歡湊熱鬧的了。
演義類的作品,悲劇感不深,英雄們死了沒什麼,祇是星宿歸位而已,什麼青龍四轉世,白虎三投唐,這本書裡的人物死了,翻到那本又出來了,仍然是一條好漢,這當然也是一種過癮,因為凡是星宿臨凡的人物,閻羅王管不著,死後不必下地獄,直接升天,真是羨煞人也。
不過,等我再讀到一些由民間傳說寫成的悲劇時,味道就不一樣了,俗說:逢「記」必苦,像《牙痕記》之類的書,讀來真正苦進骨縫,而那些苦況,都是沒良心的人——尤其是狠心男人造成的,偏偏我又是男人,發狠日後長大了,不能把良心扔去餵狗,做一個死後還被人痛恨的人,立誓自歸立誓,長大之後檢討自己,雖不挺壞,也不算好,直接升天歸位已經沒我的份了,地獄恐怕還是要去走上一遭的,閻羅王審問我,一定會加上寫書害人這一條,汙了許多讀者的眼,迷了不少讀者的心,罪莫大焉,上刀山下油鍋跑不了啦。但世上既有創作這個行業,我不寫就沒飯吃,只好先顧眼前的現實了。其實,人世間的生老病死苦,實在夠受,刀山油鍋的滋味,不必到地獄去,照樣品嘗得到,抗日和剿匪期間,我們受的苦,一樣可以寫成什麼什麼記,讓後世人也為我們灑幾粒眼淚。
我進塾唸書,先跟一個淮和尚唸,背誦是背誦了,但書的內容我根本不懂,他再解釋,我還是一腦門子漿糊,後來跟一個貢生吳老先生唸書,那位先生講得非常好,深入淺出,還打了許多讓人能夠領會的比方,懂是一回事,有無興趣又是另一回事,我對經史子集的興趣,遠不及通俗坊本小說有興趣。不過,通俗小說和戲劇看多了,總不能反覆再看,我的興趣又轉到新文學作品上了。
抗戰期間,不論是淪陷地區或是游擊地區,如果不是在大都市裡,書本都是稀少又珍貴的,偶爾見到一兩本,也被人翻爛了,有時沒有封面,連頭尾都殘缺不全,像雜誌和報紙,沒有什麼定期的,找到一本算一本,找到一份算一份,尤其是副刊上的好文章,都是轉輾抄錄下來的,那時,我在地下補習班,上國文課沒有課本,老師把一篇文章寫在黑板上,大家跟著抄,文章有古有今,新文學作家的散文,我就是那樣接觸的。我的一位堂兄讀過農校,他有個愛好新文學的同學到大後方去了,留下幾箱書籍,寄放在我家鄉下的農莊裡,我逃難下鄉找到那些書,真是如獲至寶,便吃力的硬啃起來。那些書籍,多是五四之後新文學作品,有些作品的名字很生冷,內容也不算好,少數是知名作者的作品。那位張先生收藏這些書,讀得很仔細,有許多地方,都做上眉批眉註,寫出他的感想,還在一冊描寫戀情的長篇小說扉頁,寫下「美人黃土,名士青山」的話,他的毛筆字寫得細瘦挺拔,給予我極深刻的印象。
抗戰烽火擴大了,我們四處逃難,在流浪中,我仍然不斷的讀到一些文學作品,也熟悉了當時一些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的名字;在當時,我對新文學作品談不上專一的愛好,由於日軍封鎖的關係,我們沒有選擇閱讀哪一類書的機會,找到什麼,只要是有字的東西都願意看,讀得很零碎、很廣,也很雜亂,一部分翻譯小說,也都是那時候看的。
看書看上了癮,對聽說書和看戲的興趣就減低了,因為說書的所說的那幾部書,有時誇張過度,甚至部分段落渲染過甚,沒有看原書過癮。戲呢?在兵荒馬亂的年頭,也沒有什麼好的戲可看,倒是真實的人間那些死別生離,要比戲台上演的更感人得多了!抗戰期間的許多文學作品,反映了戰亂的生活,多角度的顯陳,在在撼動了我,我時常感覺到內心也有很多話要吐述出來,讓別人聽一聽,假如用文字去表達內心,是我不敢企望的,我從來沒夢想過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個作家,但學習和嘗試的心倒很強烈,那麼就從頭做起吧。
我的學習寫作的簿本,是自己找些單面有字的紙張打翻後釘成的,到東到西都帶在身邊,一面閱讀汲取,一面學著塗鴉,最早常寫些摹仿性的東西,也是雜亂無章的,比如說,讀了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話,我就學著寫童話,讀了平江不肖生和王度盧、鄭證因的武俠小說,也學著寫武俠,讀了戴望舒、朱湘的詩,也就學著寫詩,寫完了,自己看著都覺得臉紅。
到了抗戰末期,我對閱讀的作品逐漸有了偏向性的選樣,比較喜歡讀小說類的作品,尤其是舊俄作家那些滿懷人道悲情的作品,給我極深的感染,那些書本,彷彿是一座座雄偉而莊嚴的精神建築,把希望的種子,埋藏在多難的人間。也許是生存的年代、生活的環境影響吧,使我對各類型的人間悲劇特別敏感,因此,在我習作題材的取擇上,多半都以悲劇性的事件為主,至於表現得如何,那又另當別論了。
在摸索的日子裡,我都是孤獨的,沒有同好的朋友和我切磋,也沒有前輩給我指引,整整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既沒有成績,又沒有信心,祇有生活帶給我的感覺在我內心積蓄著,有想衝瀉又無法衝瀉之感。這種痛苦,到了來台之後,有了顯著的改變,在軍中的夥伴裡面,我發覺愛好文學藝術的朋友一下子增多起來,而且其中不乏頗具素養的,我們在操課之餘,把所有能利用的時間都用上,跑圖書館,逛書店舊書攤,用微薄的餉錢去買書,彼此交換著閱讀,並且互相討論。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設立,早期的一些文藝刊物的誕生,對我們的鼓舞極大,投稿必須要有適當的園地啊!
五四的時代過去了,在這個島上,我們必須重新作精神的墾拓,今後的文學往何處去呢?那是我們頂著星和月,坐在帶露珠的草地上研究探討的主題,那時候,僅有少數在大陸上就為我們所知的老作家,像蘇雪林、王平陵、孫陵、陳紀瀅、謝冰瑩……等人,緊接著,文獎會的刊物和書籍,又不斷推出一些新的名字和新的作品,像潘人木、徐文水、端木方、方曙、潘壘、李莎、郭嗣汾、墨人,這些作家有部分是服務軍中的,那充分表示出一種意義,就是說:當兵的除了拿槍上陣,一樣能用筆描摹出內在的情神感受來。
當時在南部三軍裡,愛好寫作的朋友很多,像楊念慈、彭邦楨、朱西寧、段彩華、馬各、桑品載、李冰、沙塵、蕭颯(男)、王牧之、羊令野、王默人、高岱、洛夫、唯弦、張默、彭品光、疾夫、阿坦、金刀、朱門、郭嗣汾、墨人、舒暢、張拓蕪,還有些軍眷作家像郭良蕙、丹扉、郭晉秀……多得一時無法逐一列舉了,人說:物以類聚,這些朋友早年並不相識,但彼此在寫作過程中相互傾慕吸引,慢慢的都熟悉起來,並且都成為老友了,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自由中國文學藝術發展到今天這樣蓬勃,以上那些早期文壇開拓者的心血和勞績,應該是被記憶的,也就是說,早期文壇的開拓,除了社會作家的努力外,軍中作家的全力投入,實在是一股不可忽視的主要力量。
對我個人而言,這些朋友對我的鼓舞和啟導,助我建立信心,更勝過我所讀過的書本,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用創作作為精神上的呼應,不管我們身在何處,能否常相聚首,我深信祇要我們還在呼吸,我們的心是一致的,為了一個理想的中國,為了合理的人類社會,我們自會和繼起的文藝精英匯成一體,盡力的寫下去、做下去,創作量的多寡、作品成就的高低是個人的事,但誠懇努力的心是相同的。
幾十年如一日,我守著夜和燈,思想、閱讀和寫作,從不曾厭倦過,懷著學習心情的人是不會厭倦的,唯有自滿才會逐漸的貧弱乾涸,我常這樣的自問:「司馬,你算得了一個作家嗎?」回答是肯定:「不!作是作了一點,離『卓然成家』還差十萬八千里,要學的還多得很哩!即使匍匐終生也學不完的。」正因如此,我才用生活作為燃料,像一輛重型坦克般衝向前去,一千萬字,兩千萬字,三千萬字……直到用原稿砌成一座高樓,別人接不接受我我管不著,我能獨自坐在原稿的樓屋裡「孤芳自賞」也就夠了,人為自己的理想盡了力,還有什麼它求呢?王大空先生寫一本書,叫《笨鳥慢飛》,而我這陸軍出身的人是沒有翅膀的,既不能飛,祇有改以「笨龜慢爬」去形容了!儘管前面山遙路遠,能不斷爬下去總是好的,要是抱著幾本自己的書,作「烏龜曬蛋」,那就永遠到不了啦!這種認定,有時還被讀者誤認為過分謙虛,其實,它正是我拚命寫下去的主要理由,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我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些得自書本,有些源自生活,總括說來,知識、友情、生活和感悟,使我的精神能夠不斷成長,我能夠用筆去表現的,僅僅是這種成長的過程罷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老爬蟲的告白(增訂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237 |
文學作品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老爬蟲的告白(增訂新版)
司馬中原的腦袋就像一口裝滿好聽故事的百寶箱,隨手打開,古老中國傳奇,不論是人是鬼,他寫得栩栩如生,說得繪聲繪影,筆下的人物早成了許多人記憶的一部分,熟悉一如故友。他的小說和散文,都充滿了史詩性,抒情的或鄉野傳奇等特色。
寫作爬格子爬了大半輩子,司馬中原自譽為「老爬蟲」,在這本「告白」中,他像說書人一般,創造出最迷人的鄉野傳奇,以趣味之筆寫居家生活,更細數成長的歡愁歲月,走入不同的時間空間,跟著司馬中原的筆,尋找、創造生命不同的美與真。
本書特色:
★ 精選《月光河》、《駝鈴》、《精神之劍》三本散文集中美與真的精品。
★ 特收錄司馬中原撰寫新版序,漫談寫作經驗。
作者簡介:
司馬中原
本名吳延玫,曾獲「第一屆全國青年文藝獎」(《荒原》),獲「教育部文藝獎」、「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第一屆十大傑出榮民獎」、「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特別貢獻獎」、「國家文藝獎」(《春遲》)。
著有小說集《狂風沙》、《荒原》、《春遲》等,散文集《鄉思井》、《月光河》、《雲上的聲音》、《司馬中原笑談人生》等,其中多部改編電影,如《路客與刀客》、《大漠英雄傳》、《鄉野奇談》等,均為觀眾所喜愛。他的散文〈火鷓鴣鳥〉被選入國中課本。近年也為孩子寫故事,著有《司馬中原童話》、《司馬爺爺說鄉野傳奇》。
章節試閱
老爬蟲的告白
面對著稿紙度過半生,寫作對我而言,不是行業也是行業了,有時候認真去追想,我為什麼成為一個專業作者的呢?說來是非常荒謬,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小時候我喜歡聽說書、看野台子戲,沉迷到廢寢忘食的程度。有些比較知名的說書人,都在茶館裡設有固定的場子,聽書的人可以泡盃茶,翹起二郎腿,大模大樣的坐著聽,說書的人每說到精采之處,就停頓下來,由他的助手端著盤子請賞錢,通常一個晚上,都要收上兩次錢。我去聽書,既不泡茶,又不給賞錢,完全是白聽,一看到有人端盤子請賞,就退到門外去,等他收完了錢再回轉來...
面對著稿紙度過半生,寫作對我而言,不是行業也是行業了,有時候認真去追想,我為什麼成為一個專業作者的呢?說來是非常荒謬,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小時候我喜歡聽說書、看野台子戲,沉迷到廢寢忘食的程度。有些比較知名的說書人,都在茶館裡設有固定的場子,聽書的人可以泡盃茶,翹起二郎腿,大模大樣的坐著聽,說書的人每說到精采之處,就停頓下來,由他的助手端著盤子請賞錢,通常一個晚上,都要收上兩次錢。我去聽書,既不泡茶,又不給賞錢,完全是白聽,一看到有人端盤子請賞,就退到門外去,等他收完了錢再回轉來...
»看全部
目錄
處處展現心志、人格與風格
——司馬中原其人其文
司馬中原小傳
輯一 故 事
磨 坊
雁
晝 夜
古老的故事
開 槍
軍閥過年
伏莽之春
蛇的集錦
輯二 浮 生
笑的藝術
哭的藝術
大兵文書
無河之獅
閒話打呼嚕
文章摻水論
我的寫作生活
老爬蟲的告白
養貓記
回 首
臭棋的樂趣
生命的重量
自由的約許
浮 生
握一把蒼涼
辭歲篇
劫嬰記
旅遊之後
輯三 時 光
我的少年時代
習字的滄桑
家 宅
寒 夜
廟
倚 閭
梧 桐
舊 夢
沼 澤
月光河
蟋 蟀
蠶
撿遺集
風 聲
附錄
...
——司馬中原其人其文
司馬中原小傳
輯一 故 事
磨 坊
雁
晝 夜
古老的故事
開 槍
軍閥過年
伏莽之春
蛇的集錦
輯二 浮 生
笑的藝術
哭的藝術
大兵文書
無河之獅
閒話打呼嚕
文章摻水論
我的寫作生活
老爬蟲的告白
養貓記
回 首
臭棋的樂趣
生命的重量
自由的約許
浮 生
握一把蒼涼
辭歲篇
劫嬰記
旅遊之後
輯三 時 光
我的少年時代
習字的滄桑
家 宅
寒 夜
廟
倚 閭
梧 桐
舊 夢
沼 澤
月光河
蟋 蟀
蠶
撿遺集
風 聲
附錄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司馬中原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5-01 ISBN/ISSN:978957444881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