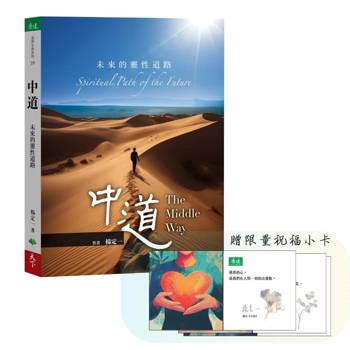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死亡練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恐怖\驚悚小說 |
電子書 |
$ 196 |
恐怖\驚悚小說 |
$ 221 |
現代小說 |
$ 22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1 |
文學作品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小說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死亡練習
彷彿生出翅膀的女人。
身後跟著小恐龍的女人。
不斷夢見河與魚的女人。
以及反反覆覆聽見鸚鵡叫聲的女人。
十四位黃美美,十四則或冰藍或翠綠或黑墨的風景。
以《親愛練習》深獲好評的張耀仁,這次透過十四位黃美美,揭露「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遭遇的屈辱、欲望、寂寥乃至對命運的不甘與拚搏,是《親愛練習》外籍移工的對位關係,更是「異鄉人系列」的延伸。
一樁又一樁商品化的跨國婚姻,來自異國的女性遠離早已慣習的語言、文化、家庭,投入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並且不斷遭男性沙文主義(Chauvinism)所扼。在權力、社經地位皆不對等的情況下,無從發聲也無從反駁,她們的功能除了勞動,只剩下傳宗接代。終日困坐於井,也終日引頸企盼,只能細長而悠遠的吟唱:
「天茫茫,地茫茫,無親無故靠台郎。月光光,心慌慌,故鄉在遠方……」
作者簡介|
張耀仁
一九七五年生,政治大學新聞學博士候選人。現任教世新大學等校。曾於師範大學「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開設「小說創作工作坊」。
作品曾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等多種,並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曾入選年度小說選,另三年連續入選年度散文選。短篇小說多篇經中華民國筆會(The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英譯。
著有短篇小說集《親愛練習》、《之後》。散文集《最美的,最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