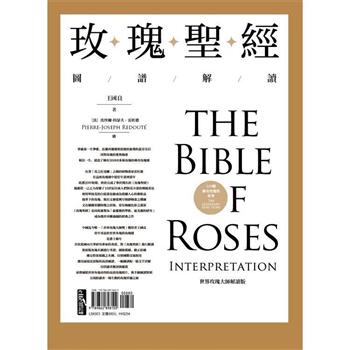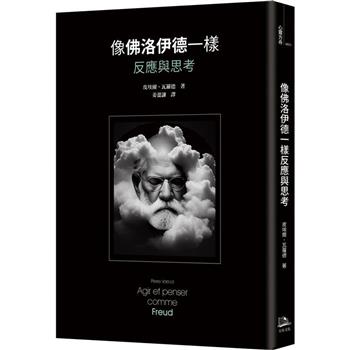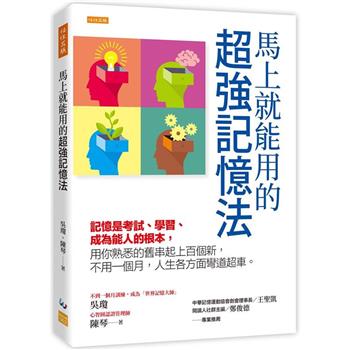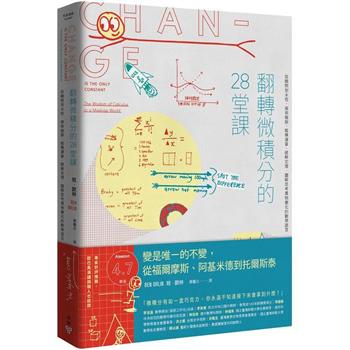序文
寫作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北港香爐人人插》的同時,其實也規劃書寫另個長篇:《路邊甘蔗眾人啃》。前者相關女性,後者著墨男人。
用來作篇名的這兩個特殊的詞語,都屬台灣流傳的俚語,非我所新創,不敢掠美。開始計劃書寫時,本來耽心寫男性的「路邊甘蔗眾人啃」易引起不必要的困擾,因而從女性的《北港香爐人人插》著手。
完全不曾想到,一場不必要的「香爐」事件,轉移探討的問題變成一場八卦風波,「對號入座」是為年度的經典名句之一。當然也不再能繼續書寫《路邊甘蔗眾人啃》,以免被認為我專門炒作這些敏感話題。
但對這未能寫成的小說,我其實十分耿耿於懷,一直想要「敗部復活」。2008年到韓國開一個「Asia Africa」會議,提出的報告,以及之後連續三年在美國多所大學巡迥演講,我更信誓旦旦的說在寫一部「男人的性與政治」的小說。
陸續寫來,離「香爐」事件已十五年,台灣社會、政治俱有了重大改變。我個人更是不可避免的得面臨因年歲漸長展現的生命中不同課題,此時來寫這樣的小說,有所沉澱,自是會不相同。
仍然感到婉惜,九○年代當時寫來,力道一定不一樣。其實應該不顧一切的先寫出來,俟適當的時機再出版,方不至有所遺撼。
就算事隔多年來寫,知道仍不免會被質疑是否合宜。我至今不曾間斷的寫了四十幾年的小說,創作是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職志,榮辱毀譽,不為所動。
我當然有我的政治認同、意識形態,但在這台灣政治變動至為巨大的十五年——我相信還可以包括過去以及將來,我小心謹慎的避開所有與政治實質相關的權位、金錢關係,為著能夠不被制約,可以無所顧慮的創作。
然仍有的制約來自小說中諸多使用事件,距今時間短暫,缺乏距離能形成的創造性空間,寫起來諸多考量不免礙手礙腳,好處却也在尚存印記。年歲漸長,已然到創作的最後階段,只有更加用心,尋求不同書寫形式來接受挑戰。
至於小說涉及的內容,為了避免《北港香爐人人插》的「對號入座」事件重演,一開始我本來還要先作明白宣言:
小說裏的男/女主人翁,那些主要的敘述者,是一個複數的集合,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是「他們/她們」,而不是「他/她」。
著眼的是往權力攀爬過程中可能的共同現象,而佈局於反對運動中,更容易彰顯權力取得的無/有過程,並非執政者與權力之間即無此呈現。尤其台灣政壇千奇百怪現象,不論執政、在野者皆如此,小說參照的,更不分政黨。
偉大的小說諸如「迷宮中的將軍」裏多聲部、多重的敘述當然深為我向往,但我無能也無意效鬢。我只有轉借為「他們/她們」,而不是「他/她」來敘說這男人的性、身體、權力與政治。
所以,特別要請不分政黨的個人勿「對號入座」,也請勿拉「他們/她們」來對號入座。
是所期盼。
2
意想不到的是下筆一路寫來,竟然發現,到處都是柳暗花明之處,還真有所不同,比如從小處寫、大量相互的隱喻等等,驚喜之餘對自己的寫作覺有所開展。
但也有新的難題得面對,相對於許多與政治相關的小說,特別是第三世界,大部份都還在抗爭的過程,少有處理到異議份子取得政權後。而這個部份,却是我想著墨之處。
台灣有了今日華人世界首見的民主,却也明說著以華文寫作的作者,尚無親身面對此的經驗/寫作,想要有所借鏡,也就很難。
便又得面對一個無人之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台灣早已不是九○年代風起雲湧的衝撞民主自由時期。整個國際局勢,連茉莉花都已經開始革命,有所成果。相較起來台灣民主化過程不曾經過政變、流血革命,算是犠牲較少,十幾年下來民主逐漸深化,也該是到了走過悲情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走過悲情方使得書寫烈士、英雄、神主牌成為可能。
寫作過程便一再轉折變化,臨近作品抵定之時,竟豁然開朗,可以大聲的說出:
歡迎前來對號入座!!!
是啊!小說本是虛構,尤其上述已一再明言《路邊甘蔗眾人啃》是一個複數的集合,如果有人還要對如此虛構的文本前來對號入座,亦屬個人自由。
特別是,寫作這部小說,基調是男人的權力與性。過往帝王與後宮,可以佳麗三千,到於今的民主時期,時間的巨大轉變,男性政治人物與性之間,女人獨立後今非昔比,演繹出來的關係具有如此多重面相——
與過往帝王/後宮相較,絕對是另類風情。
因而一個男人於今要如《路邊甘蔗眾人啃》小說中主角,有如此翻雲覆雨能力,不僅不易,還更可能被有些男人認為難能可貴,深獲不少男人賀彩,是他們的終極夢想。
此類對號入座便並非貶事,就算前來對號入座,也可能會是「與有榮焉」的對號入座吧!
那麼,也就歡迎前來對號入座。
3
更要重提《路邊甘蔗眾人啃》的姊妺舊作《北港香爐人人插》,已有英文、義大利文翻譯正在進行,期待能順利出書。《北港香爐人人插》中的「彩妝血祭」更由大法蘭克福地區的「達姆斯(Darmstadt)國家劇場」改編成為舞作,入圍有德舞蹈界奧斯卡之稱的「浮士德」獎。
前陣子有大學研究生以此小說來寫論文。事件之時我苦無媒體讓我來作辯說,只有刊載小說的報紙給了僅有的一次機會,讓我提出「請勿自己前來對號入座」。
十五年後,整個世界的女性議題重新整理,台灣亦邁歩向前更趨成熟。同樣的,《北港香爐人人插》中女主角有的翻雲覆雨能力,已然可以加以正視,更能重新探討小說中「女人藉著睡男人來獲取權力」的主題。
易卜生寫著名劇作「傀儡家庭」時,劇中娜拉離家出走追求自我,為當年衛道人士大加噠伐。易卜生憤而再寫「群鬼」,顯示娜拉如不出走留在家中,等待的是多年後長大的兒子因丈夫遺傳性的潛伏梅毒,終成白痴,整個家庭也崩散。
留下來不出走的娜拉,有的會是如此悲慘的命運。
同樣的,《北港香爐人人插》女主角林麗姿,在《路邊甘蔗眾人啃》中,成為林慧淑。不在男人/權力中翻雲覆雨的林慧淑,化身成不同於林麗姿的小說人物林慧淑,等待著她的,會是怎樣的命運?
新世紀新面相,台灣走過悲情/女性後,如不以林麗姿翻雲覆雨的能力為眨意,會不會也可能是「與有榮焉」的對號入座?
果真如此,期待一九九七年企圖探討的問題,於今終能不被八卦化,得到嚴肅的看待與討論。
4
這部小說在寫成後,面臨著要不要發表,以及何時出書。
年歲已長,老實說的確少了年輕時不顧一切的勇往直前,真的第一次考慮到:
是不是還要為一部小說,面對一些不必要的問題,尤其是台灣這十年的整體八卦化。
寫是一定要寫的,對我這種視創作如命的人,也如願的完成作品,但何時發表出書,却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比如,一段時間後,數年後,當一切都不再如此醒目,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困擾。或者是,留下遺矚,死後再發表,有困擾也地下無知。
但稍一思考,年歲越來越長,只會越來越缺乏面對的能力。留遺矚要人處理,也是另類不能面對的推委。
不就可惜了寫這部小說的緣由與心血。
這多年來台灣經濟的不景氣,台灣遠遠的落後其它的亞洲四小龍,尤其相較於中國的掘起,缺乏信心只有固步自封,絕對是形成保守主義的溫林。當一切都只要小確幸時,不要說台灣八○年代的雄心、九○年代的開拓不再,政治上的紛爭,敗象的無力解決,許多方面只有淪入細枝末節的口水中。
悶豈只是經濟面,恐怕更是整個社會集體的缺乏出路。
在台灣愈來愈趨保守的氛圍中,所幸仍有公民社會集結力量訴求改進,我決定,還是在這時間點出版這本小說。
二○一二年得「吳三連文學奬」,也的確是一種助力,最後一根稻草加在出書這一方。
至於何時出書,說來有些人一定覺得可笑。
有一天,一位有「靈感」的友人說:
「明年中,小說要出版。」
她知道我一直在寫小說,但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我問她為什麼是明年、明年中,她回答:
「就是這樣覺得。」
那一年的明年,就二○一三年出版吧!
不計毀譽,只有「聽天由命」?
作為一個小說作者,最後仍要一再的說:
《路邊甘蔗眾人啃》是一部書寫成的虛構小說。
作品訴說一切,本來無需多言。所以雖說是歡迎前來對號入座,也請一定務必看完了作品,不要像上一回《北港香爐人人插》,不少文藝圈人士,居然對只刊載了三分之一篇幅,即來對號入座的品評。
是所期盼。
附註:
由於諸多考慮遲疑不決,這本書結果拓延至二○一四年才出版。與我有「靈感」的友人所說略有出入。
卻不免驚奇發現,這小說從大概九○年代中發想要寫,卻因種種原因讓位《北港香爐人人插》先行,算起來從醞釀到出版,真正是走過整整二十年。
二○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時值農曆年大年初一,是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