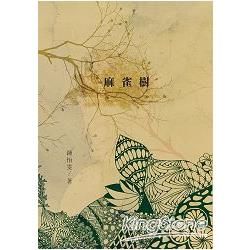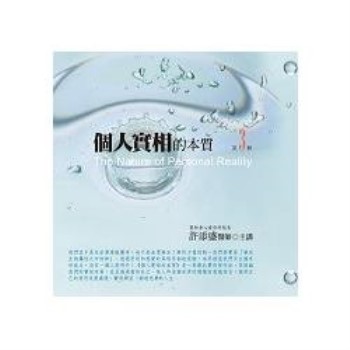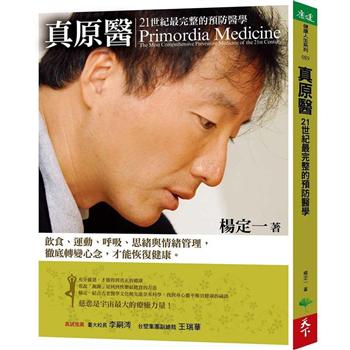種樹看貓聽麻雀,是日常
寫字睡覺走天涯,是療傷
一隻麻雀可以解放淚水,一棵樹足夠成為生活的宇宙軸心,一場旅行能認清自己的身分。鍾怡雯逃離只有夏季的熱帶雨林國度,來到四季分明的臺灣紮根生活,彷彿「兩處皆我家」,但又「皆是異鄉客」,這身分猶如黃昏介與白天與黑夜般難以劃分。然而,遭逢母親在遠方離喪變故,日常生活軌道突陷灰色地帶,透過書寫療傷,她跳脫過去,真誠面對難以釐清的身分認同。
本書以尋常生活記事、思母心情的兩地書做為開端,其後藉著遠遊,展開三地對照。看樹令她安穩彷彿腳下生根,貓兒伏枝午睡,麻雀啁啾,鄰人送菜,隔壁卡啦OK深夜高唱,這是她中壢的家,黃昏的來臨浮起過往她與母親同煲電話景象,放假的端午節遙念已無人能做的粽香滋味,夜晚躡腳來臨的夢總使她想起預示母親死亡的預告夢。當平凡的家居已無法讓她安睡、渴望自由的慾望無法壓抑,她選擇將自己丟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他方、中壢、油棕園的三方連線於是開啟,異鄉與在地的對照快速轉換,使她有另一層的體認。
還有更多的生死體悟,當時間和風景從身邊流過,無預警的告別,從時光縫隙裡掃出的塵埃與無數插曲,都在考驗著對生命的忍耐與妥協。
作者簡介:
鍾怡雯
現任台灣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豢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陽光如此明媚》、《麻雀樹》,散文精選集《驚情》、《島嶼紀事》、《鍾怡雯精選集》;人物傳記《靈鷲山外山:心道法師傳》;論文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經典的誤讀與定位:華文文學專題研究》;翻譯《我相信我能飛》;散文繪本《枕在你肚腹的時光》、《路燈老了》;並主編多種選集。
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首獎、聯合報文學獎首獎、星洲日報文學獎首獎及推薦獎、新加坡金獅獎首獎、海外華文文學獎首獎、華航旅行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及梁實秋文學獎等。
章節試閱
看樹
入夏之後,構樹成了我的生活重心,也成為鳥類的另一個活動中心。自從跟它比鄰的野桑椹被砍去大半,構樹在多雨的春天,一下長成令人側目的大樹。
這要從野桑椹說起。有一晚發現側窗亮得刺眼,湊近一看,啊,又砍樹?野桑椹從大傘變成斜傾的半邊小傘。沒有樹蔭,燈光直接穿透米色窗簾,在地板打出耀眼光影。砍成這樣未免砍得太過頭了。鄰居解釋,火蟻沿著野桑椹的樹枝爬到他家草地上,靠他家的那半邊不得不清除。
火蟻從野桑椹生長的土地,攀上兩層樓高的樹幹,沿著鐵皮屋,越過圍牆,再爬下草地?這些火蟻是變種特工隊嗎?
不是故意砍樹啦,意思是這樣。好吧。不是我的樹,我能怎樣?我家吉野櫻就要放任它長。這是我的樹。我就愛大樹。樹應該長得野野的,長出勃發的生機,長成人類無法想像,只能讚嘆的樣子。
可是那野桑椹,唉。每天在側窗發幾回呆,除了無用的嘆氣和打氣,最實在的便是給它施肥。雖然給一棵天生地養的樹做人工之事有點可笑,不過,沒有野桑椹,白頭翁可要斷糧了。對野桑椹和白頭翁而言,這是個殘忍的春天,可以聯手朗誦艾略特的詩,四月,是最殘酷的季節。
從這時開始,構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勇猛的竄生。野桑椹一定跟構樹悄悄說了什麼。望著它們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樹跟樹,可是會溝通的。
兩棵樹在我家側牆,離老厝近些,屬於卡拉OK主人。不知道從哪來的,突然長成大樹,足以庇蔭兩戶人家。如果是雌構樹,那就有好吃又漂亮的莓果,我會毫不遲疑留它。雄樹就差多了,長條的果實像紅紫色的毛毛蟲,風吹時滿樹蠕動。風雨打落之後呈棕褐色,滿地焦屍。無論毛毛蟲掛滿樹或落滿地,都很不討喜。當然,這純屬個人好惡,是我以貌取樹。構樹屬於桑科,有人說這果實是放大版的桑椹,可食用。天降果樹不懂得吃,是暴殄天物。可是,連白頭翁都只肯吃隔壁那棵小小的野桑椹,斷糧了也任憑構樹果子掉落腐爛。鳥都不吃,我犯不著去做人體實驗吧?
實際上,構樹是好樹,再貧瘠的土地都能長,強悍耐活,是製紙的好材料,又可以抗污染淨化空氣,靠我家落地生根,算是我的福氣。附近的野地裡長了不少,或許最初的壞印象,是因為它太賤生了。
是的,是這個詞,賤生,最貼近構樹的特性。小構樹小小構樹繁衍的速度簡直神奇,有一棵很快會有第二第三棵,如果不是反覆清理,後面的空地很可能長成構樹林,我家可以改名叫構樹之家。幸好卡拉OK老闆比我們還擔心老厝被掩埋,總會拔除不斷湧現的小構樹,定時修理那棵大構樹。雖然如此,樹長的速度總是超越人砍的速度,構樹林已經小有規模,或許真有那麼一天,我家會構樹成蔭。
中壢冬天最可怕的是風,我家剛好地勢空曠,只要起風,後陽臺的遮雨篷被樹枝拖拉,發出刺耳又令人牙軟的磨擦聲,好像有人粗暴磨大刀,故意凌遲耳膜。磨幾下,沒耐性了,突然猛力一擊。如果在一樓專心做事,那突發性的打擊彷彿直達心臟,好比安靜凝神的步行中,有人從背後猛力拍肩,簡直精神大地震,魂都拍散了。在灰敗的冬天裡,樹枝跟風的合奏樂高一聲低一聲,磨礪我的神經。
即使在蕭瑟的冬天,構樹的生命力也很旺盛。有一陣子它確實禿了也黃了好些葉子,當我把目光聚焦吉野櫻時,在料峭春寒中,它悄悄長出茂密的新綠。除了賤生,別無他辭。也正因為賤生,陽臺那棵小構樹才會留下。
沒養過那麼強悍的植物。花盆的表土全被長春藤悉數覆蓋,根本沒有樹苗的生存空間。這傢伙從花盆底下的出水孔掙扎著探出頭來,長出細瘦的主幹,幾莖綠葉。長春藤肯定不是對手,早晚營養會被這傢伙吃光。我使盡蠻力拔除它,沒想到小不點的根鬚堅韌無比。拔不掉,剪。剪沒多久,它悄悄抽芽。我剪。它長。它長我剪。如此這般三四回,絲毫不肯妥協,頑抗到底。樹很小,可是很倔強。
我投降。好吧,留你。
沒有土地的滋養,它長不成大樹,變成奇特的盆栽。兩三年了,也只尺餘高,主幹粗獷,幾枝搖曳的莖,四五片缺裂形的葉,剛好讓來陽臺洗澡喝水的綠繡眼暫時棲息。秀氣的綠繡眼配上迎風款擺的小樹,另有一番閒散風情。不過,構樹頑抗的個性,算是給我長見識了。
比起來,野桑椹身姿柔軟多了。算一算,野桑椹比構樹大上四五年,可是身形沒那麼張揚,是守候好幾代貓族的聖樹。十點二和十點半最愛這棵樹。牠們身形輕盈,表演特技似的走到樹枝末梢叫我,幾乎可以一躍而下進入我家。十點二的幼貓出生時夏正盛,等到牠可以爬樹,乾脆伏在樹枝午睡。風吹樹擺貓搖曳,這隻貓的絕世武功真是了得。牠垂下四肢,半歪著頭,蓋著樹葉編織的涼被,隨著風隨著樹枝的款擺安然入夢。這是貓界的小龍女,多麼不食人間煙火。樹影閃呀閃,陽光在牠的白毛上跳舞,這世界看來多麼安穩,多麼傳奇。看得我忘了熱,忘了人間危機四伏。
這隻貓雖然身手不凡,卻沒機會長大成貓,向世界展示牠的與眾不同。不到兩個月,小龍女突然失蹤,十點二懨懨寡歡。雖然我很清楚那意味著什麼,仍然每天望著空空的樹枝等待奇蹟,甚至夢見某個午後牠回來了,掛在樹上搖呀搖,像個轉瞬即逝的夢。奇蹟當然沒出現,只一張照片留下牠的絕世身影。傳奇不屬於人間,野桑椹默默的見證了這一切。
春天,野桑椹跟我家陽臺的桑椹一樣,同時由綠轉紅紫,白頭翁每天來啄果子,在枝頭高歌,母鳥帶著幼鳥練習飛翔。白頭翁、麻雀或綠繡眼的幼鳥都圓頭圓身,嬰兒肥的樣子,看起來非常稚氣。牠們在樹枝棲息時,老在理毛,翅膀末梢收不全攏,一副我還沒長大的樣子。等我長大,可就一體成型啦。
幼雀接受成雀餵食翅膀總是抖個不停。在我這個人類看來,牠們吃東西時,可是亢奮得很啊,好像身上裝了老在震動的小馬達。因此,麻雀小時候一律叫小抖。小抖抖翅膀。小抖吃東西。小抖追著成雀要吃的,邊追邊叫還邊抖,就是不喙。食物在腳下啊。我不免懷疑,牠們是真的不會啄,還是在撒嬌?成雀大概從沒吃飽過,身型永遠比小抖瘦,總是在啄和餵,食物一到嘴,立刻被小抖急急要去。每天清晨,我在八重櫻樹底撒下有機糙米和混合穀類,彈舌喊開飯,守候已久的成雀和小抖急急待落下,如秋風吹下枯葉片片。
新生的抖們跟著爸媽來覓食,從叫聲便可以判斷是成鳥或小抖。小抖的發聲聽起來是啜起嘴形吸入式的,很稚拙當然有時也挺煩的。牠們跟成鳥一樣話多,一樣中氣十足,急切的單音要命的清晰。只要一隻,一隻就夠了。如果牠透早練嗓,靠落地窗睡覺的人若非睡得熟爛,肯定會醒。白頭翁是起床號,叫起來一連串五六個抑揚頓挫的高音。牠們不吃穀類,可是鍾愛我家吉野櫻,也很喜歡野桑椹和構樹,每天來玩耍。從早到晚,耳朵都是白頭翁此起彼落的應和,牠們是真正的歌唱家,比聒噪的喜鵲悅耳太多了。後來,樹雀拖著長尾巴來逛了幾回,麒麟斑鳩也高貴現身。
因為樹,我家快成飛禽公園了。
我養成隨時倚窗,且倚窗成痴的習慣。從一樓二樓到三樓,從屋前到屋後,看樹看鳥看天,更遠處的茂密竹林,小規模的野樹叢。睛天看,雨天看,甚至晚上。夜裡的樹影顯得特別寧靜。經過鳥類一整天的疲勞轟炸,樹也終於準備歇息了。
這種放空最容易廢時曠日,該做的事沒做,做到一半的事,也沒興致再做了。杯子、書和手機出現在不該出現的位置,大概是東西拿著,走到窗邊出神,隨手一擱,便把它們遺忘了。
入夏時,竟然來了一隻松鼠。簡直發現新物種似的歡騰,喔,松鼠,哪來的松鼠。牠攀在野桑椹的主幹上,專注觀察四週的環境。大概是初來。我屏息凝神,直到牠轉身躍上構樹,迅速消失在視線之外。
那幾天,松鼠一直在我腦海忽隱忽現。
從前我確實很愛看樹。與其說看樹,不如說對著樹發呆。紅毛丹、紅毛榴槤、芒果、土番石榴,連綿的望不盡的油棕。認識與不認識的,軌道與公路旁,無論坐火車、巴士或汽車,或者在家裡,那些風姿迷人的赤道之樹,被雨水驕陽滋養得多麼出色。看樹時,其實內心充滿對現實的迷惑,對未來茫然,一點也不詩意,只想籍著外物移轉情緒,讓跑不停的腦袋喘一喘息。
有樹,便有鳥;有果樹呢,肯定少不了松鼠。松鼠在客家話裡叫「大尾鼠」,非常形象化,母親喊「大尾鼠」時很開心很有喜感,好像松鼠拎了一條大尾巴來娛樂她似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油棕園塵土滿布的候車亭旁,攀附著錢榆和野蕨的老樹。上學的日子,我從斜坡沿著一排扁柏走下來,遠遠望見老樹佇立在尚未破曉的天色中。樹形跟天色之間仍然是界線清楚的,它的粗壯枝椏集中在高處,落落幾筆,線條遒勁有力。樹葉在枝幹中間或末梢成團蓬開,像朵朵暗綠色的雲錯落有致的掛著,很適合入畫。
因為松鼠,突然電光火石,那麼久遠的畫面清晰的穿越時空而來。突然明白,旅行時,為何樹常常是眼睛和鏡頭下讓我著迷的風景。溫帶的樹。赤道的樹。冷與熱的強烈對照,內斂與外放,兩者都讓我凝神。
幾年前,深冬在亞維儂。染坊街清澈的溪水旁,有一株傲岸的樹,不高,樹型是個傾斜的「乙」字,凌空掠過溪水,往天空斜斜飛上去。溪水裡長著它的倒影,一樹生二相。跟張揚茂盛的赤道之樹比起來,松針科植物的葉片和枝椏相對稀疏,有種極簡的俐落風格。不過,它吸引我的不只是外形,而是一種乾淨純粹的氣質,像個真正的修行者。這樹好像連皮相都不要了,部份樹皮跟樹幹分離,呈半附著狀,樹身因此顯得特別斑剝。用手指輕撫樹皮,感受到它的剛毅。稍用力一板,乾硬的樹皮立刻成塊剝落,我吃了一驚,那麼容易就掉了啊?
無所謂,你要,拿走吧。彷彿它的回應是這樣。分明是它身上的東西,卻有身外之物的瀟灑。堤邊翠綠的青苔上,撒落幾顆暗褐色果實。我很好奇這樣一棵樹究竟結出什麼果?於是撿了一顆,使盡力氣想掰開它。沒辦法,太硬太堅固了。
這「做壞事」的畫面,被兩張照片留了下來。人與樹,人與樹子。照片最大的意義不是好奇可以留痕,而是揭露了連我自己都沒發現的,我跟樹的微妙關係。
最奇特的是黑森林。從上山纜車俯瞰,墨綠的松林那麼高聳,那麼清冷。人只能低頭向歲月向古老的樹林致敬。春天已到,松葉頂端猶盛著未溶的殘雪,柏樹卻迫不及待長出稚嫩的黃綠,然而那小小的點綴,畢竟化不開黑森林的墨色。
下了纜車入山,山中已起霧。微雨的山上寒氣透骨,隨處可見苔蘚,滿山遍野遊走的霧,幾乎是沿著上山的路流下來的,一波一波,濕了的頭髮冷冷的貼到臉頰。行走在霧氣縹緲的山林中,整個人變得跟苔蘚一樣低跟枯葉一樣沉默。那些深濃厚實的綠沉沉的彷彿有重量,走著走著,巨大的壓迫感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
何況空無一人的山,沒有鳥鳴沒有風動,除了霧,一切都是靜止的。龐大的寂靜有種懾人的氣勢。從前我常在熱帶的樹林裡行走,熱林子蒸騰鼓噪,野草野蕨在生長,蟲在土地裡孵化,從不停歇的蟲聲鳥鳴,偶有溪水歡快的流,水牛在洗澡。溫帶的樹林卻嚴肅深沉。冷的地方總是適合省視內心,思考形而上存在的吧?長長的冬天,德國哲學史上長長一串擲地有聲的哲學家。那懾人的哲學厚度和深度,也跟黑森林一樣讓人沉默。
樹沉默的看我。我也沉默的回看自己。一個離家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家,卻又老是渴望離家的人類,像長了根還想四處行走的樹一樣令人難以理解。我也以難想像,如果一輩子杵在同一個地方⋯⋯
如果不是離家,我是指中壢的家,黑森林給我的提問,全都將埋沒在日常生活的瑣碎裡,隨著如水的時間流走。如今這些問號像那棵倔強的小構樹,怎麼砍怎麼剪都處理不掉,我只好帶著問號,每天看樹。
樹什麼都沒說。
然而我很確定,有樹就有鳥,還有松鼠,以及蟬。雖然我從沒喜歡過蟬。新村時期在柴房裡捉過,用線繫在人參果樹上,聽牠們絕望的怒號。油棕園裡沒有蟬,我對蟬聲沒有免疫力特別沒轍,樹又那麼近。太吵了,我常對牠們說,饒了我吧。
蟬跟鳥們一樣喜歡構樹和野桑椹,夏天從清晨五點吵到入夜,七點多天都黑了還不肯放過我。有時快十點社區都睡了,竟然還有稀落的蟬聲,一度我還以為是幻覺。盛夏倚窗看樹時,蟬東一隻西一隻黏在樹枝上,不必多,只要三四隻,巨大的聲浪便足以將我吞沒。
這是油棕園記憶沒有行旅沒有屬於我家的夏之聲。
油棕園太遠,行旅中的相遇是偶然,我終究要回家。每天看樹讓我安穩,彷彿腳下生根,有了重生的力量。或許,當一株移植的樹,帶著原生土地的記憶和祝福,接受新土地的滋養。如果,蟬可以不那麼吵,就更好了。
看樹
入夏之後,構樹成了我的生活重心,也成為鳥類的另一個活動中心。自從跟它比鄰的野桑椹被砍去大半,構樹在多雨的春天,一下長成令人側目的大樹。
這要從野桑椹說起。有一晚發現側窗亮得刺眼,湊近一看,啊,又砍樹?野桑椹從大傘變成斜傾的半邊小傘。沒有樹蔭,燈光直接穿透米色窗簾,在地板打出耀眼光影。砍成這樣未免砍得太過頭了。鄰居解釋,火蟻沿著野桑椹的樹枝爬到他家草地上,靠他家的那半邊不得不清除。
火蟻從野桑椹生長的土地,攀上兩層樓高的樹幹,沿著鐵皮屋,越過圍牆,再爬下草地?這些火蟻是變種特工隊嗎?
不是故...
目錄
【自序】
輯一 看樹
看樹
麻雀樹,與夢
晚安,我的家
夏的序幕
從榴槤到臭豆
時光的縫隙
近黃昏
我要為你歌唱
昨夜你進入我的夢境
儀式,就是儀式
當秋光越過邊境
輯二 塵埃
破夢而入
夜色漸涼
跟過敏一樣麻煩
地鐵與黑麵包
伊斯坦堡的呼愁
紗麗上的塵埃
單純紀事
【自序】
輯一 看樹
看樹
麻雀樹,與夢
晚安,我的家
夏的序幕
從榴槤到臭豆
時光的縫隙
近黃昏
我要為你歌唱
昨夜你進入我的夢境
儀式,就是儀式
當秋光越過邊境
輯二 塵埃
破夢而入
夜色漸涼
跟過敏一樣麻煩
地鐵與黑麵包
伊斯坦堡的呼愁
紗麗上的塵埃
單純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