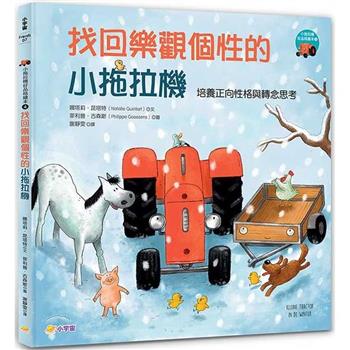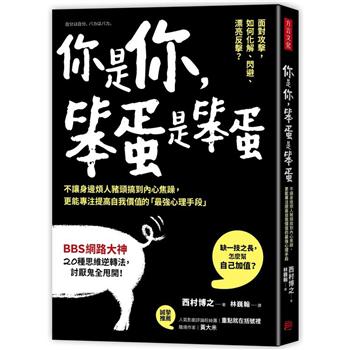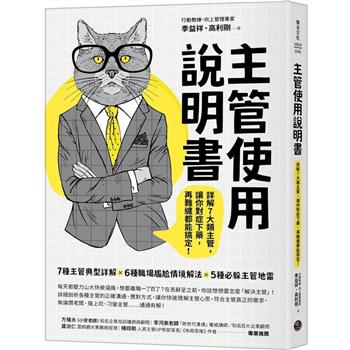是命運的狎弄,或是誰刻意揀選了他,他不過是個窩居繁華城市在高級餐廳工讀的打工仔,渴望單一的愛情,這些身體泌出甜漿果酒味的女人,卻把愛情與男人當成餐桌上的豪華全餐,每道都想嚐一口,他一次次成為愛情的第三者,被豢養在用金錢與溫情包裹的金屋裡。
他用自由換取金錢與紅酒知識,曾有人對他說,紅酒有自己迷人的故事也會替人帶來故事,在特殊時刻喝過的紅酒,這輩子忘不了;紅酒成為他另類的愛情占卜師,選酒品酒過程揭示了他的現狀與未來。不甘成為遊戲裡的棋子,他算計,他離開,他回到自己充滿廉價超商贈品的簡陋小窩,迎接他的會是桑椹莓果酒香的單純新戀情,還是淪為另一個豢養者的賭注與獎勵?
徐嘉澤以全新觀點顛覆傳統愛情關係,造起物慾、金錢橫流的索多瑪城,大量的紅酒美食在故事裡展示玄妙的真身幻影,嗅覺、味覺的衝擊刺激,風味獨具,魅惑人心。
本書特色
★ 書中植入大量名酒:如八二年木桐、Vougeot 1er Cru、nuits-saint-georges……,以及選酒、品酒情節,極具風味。
★ 第三者除為感情的闖入者,也是三人行式的愛情,並以女性為中心,讓女人成為愛情的主宰者。
★ 都市邊陲租賃公寓小隔間的單身生活十分傳神,超商集點換來的贈品堆滿房間,側耳傾聽隔房不相識、不往來的房客,表現出在都會生存的寂寞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