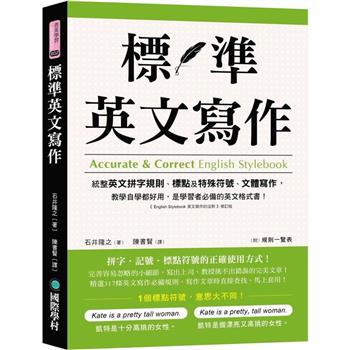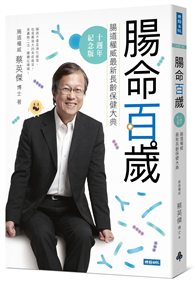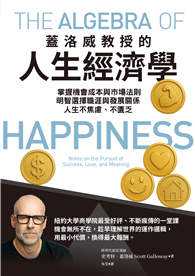可以是21世紀的藝術福音:
薪傳葛羅托斯基的藝乘
1967年,美國藝評家蘇珊.桑塔(Susan Sontag)劈頭寫道:
每個世代都必須為它自己重新建構「精神性」的計畫。(精神性=立身處世的某些規劃、術語、觀念,目的在解決人生際遇中固有的、痛苦的結構性矛盾,冀望達到意識完滿,超凡入化。)在現代,藝術成了精神性計畫最活潑有力的隱喻之一。
桑塔的這種「精神性計畫」很謹慎地避開了任何宗教色彩或超自然的泛音,卻很清楚地指出個人解脫的「精神性需要」:這是每個世代的人的生命之需,就像空氣和水一般。她在「沉默的美學」中以杜象(Marcel Duchamp)、凱基(John Cage)、貝克特(Sanuel Beckett)和葛羅托斯基等人的「沈默(貧窮)藝術」為例,說明了現代藝術如何可能指向當代人走出自我、解脫煩惱的「精神性計畫」。
在知識成為經濟,創作成為工業的e時代,把藝術跟「精神」、「圓滿」、「超凡」、「入化」聯結在一起必須非常小心,因此,我選擇讓一個美國知名美學家來做這篇「再版序」的開場白。美國傳統通常被認為是比較務實或「物質」的。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我們的美國藝評家、美學家似乎只想關心美學反思的問題:「藝術」只是當代迫切需要的精神性計畫之最活潑有力的「隱喻之一」而已。至於「藝術」如何可以直接契入當代人的生命、提昇現代的社會生活,她只聰明地再三述說沉默的「美學」,沒有沉默的「行動」。
這不是一種究竟之道,雖然我們無法苛責或強求她。我們的問題是:直接做為每個世代──包括e世代──的精神性計畫的「藝術」是什麼呢?
波蘭藝術大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1999)在他「活潑」的創作生命中,幾近於「沉默(貧窮)」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藝術是種乘具(Art as vehicle),可以讓你自「人生際遇中固有的、痛苦的結構性矛盾」中解脫,把自己傳送到那個「意識圓滿、超凡入化」的境界。他說:
你所過的生活,你滿足嗎?你幸福麼?你對周遭的生活滿意?藝術或文化或宗教(指活生生的泉源而非教堂或教會)——所有這一切都是不滿意的表達之道。不,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不足夠的……。
我們為何關心藝術?為了跨過我們的邊界,超越我們的限制,填滿我們的空虛──實現自己。這不是種狀態,而是種過程:在﹝創作或欣賞藝術﹞這個過程中,我們裡面晦暗的部份會緩緩地變成光明剔透。在這種與自己的真實(truth)的奮鬥中,在這種剝除生命的面具的努力中,劇場由於其運用到全身的覺感,對我而言,一直似乎是個充滿挑釁的場域。藉由觸犯各種理念、感情和判斷方面的陳腔濫調,劇場可以挑戰自己和觀眾──這種冒犯由於乃形之於人的呼吸、身體和內在的脈動,結果更形尖銳。這種對禁忌的挑釁和逾越會產生震撼,叫面具剝落,使我們能夠赤裸裸地獻身於某種不可說而卻隱含著情欲與慈悲(Eros and Caritas)的東西。
1965年前後,葛羅托斯基才三十出頭,卻已經以「貧窮劇場」的幾個作品,動搖了歐美前衛藝術界,開啟了未來更「圓滿」(total)或「神聖」(holy)的藝術創作。之後,從1970年代開始,這麼一個不世出的藝術創作天才,傾全力用了整整一生的身體行動,終於結晶出「藝乘」這個身心工作方法,具體回答了「藝術做為一個精神性的計畫」這個急迫的世紀末問題。
我必須向讀者坦誠:我自己是葛氏的最大受益人之一,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循著「從貧窮劇場到藝乘」這條葛氏之道(Groto’s Way)偊偊前行以至於今,雖然沒有成就「武功蓋世、名被環宇」,但是卻清楚地品嘗著「息業養神、隨份度日」的歡喜自在,對葛氏和所有先聖先賢因此朝夕充滿了感恩之心,也因此我在世紀之交發願寫了一本書,要讓葛氏的道理行誼用中文散佈出去。《神聖的藝術:葛羅托斯基的創作方法研究》在2001年3月由揚智出版社印行,反應相當不錯,但是賣了一兩年就絕版了。我因為想力行葛氏門徒「沉默守獨」的家風,面對著不少年輕朋友的問訊,總以請向中央圖書館或北藝大總圖調借影印委婉答覆。
時光荏苒,葛氏辭世轉眼已經要十年了。去年年底欣聞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已經頒訂2009年為「葛羅托斯基年」(the Year of Grotowski 2009),以茲紀念葛氏逝世十週年,葛氏接掌「十三排劇坊」50週年,以及「波蘭劇場實驗」解散25週年──藉著這個機會,讓《神聖的藝術:葛羅托斯基的創作方法研究》再版好麼?沉吟之間,書林出版社的蘇經理?隆大力贊成,勘誤之外,也建議將書名改為《從貧窮劇到藝乘:薪傳葛羅托斯基》,原因之一是原先的書名《神聖的藝術》常常叫現在的書店人員把書擺錯地方,對愛書人不夠友善。我從善如流,只希望葛氏的先知卓見可以更清楚方便地普及於一切。
是為幸!
2007年6月30日前往靈泉禪寺前
於北藝大戲劇學院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