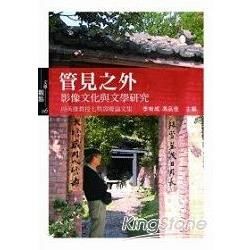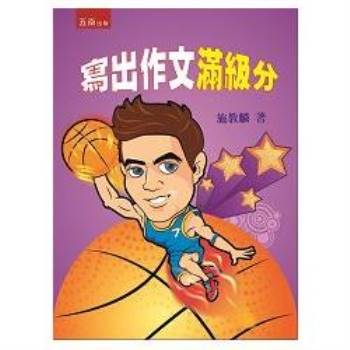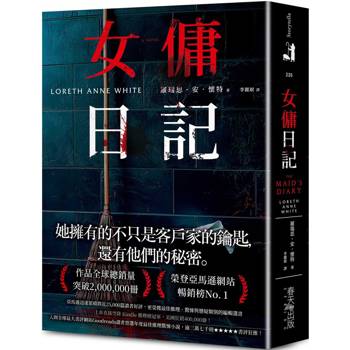周英雄教授為臺、港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界備受尊崇的資深學者,先後任教於臺、港著名大學,主持學術行政,並膺選為香港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及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執行委員。周教授學養豐厚,勤於研究,著作等身,誠懇謙和,煦煦紳士,數十年來作育英才無數,兼之古道熱腸,服務學界不遺餘力,其為人、治學、處事,堪為後進之楷模。為祝賀周教授七十壽辰,臺、港若干重要學者特撰論文,輯為文集,以為賀禮。本文集主要分為二輯,分別論述影像文化與文學,所論類型包括電影、攝影、小說、戲劇、詩及理論等,多元豐富,兼具廣度與深度。文集另輯有訪談錄一篇,周教授首次暢談其學思歷程與其對臺、港學術教育界之觀察與思考,實屬難得。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李有成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曾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等職,現任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主要著作有詩集《鳥及其他》、《時間》,散文集《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文學評論與學術專書《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複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與王安琪合編)、《離散與家園想像》(與張錦忠合編)。
馮品佳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中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及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外文系系主任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等職。主要研究興趣為英美小說,女性書寫,離散文學,少數族裔論述以及電影研究。著有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En-Gendering Chinese Americas: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ers;編有《重劃疆界:外國文學研究在台灣》,《通識人文十一講》,《影像下的現代性:影像與視覺文化》(與周英雄教授合編);譯有Love。
作者序
序
李有成
一
四十年前一個春日的早上。周英雄老師走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的A1教室,隨即要我到教室前面報告閱讀喬伊斯(James Joyce)短篇小說〈一抹微雲〉(“A Little Cloud”)的心得。那是大一英文課本的選文,我事先讀了,並寫了一篇分析習作請老師過目。周老師大概覺得還可以,要我上課時跟同學談談這篇小說。四十年前的一件小事,老師可能早已忘記,可是對我而言,那天早上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
周老師就站在A1教室的門口,專心聽我分析。當時的我可能比班上剛從大學聯考衝刺過來的同學早一些接觸西方文學,對喬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並不陌生,只是大一的學生,對這位愛爾蘭大作家能有多少了解?那個上午我怎麼談喬伊斯的小說,細節當然已不復記憶。只記得在談到小說中的角色時,我突然間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大概自己也不太了解的話:「現代主義的小說裏再也沒有英雄!」我猜想當時自己心中的對照或許是希臘羅馬的史詩與悲劇。
站在教室門邊的周老師緊接着我的話面露微笑地說:「那我大概是最後的英雄了!」話才說完,全班哄然大笑,課堂上的氣氛頓時輕鬆了不少,我有些緊張的心情也放鬆了下來。我更因此發現,眼前這位年輕的老師其實是一位和藹而易於親近的師長。周老師大概不知道,我事後為了弄清楚自己那句話的意思,還囫圇吞棗看了不少現代主義的理論。年少懵懂,信口開河,奇怪的是,四十年前春日上午周老師的那一堂課卻是我大學時期最難忘的記憶之一。
那一年夏天周老師就出國去了,到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念博士學位。記得老師出國前,暑假剛開始,我還特地跑到建國北路老師的寓所去看他──那時候建國南北路尚未拓寬,還不是現在的高架快速道路。
往後有好幾年沒見到周老師。後來聽說他完成了博士學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再見到他時我已經進入博士班就讀。印象中每四年一次於淡江舉辦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他都會回來參加。我有時候在會場看到他,就跟他坐在會議室的後頭聆聽台上的學者發表論文。周老師在香港十七年,在文學教育、學術行政及專業服務等方面有很多貢獻,同時也出版了不少著作。他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系主任、文學院的署理院長,並膺選為香港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和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執行委員。一九八○年代初我和單德興在臺大念書,那個時候文學理論正熱衷於所謂語言的轉向,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等是必讀的書,雅克慎(Roman Jacobson)的若干重要論文我們也不只讀過一遍。我們從俄國形式主義,經布拉格語言學派,一路讀到巴黎的結構主義。當時鄭樹森教授和張漢良教授都有長文論述結構主義,周老師也發表了好幾篇結構主義的論文,特別是以結構主義析論樂府古辭和賦比興等那幾篇,思路綿密,論證嚴謹,在方法上更是步步為營,環環相扣,引人入勝,不僅引領我們深入了解結構主義,並且為我們示範演練如何將結構主義部署為文學批評的利器。周老師的論文沒有神秘費解的術語,字裏行間總是清楚交代術語背後的諸多觀念,無疑是經過消化反芻之後的結果。我自己細讀周老師的論文,印證幾位結構主義理論家的說法,彷彿又回到當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的情形。跟一般「拿來主義」的做法不同,周老師花了不少功夫在協商調和結構主義與傳統中國文學研究之間的扞格;他不認同若干學者視結構主義為機械與形式主義的說法,反而從結構主義的細部文本分析中,見證文學與人生和社會文化緊密複雜的關係。周老師在〈結構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文學研究?〉一文的結論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除了堅守各學科的專業學養之外,同時也要放棄『閉關自守』的觀念,找求各個不同學科之間如何互通有無,如何交換資料的方法。」這是約三十年前所說的話,這種跨領域研究的信念貫穿了周老師大半生的學術產業。
我最早讀到的周老師的著作是他的碩士論文《小說中的還魂母題研究》(A Study of the Return Motif in Fiction),出版時被納為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二四六種。發現這本論文其實相當偶然。我寫碩士論文時對神話或原型批評甚為著迷,對傅萊(Northrop Frye)的著作──尤其他那部體大思精的《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非常欽佩,以為要建立文學研究的科學,這是最好的借鏡。當時我已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經常跑到民族學研究所的圖書館看書,特別是有關神話與民俗學方面的著作。那時候當然還沒有電腦可以檢閱資料,不過民族所圖書館的圖書編目在相互參照(cross reference)方面做得非常詳細,查詢資料相當方便,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現周老師這本英文專著的。這本論著處理的文本主要包括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和《霍華斯莊》(Howards End)、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七角屋》(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華頓(Edith Wharton)的《伊丹.芙洛姆》(Ethan Frome),以及詹姆斯(Henry James)的〈歡樂角〉(“The Jolly Corner”),可以看出周老師對小說與民俗敘事的濃厚興趣。他後來的學術研究一直延續這樣的興趣。
周老師在一九八○年代末和九○年代初出版了《小說.歷史.心理.人物》與《文學與閱讀之間》二書,其中大部分的章節都是在處理小說的問題。關於這個時期的學術興趣與著述,他在接受單德興的訪談時這樣說明:「我自己的論著大致上探索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的體用問題,之後我有機會接觸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同時配合中西比較小說的理論,撰寫了一些小說與心理的論文,並著眼於閱讀,寫了若干書評,算是個人比較熱中的副產品。」這個時期周老師也數度為文暢談文學理論與文學教育,特別是他所熟悉的外國文學教育。在〈文學挑戰的正反面〉一文臨結束時,他說:「外國語文的掌握固然不可或缺(外文教學勢非重視語文能力不可);可是語文之外,我們期待自己能對外文背後的文化有所挑戰。也正因如此,外文教學除了語文訓練之外,另需借重外文經典之掌握,做到耳濡目染於異國文化之境界,以便以他山之石攻錯。而在此過程中,語言學專業訓練,以及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無疑有助於我們對第二語文、文學,甚至文化,有一項自覺性、分析性與批判性的專業知識。」這些話猶如暮鼓晨鐘。在今天這麼一個日漸將外國語文窄化為職場語文的教學環境裏,周老師這一席話顯得語重心長,擲地有聲。
在同一個時期裏,周老師還以一篇篇論文反覆論證小說(文學)與現世──包括歷史、政治、文化、社會、人物心理──之間的關係,他的論證有敘有議,往往落實在文本的閱讀經驗上,如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所發表的幾篇力作論西西、張賢亮、韓少功、王安憶、莫言、張大春、黃凡等人小說,其析論過程也透露了周老師的基本文學關懷與批評信念。
序
李有成
一
四十年前一個春日的早上。周英雄老師走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的A1教室,隨即要我到教室前面報告閱讀喬伊斯(James Joyce)短篇小說〈一抹微雲〉(“A Little Cloud”)的心得。那是大一英文課本的選文,我事先讀了,並寫了一篇分析習作請老師過目。周老師大概覺得還可以,要我上課時跟同學談談這篇小說。四十年前的一件小事,老師可能早已忘記,可是對我而言,那天早上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
周老師就站在A1教室的門口,專心聽我分析。當時的我可能比班上剛從大學聯考衝刺過來的同學早一些接觸西方文學,對喬伊斯的《都...
目錄
目錄
李有成 序 i
■ 訪談 ■
單德興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教授訪談錄 1
■ 影像 ■
鄭樹森 映象風格與建築特色――溝口健二的《元祿忠臣藏》 25
單德興 攝影.敘事.介入――析論薩依德的《最後的天空之後》 31
張小虹 愛的不可能任務:《色∣戒》中的性-政治-歷史 69
馮品佳 溫哥華女兒:沈小艾的華裔加拿大女性電影 105
余君偉 冷面、黑色況味、觀賞樂趣:獨行男殺手電影初探 123
■ 文學 ■
李有成 離散與家國 149
譚國根 中國話劇的三種話語與戲劇形式的實驗 183
廖咸浩 異夢為何同床?中文現代詩中現代主義詩學與國族再造的糾結 205
葉少嫻 個人與地方的互動關係︰三篇中港台小說中的身份問題 231
廖朝陽 戰爭機器的普設性:談川端康成的《名人》 255
何文敬 跨種族的兩性關係與兩代衝突――雷祖威的《愛之慟》 268
蔡振興 破與立:論史耐德《山水無盡》跨越疆域的想像 301
李家沂 待與客 325
廖炳惠 創傷、記憶的內爆:電影與文學中的台北 345
周英雄教授主要著作書目 363
作者簡介 365
索引 371
目錄
李有成 序 i
■ 訪談 ■
單德興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教授訪談錄 1
■ 影像 ■
鄭樹森 映象風格與建築特色――溝口健二的《元祿忠臣藏》 25
單德興 攝影.敘事.介入――析論薩依德的《最後的天空之後》 31
張小虹 愛的不可能任務:《色∣戒》中的性-政治-歷史 69
馮品佳 溫哥華女兒:沈小艾的華裔加拿大女性電影 105
余君偉 冷面、黑色況味、觀賞樂趣:獨行男殺手電影初探 123
■ 文學 ■
李有成 離散與家國 149
譚國根 中國話劇的三種話語與戲劇形式的實驗 183
廖咸浩 異夢為何同床?中文現代詩中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