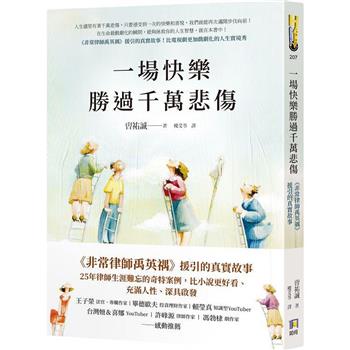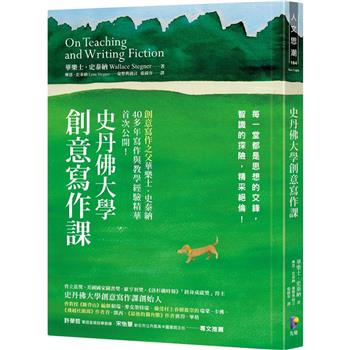世界上許多著名的英文文學作品均無法脫離與英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聯繫,而語言正是後殖民文學關注的重點之一。
塔力卜在《後殖民文學的語言》書中列舉許多作家,如珍‧瑞絲(Jean Rhys)、奇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及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指出英語/文的形成不僅受到英國前殖民地的影響,同時也必須與殖民地原有的語言競爭。藉由探究印度、奈及利亞、加拿大、澳洲、加勒比海及愛爾蘭等前殖民地的文學,讀者將能了解到,被殖民的人們在面對殖民者帶來的巨大改變時,如何保有他/她們的文化及國族認同。
本書特色
1. 列舉許多知名英文文學作家,如珍‧瑞絲、薩爾曼‧魯西迪、馬克‧吐溫、奈波爾等。
2. 詳盡介紹各種後殖民文本中的語言特色。
3. 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之外,在英語/文的演進和發展(語言學)方面也極具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伊斯梅爾‧塔力卜(Ismail S. Talib)
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英文系。主要研究領域為敘事學、文體學、後殖民理論、後殖民文學以及新加坡英文文學。教授課程包括:「電影論述和語言」、「敘事結構」、「敘事學導論」、「文學中的語言分析」以及「後殖民理論」。與Lionel Wee 合著有《英語結構與意義》(English Structure & Meaning,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8)。
譯者簡介:
李勤岸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所長。著有《李勤岸詩選》(Selected Poems of Khin-huann Li)、《哈佛台語筆記》、《大人囝仔詩》、《母語教育:政策及拼音規畫》等。
章節試閱
第四章 口語、書寫及英語所帶來的物事
從白人殖民地把眼光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景象。第三世界國家在情感和文化上並未與英格蘭緊密相繫,而英語也不是這些區域多數人口的母語,或許只有加勒比海的一些國家例外,這些國家使用英語或一些英語的變體做為第一語言。當我們談到許多非加勒比海國家以英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比較恰當的說法是稱之為「使用借入的語言所書寫的文學』(literatures in a borrowed tongue),這類文學也因此可說是非在地文學(non-native literatures)。本章將探討分析這些文學作品所需的背景脈絡知識,以及口語、書寫與做為外來語言的英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文字書寫之引進
在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引進書寫和引進英語同等重要。的確,在某些社會脈絡,書寫的引進尤其重要。例如,阿須克爾夫特等人(Ashcroft et al. 1989: 82)就主張,「在許多後殖民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並非英語這種語言本身,而是書寫一事」。在這些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社會中,引進書寫和英語一樣,兩者都與殖民主義息息相關。對這些語言而言,經由英語所引介的羅馬字,是為了引介書寫而來的。當然,在那些被其他使用羅馬字的歐洲強權(例如西班牙和法國)佔領控制的地區,情況也類似。
然而,書寫的引進並不單純只是為沒有文字的語言引進文字,讓人們有了閱讀與書寫的初次體驗。某些語言在歐洲殖民主義者到來前,已經有了文字,例如西非的古阿坎語(ancient Akan)就有自己的文字,而馬來語(Malay)和斯瓦希里語(Kiswahili)則是使用阿拉伯字母。古阿坎文字隨著時光的流逝已不復存在,馬來語和基斯瓦西里語則是因為語言學上的緣故,引進比阿拉伯文字更為合適的羅馬字母作為書寫系統。在馬來語和斯瓦希里語的例子中,書寫的引進和殖民強權未必有很強的關連性,土耳其的情況也類似。這個國家並未受到西歐強權殖民,但土耳其人卻因為認為羅馬字在書寫上較有效率而予以採用。以羅馬字取代阿拉伯字母的做法,受到部份馬來語、土耳其語使用者的反對,甚至一如馬茲律和馬茲律兩人(Mazrui and Mazrui 1998b: 72-3)所提及,斯瓦希里語的使用者也因為阿拉伯字和伊斯蘭傳統的某些部份有關而不贊同這個做法。反對的聲浪之所以高漲,不僅僅是源於文化的基礎,以斯瓦希里語為例,甚至還涉及語言學上的理由(Mazrui 1998: 45-6)。
然而,就大多數其他的語言為例,羅馬字都是經由殖民帝國或其他和殖民帝國有關的機構,引介到自身語言沒有書寫系統的社群。這些相關團體有的是行政或教育機構,有些則藉助政府對其他領土的殖民控制散播羅馬字母系統,例如傳教士。
書寫引進後隨即取得優勢,代價卻是犧牲口語,使得有些人憂心忡忡。例如,布奇‧愛梅切塔(Buchi Emecheta)所著的小說《為母之樂》(The Joys of Motherhood)裡,文中的敘述者觀察到小說中Nnu Ego和Nnaife這兩個重要的角色,「對於只能透過文字,卻不能用言語表達的生活感到措手不及」(1979: 179)。除了擔心無法應付書寫媒介,也會恐懼一般口語傳統的某些面向(尤其是口述文學)將會消失,有時候這樣的恐懼是合情合理的。舉例來說,辛巴威作家吉吉‧丹格倫博嘉(Tsitsi Dangarembga)回憶起1980年,辛巴威人慶祝建國獨立。當時,她聽見「人們朗誦著那首她所聽過最優美的詩」,那首詩是用她的母語紹納語(Shona)所寫的,更「讓我想起,我們在這片土地上還有自己的口語」(Wilkinson 1992: 195)。但她也說道:
……但這對我來說,卻也是痛苦的經歷,只要想到關於這語言我們已經失去太多太多。有時我覺得我們需要一項計畫,可以說是迫切需要,來儘可能寄發錄音機和錄音帶到各個角落,請大家坐下來講講話,尤其是耆老。一切都在流逝……這真是太悲哀了。我感到痛苦萬分,這麼豐富的文學資產存在著,卻沒有書寫記錄下來,以致於沒有途徑可以接觸這些文學資產,就讓它這樣白白流失。
(Wilkinson 1992: 195)
書寫帶來了什麼
一般而言,在殖民者到來之前沒有文字的社會,都會有從口說文化到讀寫文化(literate culture)的過渡期。照理來說,隨著書寫的引進,人們或許可以把文學的起始本身視為是一種書寫的藝術形式。就這點來說,安東尼‧衛斯特(Anthony West)(1953: 22)曾宣稱,在閱讀阿摩斯‧圖圖歐拉(Amos Tutuola)的第一本小說《棕櫚酒鬼》(The Palm Wine Drinkard)的同時,「就得以窺見文學的起始,而那就是書寫終於得以捕捉並明確記錄無文字文化(analphabetic culture;即沒有文學的文化:「非使用字母的文化」)的神話與傳說之時」。這個觀點並不完全適用於奈及利亞的情況,因為早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奈及利亞的某些在地語言(例如豪撒語〔Huasa〕、艾菲克語〔Efik〕和圖圖歐拉的母語約魯巴語〔Yorùbá〕)就有自身的書寫文學傳統了。
無論衛斯特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否符合實際情形,引進書寫伴隨而來的是全新的文學體裁,而這是以口述傳統為基礎的文化所沒有的。長篇非詩體的敘事文學(non-poetic narratives)就是一例。在口說傳統中,長篇敘事通常是以詩歌的形式出現,因為韻腳、固定格律等修辭手法能幫助記憶。換言之,這些特色有助於我們記住敘事的詩行。通常這些長詩也用於唱頌。缺乏文本的輔助,敘事詩中屬詩體及音樂的某些顯著特性幫助人們記住故事的諸多細節。
雖然有些人認為書寫是語言的一大進展,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都一致這麼認為。例如,早期的南非黑人作家對書寫沒有太多的敬意,他們認為,「書寫文學將文學私有化,這違反了文學最重要的信念之一」(Kunene 1996: 16)。對他們來說,文學「之所以有價值是藉由在社群所組構的背景中進行散播」。為了獲得或重新獲得社群意識,「許多不擅書寫的長者,會要求能寫字的人讀故事給他們聽」(Kunene 1996: 16)。因此,在早期的南非黑人文學史,書寫文學(written literature)的傳播有部分是透過口述流傳。
第四章 口語、書寫及英語所帶來的物事
從白人殖民地把眼光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景象。第三世界國家在情感和文化上並未與英格蘭緊密相繫,而英語也不是這些區域多數人口的母語,或許只有加勒比海的一些國家例外,這些國家使用英語或一些英語的變體做為第一語言。當我們談到許多非加勒比海國家以英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比較恰當的說法是稱之為「使用借入的語言所書寫的文學』(literatures in a borrowed tongue),這類文學也因此可說是非在地文學(non-native literatures)。本章將探討分析這些文學作品所需的背景脈絡...
目錄
一、(後)殖民情境中的英語
二、蘇格蘭、威爾斯及愛爾蘭文學中的反殖民性
三、盎格魯-撒克遜的移植
四、口語、書寫及英語所帶來的物事
五、在後殖民文學中使用英語──評論回顧
六、去殖民和前殖民地獨立後英語的持續推行
七、風格、語言、政治和可接受度
八、混合語又如何呢?──英語、方言和其他語言
結語
參考書目
一、(後)殖民情境中的英語
二、蘇格蘭、威爾斯及愛爾蘭文學中的反殖民性
三、盎格魯-撒克遜的移植
四、口語、書寫及英語所帶來的物事
五、在後殖民文學中使用英語──評論回顧
六、去殖民和前殖民地獨立後英語的持續推行
七、風格、語言、政治和可接受度
八、混合語又如何呢?──英語、方言和其他語言
結語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