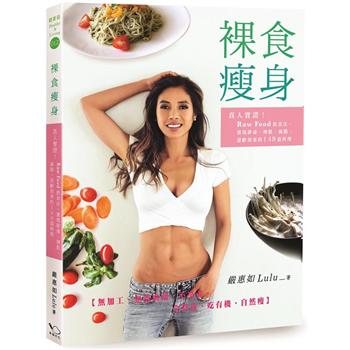2011卡夫卡獎、2005曼布克獎得主約翰.班維爾探求真實、虛構與人性本質之傑作。
席利安.墨菲(《冥王星早餐》、《吹動大麥的風》、《全面啟動》)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回憶如同幽靈一般,縈繞不去……
「強迫我們挖掘那些骯髒的細微末節,逃避自認為已忘卻的往事。」
「真實的生活已經離我遠去,現在的我只是一種死後的生存狀態。」
在愛爾蘭海中一座人跡罕至的小島上,住著謎一般的繪畫專家克羅伊茨內教授,與他的僕人李奇特。在《證詞》中因謀殺罪被關進大牢的弗雷迪.蒙哥馬利在出獄之後,來到了這個小島,尋求與克羅伊茨內教授共同研究一幅十八世紀荷蘭畫作,以及和教授一起寫書的機會。但是在小島上的寧靜生活卻無法讓弗雷迪的內心感到平靜;他仍常常想起被捕之前的生活,而他曾犯下的罪行及過往的虛無人生更經常出現在他的惡夢中,使他無法自幽魂一般纏繞著他的回憶中逃離。
在此同時,島上來了一群因船觸礁而漂流於海上的旅人。這些遭逢船難的外來客在等待船再次起航的期間,便寄居於教授的屋子中。外來客之一的費利克斯曾捲入某樁買賣贗品的案件中,而克羅伊茨內教授正是為這樁買賣進行藝術品鑑定的專家;教授是否就是策劃這場騙局的幕後黑手?
最終,克羅伊茨內教授與弗雷迪共同研究的這幅畫作被證明是贗品,甚至畫家本人也是虛構人物,但這幅畫仍透過他們二人投注的心力得到了它的價值,不再只是一幅複製品。而外來客們像是幽靈一般,突然來到,又突然離去,再度出航,離開小島,故事在此戛然而止,只留下曖昧不明的結局,讓讀者仔細思索什麼是真、什麼是假?誰是真人、誰又是幽靈?
作者簡介
約翰.班維爾 John Banville
1945年生於愛爾蘭衛克斯福德,畢業於聖彼得學院。他最初的志願是當畫家或建築師,卻並未就讀相關科系。1995年,班維爾到愛爾蘭時報工作;1998年起擔任文學主編。他也長期為紐約時報撰寫書評。除了擔任報紙編輯與寫作之外,班維爾也曾與愛爾蘭導演尼爾.喬丹合作過數部電影,如改編《愛情的盡頭》(The End of Affair)的劇本。他的作品包括《哥白尼博士》、《克卜勒》、《牛頓書信》及框架三部曲:《證詞》、《幽靈》和《雅典娜》,其中《證詞》入圍1989年曼布克獎決選名單。他在2005年再次以《大海》入圍,並擊敗石黑一雄與莎娣.史密斯獲獎。2011年,班維爾獲得有「諾貝爾風向球」之稱的卡夫卡獎。他同時以班傑明.布萊克的筆名創作「孤獨奎克」犯罪小說系列。
譯者簡介
陸劍
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英文系。譯有「框架三部曲」 (《證詞》、《幽靈》、《雅典娜》,2005年曼布克獎得主約翰.班維爾著);《墮落的信徒》(班傑明.布萊克著);《林奇的歡愉》(2007年曼布克獎得主安.恩萊特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