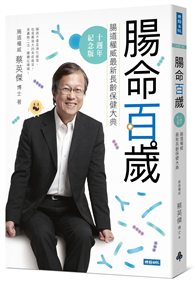導讀
荒原遍歷︰一場見證愛的《聚會》 高維泓 臺大外文系副教授
數年前的冬天在土耳其西部小城Manisa參加一個研討會,遇到一個來自伊朗的講者。也許因為各種莫名的因緣,總與這位伊朗學者同桌吃飯。在陌生的城市閒逛時,也數次在路上巧遇。見面的次數多了,吃飯喝茶外自然也聊起彼此的國「家」。
這位伊朗講者年約五十,有些嚴肅,卻沒有學究味,也不像同樣來自伊朗、伊拉克等地學者那麼拘謹(或許是因為一時無法調適同樣信奉回教,卻相對自由開放的土耳其)。他有著學術圈外人才有的自在,不怎麼修邊幅,說話也帶點草根味,但也不覺酸腐或偏激。
共桌吃飯所聊的細節已經有點模糊,但我記得他說十八歲時因為參加反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政權的運動被捕,蹲了好幾年黑牢。我注意到他走路有點小跛,以為他是旅途中受了傷,但他說是因為有一次為了逃避追捕,攀牆時跌落摔傷,之後就一直無法復原,但也不怎麼影響日常行動。有一天傍晚,我和他散步到校外,沒想到天黑極快,一下子我們就迷了路。明明校園就在圍牆的另一邊,可怎麼樣就是找不到原來的出口。他提議不然我們就翻牆吧!下一分鐘他就已經身手矯健地翻過牆,一邊拍去身上的塵土,一邊說:「別忘了我以前是跑給政府追的。」
或許因為他曾經是個政治受難者,所以事隔多年,他在我心裡的形象還是很清晰。在獄中他為了接觸西方知識苦學英文,出獄後重拾課本一步步完成大學與碩士學業,結了婚也有了小孩。好不容易找到教職,卻因為被人發現政治犯的背景而遭解雇(他說一方面是同事鬥爭的結果,害他被掃到颱風尾)。之後輾轉找到了新的工作,幸虧有人幫他說話:「他都這個年紀了,還能有什麼破壞力呢?」才僥倖待了下來。他的這些經歷我並不格外驚訝,畢竟臺灣也曾走過白色恐怖的年代,我只是看到了一個活脫脫在極權統治下倖存的小人物,試著走回他應有的人生。
我從旁觀者的角度聽著這位過去的政治異議分子講述過往,腦海總不免浮現一些問句:「那他的家人呢?他的父母姐妹兄弟有因為他的政治傾向而受牽連嗎?」我不好意思問的太過唐突,只說:「你坐牢的那段期間,會想念你的家人嗎?」我原以為他會開始談談他的家人,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語氣決絕地說:「I don’t miss my family」,說早就不和他們聯絡了,他們在哪裡對他也不重要了。
我在讀安瑞特《聚會》的同時,不時想起這個已經不在乎原生家庭的伊朗講者。是什麼原因讓他不願意再和「那個家庭」產生關連?「那個家庭」是否曾經在他最需要的時候,關心他、理解他、幫助他?還是兄弟姊妹大難臨頭各自飛,和他劃清界限?他的父母親呢?強人政權如何撕裂了他的家庭?他童年快樂嗎?他怎麼走上反政府的崎嶇道路?他的家人怎麼看待他:是鬥士,還是家族之恥、麻煩製造者?坐牢有改變他的政治態度嗎?如果出獄後和家人保持連絡,他的人生會比較順利嗎?我更想問的是:五十歲的他,後悔嗎?
安瑞特的《聚會》是一本關於「家」的書。不同於一般人對「家」的美好想像和歌頌,三十九歲的主角薇羅妮卡因為哥哥黎安的死,終於勇敢面對她的家其實是個無法醒轉的夢靨,她所受到的心靈創傷遠多於美好回憶。為了療傷,薇羅妮卡試著追溯這些家族創傷的幽微根源,嘗試拼湊外婆艾達未婚前的種種,如何周旋在兩個追求者,而被鬥敗的一方像鬼魅般遙控著這三代家庭。薇羅妮卡不斷透過回憶要說出造成哥哥死亡的真相,但這真相又混雜著太多難堪。要追究黎安的死因,得被迫將自己瀕臨破碎的婚姻攤在陽光下,得將自己從性壓抑解放出來,得原諒忙著生育(懷了十二個孩子,流產七次)卻任憑孩子被欺負的母親,得原諒那個無法確認是否被猥褻的自己,得原諒有著血脈關係卻彼此敵對傷害的家人,得原諒你深愛卻自私遠走的另一半……
安瑞特的《聚會》也是一本關於「愛」的書。在薇羅妮卡的推斷裡,外婆艾達是個渴望被愛的孤兒,因為愛而從應召站被贖出來。薇羅妮卡和她的手足們,為了證明有被愛的價值,幾次在愛情裡迷失碰撞,或逃離這個以愛之名傷害彼此的家庭。為了怕失去愛,對出軌的丈夫百般忍讓,即使已知所做的一切只是維繫一個有性無愛,卻又被小孩牽絆的空殼婚姻。為了讓自己在愛的壓力裡喘息,只得半夜毫無方向地飆車和嚎啕大哭。一切的委曲求全,只為承擔因為愛所產生的責任和後果:愛與恨彼此共生,是最艱難的人生課題。
若要解釋這樣一本沈重的家庭小說為何會受英國曼.布克獎評審的青睞(在此之前,安瑞特並不被賭盤看好;是的,英國人連這個也賭),在於作者有著看穿人情的犀利,描述各種因愛產生的掙扎或抗拒,迂迴或直接打到每個人的痛處。然而創傷不是不可療癒,而是當「失去愛」、「不被愛」變成一個迴避不掉的心理罩門,或是當愛變成咒罵的理由,我們該怎麼看待「愛」這門功課?該怎麼重新為「愛」而生存,恢復愛人的勇氣?對薇羅妮卡而言,當她誠實面對被傷害過的自己,才能從飄搖的婚姻中站起來,也才能從原生家庭給她的陰影走出來。當她重新發現「被愛修復」的自己,她的愛不再需要言語粉飾,也不再需要用道德或宗教來自我束縛。對她而言,即使人生不能重來,即使斯人已逝,是愛讓一切都不再那麼步步艱難。
有評者不解這本緩慢冗長,令人不舒服的小說為何會得曼.布克獎;也有評者認為這本小說選材無新意,敘述手法令人坐立難安,或認為作品充滿情緒的爆發力,直逼讀者內心深處,讓人又愛又恨。也有書評婉轉地說這本書實在沈悶,得百年之後才有人能了解。但這些褒貶對安瑞特應該不至是煩惱,因為這本真誠釋/示愛的書,最終給讀者療癒的希望。書中痛苦的薇羅妮卡聽到她八歲女兒在電話裡童言童語︰「我要告訴你一個字,那個字就是『愛』。」在一次訪談中,安瑞特透露此話來自她的女兒。這句話天啟般點醒了書中的薇羅妮卡,知道得多愛自己,才有能力愛人,而不再因恐懼失去而終日惶惑不安,或因愛而重蹈覆轍。
如果還有機會再遇見那位伊朗講者,我想告訴他,只有先真誠面對內心深處的家/痂/枷,才能和過去言和,「你現在需要的只是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