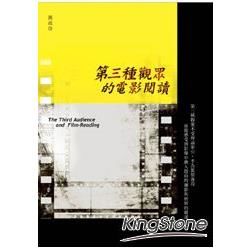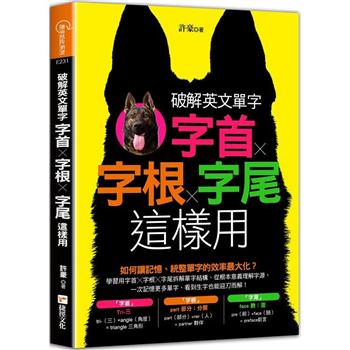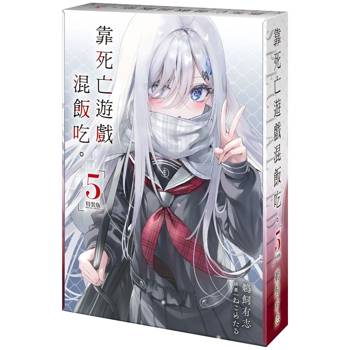代序
「第三種觀眾」的電影閱讀∕簡政珍
也許,藝術成就的高低,經常與「刻意」成反比。越刻意寫作的詩,越是遊戲和玩弄標籤的代言人。「刻意」也經常是想像力匱缺的遮掩,反諷的是,喜歡貼標籤的評論家因為找到標籤,卻將這些詩作哄抬成超凡的創意與想像力。
放眼當今的電影,「刻意」的影像敘述經常墜入兩種模式。許多好萊塢的影片以票房收入為標的,驚悚的大場面、激情的場景、濫情的結局是票房的保證。一般觀眾生活單調平凡,影片變成日常服用的安慰劑,現實不得意,因而渴望麻雀變鳳凰,小人物的日子蒼白無趣,因而有時幻想自己是終極警探,有時幻想是藍波為天下流第一滴血。攬鏡自照,五官長相乏善可陳,因此夢想與白馬王子做第六個夢。電影不論悲劇或是喜劇,都類似迷幻藥,遠離當下有血有肉的人生。所謂感動,是因為影像煽動觀眾的情緒,所謂「好看」,是因為大場面鋪成的輝煌與虛假。
另一種模式是,以刻意呆滯的影像散發學術理論的昏光。電影製作者為了和好萊塢的濫情影片有所區隔,刻意讓電影乾澀沈悶,以別於大眾口味。由於善用當代全球化與地域化的矛盾,經常在國際影展裡,因為呆滯乏味顯現第三世界的「不同」而得獎。部分得獎的原因是影像配合當代理論的標籤,讓喜歡套用理論的批評家趨之若鶩。電影製作因而類似是編導與批評家的共謀;拍攝這樣的電影是獲得評論讚揚因而得獎的契機,拍攝這樣的電影也讓那些只會套用理論而無法觀賞動人細節的批評家有了撰寫論文的題材。
於是,我們有一部《海上花》,在油燈下,妓女A對一個男子抱怨妓女B,接著妓女B也是在油燈下對同一個男子抱怨妓女A,接著又是類似的場景裡(永遠的油燈與圓桌),妓女間的唇舌,妓女和嫖客的抱怨,夾雜吃飯喝酒、瑣碎的言語,反反覆覆一個多小時。我們還有一部影片叫做《愛情萬歲》,女主角對著完全不動的半特寫鏡頭放聲大哭五、六分鐘。我們甚至還有一部《河流》,一個幾乎全黑,只有中間一個小光點似乎在動,但觀眾完全看不出在做什麼的畫面,這樣的畫面,鏡頭竟然可以持續不動十三分鐘。電影乏味如此,的確與眾「不同」。但這些影片都是批評家一再在《中外文學》、《電影欣賞》、《電影欣賞學刊》,以及各個學報給予掌聲的例子。
其實,假如把電影純粹當作一種娛樂,大眾在娛樂中得到情緒的抒解,濫情電影無可厚非。假如編導偶爾把影像當作一種形式的實驗與戲耍,即使自欺欺人,也未嘗不可。但是當大眾文化把濫情營造的票房當作電影成敗的指標,當批評家對沈悶影片的讚賞而造成價值觀的倒錯,進而將我們的電影工業帶入死胡同,我們禁不住要問:為什麼要讓濫情淹沒我們內心纖細的感情?為什麼要讓發霉的影像醃製我們的品味?在我們周遭的人生中,有多少動人的場景,他們竟然視而不見。除了大場面、大哭嚎、大動作,人所有的感情似乎已經麻痺。假如沒有套用國族論述、殖民論述、文化論述、同性戀論述、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批評家就沒東西可寫?假如不迎合批評家的理論框架,假如畫面不夠呆滯,影片就無法顯現「不同」,因而也就沒有「創意」,因而更不可能得獎?
但,我們在不少類似伊朗的《柳樹之歌》(Willow and Wind)的電影裡看到動人的影像。一個小男孩打破教室的玻璃,他必須在第二天上課前補好玻璃,否則就不准來上課。他的父親幾乎不管,他必須向新來的同學借錢。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場景,遠方,新同學去跟爸爸借錢時,鏡頭擺在近景的小男孩邊,鏡頭的觀照也是小男孩的觀照。有時鏡頭攝景兼容並蓄,觀眾看到遠方新同學爸爸「概略的」反應時,同時也看到主角小男孩臉上「細微的」表情。山坡上,他的頭髮在呼嘯的風中飛揚,他看到遠方的父子無聲的交談,這時有感覺的觀眾會不自覺地和小男孩的意識結為一體,觀眾會投入情境,因而看到旁邊風力發電機葉片徐徐的轉動,有意無意間暗示命運之輪的運轉,隱含小男孩的焦慮與不安。遠方的大人回頭看著主角,風聲似乎呼應小男孩在風浪中起伏的心情。一瞬間,有感覺的觀眾甚至悲從中來,他感受到小孩的無助、普天之下無數蒼生的無助,人情的溫暖、最後遠方同學的微笑傳遞的溫暖。
如此動人的影像,我們不可能在濫情影片裡緣木求魚,我們更不可能在那些酸腐洋溢、呆滯無趣的影片裡追逐幻影,正如我們不可能在四處飄散的煙花中尋求真正的花朵。動人的電影,撩撥的是我們人性共通的琴弦。感動的出發點,在於影像瞬間邀約觀眾遺忘自我,而融入電影的情境,並與角色的意識結為一體。觀眾在感動之餘,會進而對人生進一步的省思。感動是思想的基石,知性不是脫離人生蒼白的學理。
許多套用理論的批評家無法分辨情感與情緒。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與濫情影片涇渭分明,他們經常將枯燥無味的電影詮釋成藝術。他們無法感受到介於兩者之間,有不少讓人心動且引人深思的影像,正在真誠細緻地譜寫人生。人生的感動,不是濫情的眼淚,但有感覺的人會為某一個眼神、某一個背影、某一個堅持的手勢動容。假如文明有所成長,並不是「刻意」宣稱藝術的得以提升藝術,真正的藝術可能似重又輕、似無又有。但是我們的學界一再為那些虛假造作、刻意表現「藝術」的影片背書,以這樣的背書同時為自己的論文、升等、國科會計畫背書。
真正能體會那些幽微細緻的電影的是「第三觀眾」。「第三種觀眾」不會給濫情影片的眼淚與大場面淹沒,他更能看穿一些所謂的「藝術」是因為創意捉襟見肘,所以故弄玄虛。他領悟到最好的技巧是似有似無的技巧。他能在一個表象平靜的畫面裡看到層層的縱深。他感受到動人的影像飽含自然、稠密、隱約的細節。他體認到影像不是言說,因而「刻意」要說什麼的、明顯要表現什麼的,大都源自於想像力的欠缺。
「第三種觀眾」不一定是博士,但他可能比許多博士細膩敏銳。他不反對理論,甚至閱讀了很多理論,但是他和電影的第一個照面,絕不是理論的牽引。理論可以深化個人的思維,但閱讀與詮釋不是套入理論的框架。以前,我說過套用理論詮釋一首詩,幾乎就是謀殺一首詩。反諷的是,批評家無法謀殺許多感動「第三種觀眾」的影片,因為他們很難找到可以套用的理論,只是他們視野茫茫,不承認它們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第三種觀眾」一定是很有感覺的人。一個對人生有感覺的人,才會對文本有感覺;反過來說,一個對文本有感覺的人,因為他對人生有感覺。因為體會到「報紙登載的事,可能就是你的事,只是用了別人的名字」,人生才動人,影像才動人,「第三種觀眾」的閱讀才動人。
本書第一輯包含六篇論文,第一篇〈以「第三種觀眾」觀照兩種華人導演的影像敘述〉,與第二篇〈「第三種觀眾」感動的立足點〉,主要的重點是提出「第三種觀眾」的理念,並以這個理念審視當今華人電影南轅北轍的兩種樣貌,探討動人影像的立論基礎,以及觀眾受到感動中「知」與「情」的互動關係。第三篇〈當代華人影像敘述中「似有似無」的技巧〉,說明「第三種觀眾」對於「刻意」技巧的保留,最好的技巧應該似有似無。第四篇〈以李安的電影論全球化與「傳統敘述」的當代性〉,以李安當作「第三種觀眾」閱讀的具體案例,說明李安如何在全球化與地域化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本文進一步探討李安表象傳統、實際蘊含豐富的當代性,當代性並非玩弄形式的代名詞。第五篇〈塗寫與塗消--當代華語影像敘述家庭關係的書寫〉,說明「第三種觀眾」透過家庭關係的探討,與現有的理論對話,本文且藉由塗寫與塗消的意象與意涵,闡明影像敘述的書寫特性。第六篇〈門檻上的視野--當代大陸社會批評的影像敘述〉一方面說明影像的雙重視野,一方面探討大陸影像社會批評一把刀的兩面開口。表象的指陳,可能迂迴回到自身。整體來說,第五篇與第六篇的書寫,在於證實「第三種觀眾」如何運用理論而不是套用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篇〈以「第三種觀眾」觀照兩種華人導演的影像敘述〉,原來以〈「第三種觀眾」與華語「傳統寫實」的影像敘述〉發表於大陸《電影藝術》,由於該期刊字數的限制,發表的文章比本文少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第六篇〈門檻上的視野--當代大陸社會批評的影像敘述〉發表於《北京電影學院學報》,也是因為字數限制的關係,刪減了將近五分之一。除外,發表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的〈塗寫與塗消--當代華語影像敘述家庭關係的書寫〉與〈當代華人影像敘述中「似有似無」的技巧〉,為了與本書其他各篇的體例一致,中英文摘要皆刪除,各節小標題前面的一、二、三、四等也刪除。
本書第二輯「第三種觀眾與動人的影片」裡面的各篇文章,先後發表於《人間福報副刊》與《明道文藝》。由於報刊與雜誌提供的篇幅不同,各篇的長短不一定與相對應的重要性成正比。《戀戀三季》、《柳樹之歌》、《巴爾札克與小裁縫》、《那人那山那狗》與《色,戒》四部影片因為發表於《人間福報副刊》,賞讀比較短。另外,與其他發表於《明道文藝》的各篇相比,《一一》的閱讀也比較短,它是我心目中最想寫的一篇,但因為是專欄的第一篇,必須挪出四分之一的篇幅給專欄的開場白。除外,在本書第二輯裡,同一部影片的同個片段有時在不同文章裡出現,為了避免文字的重複,本書結集時,部份發表後的影片導讀必須稍做更動,《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最明顯的例子。再者,為了標題的統一,部分《明道文藝》發表的文章,結集時題目已略有變更。
最後,感謝所有發表我論文、導讀的學報、雜誌、副刊。感謝國科會通過我多年來對華語影像敘述的研究。感謝書林出版社。感謝所有那些讓我們看到細緻動人的人間、啟迪心靈讓我們看到纖細自我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