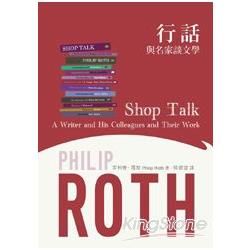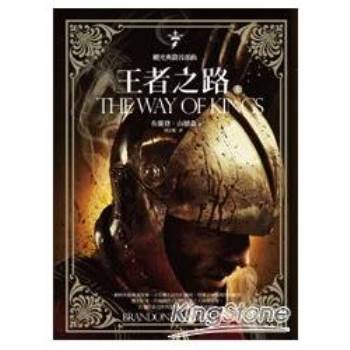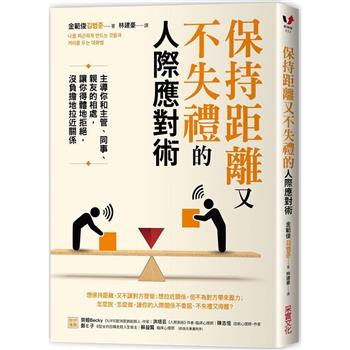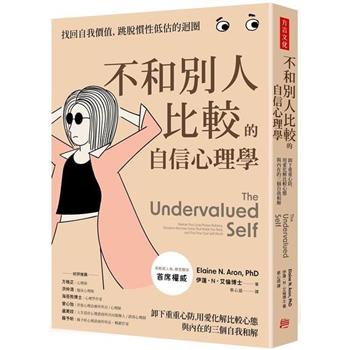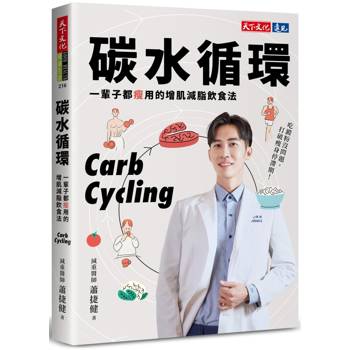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行話:與名家談文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林榮三文學首獎得主 伍軒宏 推薦
‧shoptalk:行話,職業用語;指某特定行業、領域人士使用的專業用語或主題
曼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菲利普‧羅斯在《行話──與名家談文學》中,與普里莫‧列維、阿哈隆‧艾沛菲爾德、伊凡‧克里瑪、米蘭‧昆德拉、愛德娜‧歐布萊恩、瑪麗‧麥卡錫等作家或對談、或魚雁往返,深入探討地域、歷史、文化、記憶,以及個人的生命軌跡如何影響作家們的書寫與創作。最後三篇文章則是羅斯對兩位友人──作家伯納‧瑪拉末、畫家菲利普‧加斯頓創作生涯的描繪,以及索爾‧貝婁作品的短評。藉由與文學高手對話、交流,羅斯同時也帶出自己對敘事和身份認同的想像和定位,不僅能讓寫作者獲得啟發與省思,也提供了讀者一場高水準的文學饗宴。
「羅斯借提問引導受訪作家透露出他們對寫作志業的信念,以及身為人的脆弱……顯示羅斯在訪談時目的清晰,且具備卓越的智慧。」──紐約時報書評
「羅斯的提問帶出受訪者堅定、具有強烈存在感的特質……他的讀者一看便知那是羅斯獨具的慧眼。」──紐約時報
「太精彩了,能夠一窺二戰後文學泰斗的創作歷程,而這些作家們的經歷也是讓羅斯保持書寫的動力。」──洛杉磯時報書評
本書特色
1. 獲獎無數的菲利普‧羅斯與國際知名作家的對談集
2. 文壇大家的對話與分享創作歷程,寫作者與讀者皆能獲得許多啟發
3. 可搭配羅斯的半自傳小說《再見,哥倫布》閱讀,更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命經驗
作者簡介:
菲利普‧羅斯 Philip Roth
羅斯出生於1933年美國紐澤西州的紐華克,芝加哥大學英文碩士。原計畫攻讀博士,但在24歲時放棄,專攻寫作,自此筆耕不斷,創作源源不絕,在美國文壇上舉足輕重。他有旺盛的寫作精力,筆鋒猶健,每年一部高質量的作品仍持續影響文壇。
身為文壇長青樹的他,獲獎無數。自26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再見,哥倫布》時,即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寫作生涯中曾三次獲福克納小說獎、兩次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兩次書評獎、美國筆會╱福克納獎、白宮頒發的美國國家藝術獎章、美國藝術與人文學院最高獎──小說金獎的殊榮,1998年以《美國牧歌》拿下普立茲小說獎。2005年他成為第三位在世時,作品即入選美國經典文庫的作家。2011年獲英國曼布克國際文學獎。
譯者簡介
陳婉容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畢業。曾從事英文教材編輯,現為自由譯者,譯有《綠野仙蹤》(逗點文創出版)、菲利浦.羅斯《波特諾伊的怨訴》(合譯,書林出版)、《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逗點文創出版),也偶爾寫字自娛。喜歡山嵐、N次貼,以及在街巷中迷走和電車裡的眾生相。
於倫敦、康乃狄克
與米蘭‧昆德拉
[1980]
此訪談是我拜讀過米蘭‧昆德拉《笑忘書》的譯稿後,與他兩次進行對談的濃縮內容──一次是他首度到訪倫敦的時候,另一次則在他初訪美國時進行。他這兩次旅程的起點都是法國;自一九七五年起,他與妻子便以流亡者的身分居住在雷恩,並於當地大學任教。現在他們搬到巴黎了。我們對談的時候,昆德拉偶爾會講法語,不過主要還是說捷克語。他的妻子維拉負責為我倆翻譯。彼得‧庫西將最終版的捷克文稿譯成英文。
羅斯:你認為世界很快就會毀滅了嗎?
昆德拉:那得視你如何定義很快這個詞。...
1 於都靈,與普里莫‧列維
2 於耶路撒冷,與阿哈隆‧艾沛菲爾德
3 於布拉格,與伊凡‧克里瑪
4 於紐約,與以撒‧辛格談布魯諾‧舒茲
5 於倫敦、康乃狄克,與米蘭‧昆德拉
6 於倫敦,與愛德娜‧歐布萊恩
7 與瑪麗‧麥卡錫的書信交流
8 瑪拉末寫意
9 加斯頓的畫
10 重讀貝婁
- 作者: 菲利普‧羅斯 譯者: 陳婉容
- 出版社: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21 ISBN/ISSN:978957445578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