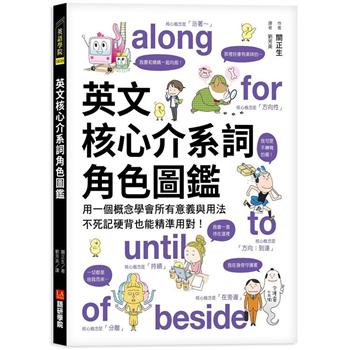再版序
1.
「我們就是要這麼做,叫那些老頭子知道自己的時代結束了。」(P.19)
說這句話的小劇場導演現在不知哪裡去了,可是我卻清楚記得她話不多,聲音細,音節短,尾音上揚。
2.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初版於1999 年,出版後不到三年,許多人就跟我反應說絕版了。
「到圖書館去借出來影印好了。」我通常如此回應。最近幾年,有人在露天拍賣買了一本,我乾脆請他幫忙掃成PDF檔給需要的人。
那現在為何要再版呢?也許是閱讀和典藏的慣性吧?紙本的時代終於結束了嗎?出乎意料,也許還有好一段時間要走。
3.
這本書原是我的英文博士論文,寫於1991 年,從暑假開始一直寫到初雪來臨。那時候我是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表演研究所的博士生,在Bobst 總圖六樓租了一個研究小間,裡頭有書櫃和寫字桌,抽屜還可以上鎖,但我不使用的時候別人也可以進去用,那時最高興的是研究小間還可以抽煙。
一星期五天,我每天早上用過早餐後,從東村第二大道12街的老公寓走15分鐘到研究小間。早課大約寫三個小時,然後到對面的華盛頓廣場走兩圈,吃個披薩或三明治,曬曬太陽,保持戰力。午課一點半開始,五點半左右結束。晚餐後,整理第二天要寫的資料,照原訂章節大綱擬出一頁左右的書寫重點,十二點前就寢。週末去唐人街買菜、吃飯,或者跟「博士論文寫作受難者聯誼會」聚一聚,相濡以沫。
那段期間幾乎「六親不認」,大隱隱於市。行走於觀光客、藝術家、名士淑女、大師巨賈滿街流竄的東村、蘇活,也沒有半個人理你。沒有看戲、沒有音樂會,只有週六晚上八點買份三磅重的《紐約時報》週末版回家,維持跟這個世界的一縷牽連。
這種修道院生活生產力很高,大約三星期可以完成一章初稿,看完一遍,就到第九街的全真影印行拷貝三份:一份留在老公寓,一份鎖在研究小間,還有一份放在包包裡隨身攜帶。紐約市那時候火災、搶劫頻率挺高的,杞人憂天之心不可無。章與章之間有個準備週,算是給自己慰勞,然後,開始下一個輪迴。四時變化忽悠,只記得有一天走出總圖,從La Guadia Place 往南瞭望,看見世貿大樓雙塔在夕陽餘暉中金光閃閃──下個季節這一切就結束了。
4.
這本博士論文叫 The Little Theatre Movement of Taiwan (1980-89):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指導教授是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託天之福,寫作蠻順利的,前後只花了四個半月初稿就完成了,接下來的四、五個月進行附錄、註釋、修訂、編排、改寫、校對、審查,到送出口試本時,猛抬頭,華盛頓廣場村的櫻花早已「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了。
但是《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這本專書的出版相對來說,就拖拖拉拉的,不只缺乏紀律,甚至連學術責任心都沒了。我還記得那時候姚一葦先生碰到我就說:「你的博士論文要趕快出版呀!」
1994 年秋我在國立藝術學院戲劇所開了「台灣現代戲劇專題研究」這門課,期末召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特別請到姚老師當我們的開幕嘉賓──就我所知,這是第一個台灣劇場史研討會──姚老師總結說:「大家要努力寫論文,趕快出版啊!」有圖為證:
5.
1999 年暑假,在揚智出版社于善祿企劃主編的努力下,《台灣小劇場運動史》終於問市了,但是,就我個人而言,這本書隨即成了孤兒──原因是稍早,1998 年12 月13-14 日,我在賽夏族矮靈祭上突然的蛻變,讓我的學術研究旨趣和方法有了180 度的轉彎:從向外改成向內,往前探看變成往後追溯,文字理解逐步讓給了身體行動,如何取代了為何。
個人原因之外,大環境也在改變:2000 年民進黨首次執政,台灣研究成為顯學。國立藝術學院在一片高校升級風中,也被迫成了「臺北藝術大學」,從此跌入庸庸碌碌、競逐補助之途。千禧年第一道曙光照到島上時,我跟自己說:《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已出版了,台灣戲劇研究也有他校在開了,讓我們啟程吧。
於是,每天早上起床梳洗後,我就在書房翻開斑駁的矮靈祭歌歌詞,點起蠟燭,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吟唱下去。伴隨我的首先是劇場大師葛羅托斯基,五年之後,又來了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身體行動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簡稱MPA)的探索,跟我1980 年代的留學研究同出一脈,前呼後應。有些時候我腦海會吹落一陣西風:在小劇場運動走進歷史之後,我大概是少數幾個依然逆著時代之風行走的人?
MPA 是劇場先賢注視之下生命藝術的發現之旅,風景深邃幽遠,雲蒸霞蔚,千巖競秀,只是一眨眼,時序就來到了今天:2017年聖誕節前夜。
6.
那美好的仗,我們打完了。
但是,我不想這樣結論。1980 年代台灣的小劇場運動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智慧財產,每個人都有權利來繼承和運用它份內的這個遺產。因此,《台灣小劇場運動史》這次再版,其主要內容和編排沒有任何更動,原因是那代表著上一個世代一個青年的理想、掙扎和行動──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或好或壞,就讓它以那個時代的模樣粉墨登場了。
至於本文開頭那位小劇場導演的慷慨陳詞,我想,也成了我們共同的智慧和傳統了。我很高興捕捉了這彷如風中燭火的一句話。在小劇場運動近40 周年之際,在台北反勞基修惡大遊行之後,讓我們逆著時代之風繼續前進:
我們就是要這麼做,叫那些老頭子知道自己的時代結束了。
──這老頭子可以是我們中的任何人,包括那位話不多、語音短促上揚的小劇場導演。
國家藝術庭園,2017.12.24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自1999年出版以來,已經成了當代台灣戲劇研究的一本必讀之作。這本專書原係鍾明德1992年完成於紐約大學表演研究所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謝喜納和其他口試委員一致評定為「傑出」。透過1986-89三年的田野調查,親身參與,以及對現代社會、文化和劇場史料的細心判讀,鍾明德為台灣1980年代最活躍的戲劇文化潮流留下了可靠的、動人的、不可磨滅的身影。
本書特色
1. 爬梳1986-89年間台灣小劇場的發展,詳盡介紹各個劇團的歷程與簡史。
2. 深度評析台灣小劇場運動如何反映當下社會及政治現狀。
3. 台灣劇場史的重要參考書。
4. 適合劇場研究者,戲劇相關科系教師及學生,以及表演工作者閱讀。
作者簡介:
鍾明德
紐約大學戲劇博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著述有《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2018)、《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2013)、《從貧窮劇場到藝乘:薪傳葛羅托斯基》(2007)《OM︰泛唱作為藝乘》(2007)、《神聖的藝術:葛羅托斯基的創作方法》(2001)、《舞道:劉紹爐的舞蹈路徑與方法》(1999)、《繼續前衛:尋找整體藝術及當代台北文化》(1997)、《現代戲劇講座:從寫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1995)、《補天:麵包傀儡劇場在台灣》(1994)、《在後現代主義的雜音中》(1989)、《紐約檔案》(1989)、《從馬哈╱薩德到馬哈台北》(1988)等書。
TOP
作者序
再版序
1.
「我們就是要這麼做,叫那些老頭子知道自己的時代結束了。」(P.19)
說這句話的小劇場導演現在不知哪裡去了,可是我卻清楚記得她話不多,聲音細,音節短,尾音上揚。
2.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初版於1999 年,出版後不到三年,許多人就跟我反應說絕版了。
「到圖書館去借出來影印好了。」我通常如此回應。最近幾年,有人在露天拍賣買了一本,我乾脆請他幫忙掃成PDF檔給需要的人。
那現在為何要再版呢?也許是閱讀和典藏的慣性吧?紙本的時代終於結束了嗎?出乎意料,也許還有好一段時...
1.
「我們就是要這麼做,叫那些老頭子知道自己的時代結束了。」(P.19)
說這句話的小劇場導演現在不知哪裡去了,可是我卻清楚記得她話不多,聲音細,音節短,尾音上揚。
2.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初版於1999 年,出版後不到三年,許多人就跟我反應說絕版了。
「到圖書館去借出來影印好了。」我通常如此回應。最近幾年,有人在露天拍賣買了一本,我乾脆請他幫忙掃成PDF檔給需要的人。
那現在為何要再版呢?也許是閱讀和典藏的慣性吧?紙本的時代終於結束了嗎?出乎意料,也許還有好一段時...
»看全部
TOP
目錄
目次
再版序
出版緣起
前言與誌謝
圖表目錄
第一章 導 論
一、測繪小劇場運動
二、定義「小劇場」
三、小劇場運動興起的背景與緣由
四、小劇場運動的分期問題
五、敘事許可、主題及其它
第一部分 第一代小劇場與實驗劇場
第二章 一切由《荷珠新配》開始:蘭陵劇坊的初步實驗與小劇場運動
一、耕莘實驗劇團時期的劇坊訓練
二、《荷珠新配》一役功成
三、關於蘭陵劇坊的初步結論
第三章 我們一同走走看:實驗劇展、戲劇教育與校園劇場活動
一、實驗劇展開鑼
二、「五加一」屆實驗劇展的內容與特色
三、實驗劇展的突破與...
再版序
出版緣起
前言與誌謝
圖表目錄
第一章 導 論
一、測繪小劇場運動
二、定義「小劇場」
三、小劇場運動興起的背景與緣由
四、小劇場運動的分期問題
五、敘事許可、主題及其它
第一部分 第一代小劇場與實驗劇場
第二章 一切由《荷珠新配》開始:蘭陵劇坊的初步實驗與小劇場運動
一、耕莘實驗劇團時期的劇坊訓練
二、《荷珠新配》一役功成
三、關於蘭陵劇坊的初步結論
第三章 我們一同走走看:實驗劇展、戲劇教育與校園劇場活動
一、實驗劇展開鑼
二、「五加一」屆實驗劇展的內容與特色
三、實驗劇展的突破與...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鍾明德
- 出版社: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21 ISBN/ISSN:978957445767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68頁
- 商品尺寸:長:230mm \ 寬:170mm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