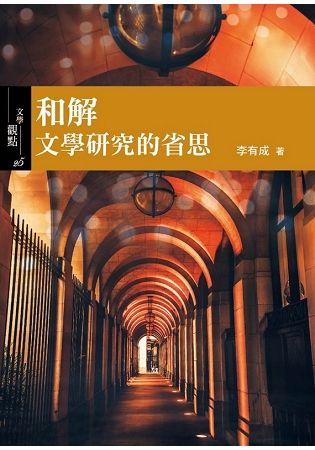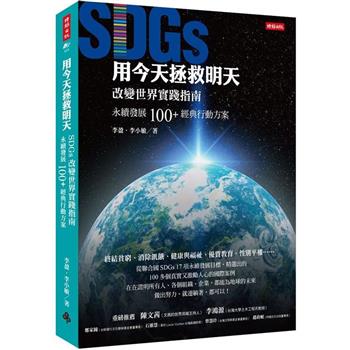《和解》一書所收諸篇反映的是作者面對理論,介入文本的基本態度。從這個視角看,這也是一本有關閱讀的書,記錄的是讀書經驗,也是批評立場清楚一致的閱讀行為的結果。作者一向強調學術研究的淑世功能,其研究投射着個人的感情與思想,隱含或展現生命關懷。本書收錄的文章雖然是作者為因應不同場合邀請而寫的,卻也是在學術論文與專書之外,另一個可以抒發胸臆的空間。這些文章也反映多年來作者所秉持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立場。
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檢視作者的學術理念與理論立場,是對其學思歷程的省思。第二輯主要是為學術著作所撰寫的導讀、序文或評論,加上兩篇專文評介近年呼聲甚高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第三輯則以當代英美小說書評為主,並有專文反思華裔與非裔美國文學。附錄三篇為座談與訪談紀錄,內容與本書若干議題相關,納入書中一併提供讀者進一步參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3 |
中國文學總論 |
$ 253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272 |
Social Sciences |
$ 281 |
中文書 |
$ 288 |
華文文學研究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有成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國文學學門召集人,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並曾多年兼任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近期著作有《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複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他者》、《離散》、《記憶》、《荒文野字》、《詩的回憶及其他》及詩集《鳥及其他》、《時間》及《迷路蝴蝶》等;另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合編)、《離散與家國想像》(合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合編)及《生命書寫》(合編)等書。
李有成
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國文學學門召集人,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並曾多年兼任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近期著作有《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複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他者》、《離散》、《記憶》、《荒文野字》、《詩的回憶及其他》及詩集《鳥及其他》、《時間》及《迷路蝴蝶》等;另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合編)、《離散與家國想像》(合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合編)及《生命書寫》(合編)等書。
目錄
001 ∕ 自序
【第一輯】
009 ∕ 南港四十年
014 ∕ 我寫《他者》
021 ∕ 理論與我
029 ∕ 翻譯的慾望
033 ∕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
035 ∕ 關於跨領域研究
038 ∕《中外文學》四十年後
042 ∕《歐美研究》年屆不惑
【第二輯】
049 ∕ 關注式閱讀:馮品佳的《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
054 ∕ 醫學之為隱喻:陳重仁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
059 ∕ 尋找家的意義:劉紀雯的《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
065 ∕ 知識與文采:張錯的《西洋文學術語手冊》
071 ∕ 知識分子的畫像︰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經典版
080 ∕ 殖民語言的今生來世:讀《後殖民文學的語言》
088 ∕ 雙文化寫作:任璧蓮的《老虎書寫:藝術、文化及相倚互賴的自我》
096 ∕ 書寫與背叛:哈金的《在他鄉寫作》
102 ∕ 恩古吉:清貧理論與解放文學
107 ∕ 阿多尼斯:流放、語言、詩
【第三輯】
113 ∕ 和解:鮑爾溫的《山巔宏音》
131 ∕ 階級與性:麥克尤恩的《卻西爾海灘》
139 ∕ 美國夢碎:莫欣‧哈密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
152 ∕ 都是病毒惹的禍:昆祖魯的《失控》
160 ∕ 在帝國的陰影下:歐大旭的《和諧絲莊》
172 ∕ 冷戰歲月:歐大旭的《沒有地圖的世界》
181 ∕ 解構愛國主義:哈金的《折騰到底》
185 ∕ 布希時代的哀歌:班‧方登的《半場無戰事》
188 ∕ 遺忘的政治:石黑一雄的《被埋葬的記憶》
193 ∕ 怪異建制下的文學
199 ∕ 清純與坦率:歐巴馬的自傳
201 ∕ 裴克與非裔美國論述
203 ∕ 家國想像:離散與華裔美國文學
213 ∕ 臺灣的非裔美國研究
【附錄】
233 ∕ 在學術與創作之間:南方學院座談會紀錄
255 ∕ 臺大歲月:李有成老師訪談錄
275 ∕ 理論的基因:訪李有成談理論、年代與創作
301 ∕ 跋 一座豐盈的海:記與有成交往四十年 張錦忠
【第一輯】
009 ∕ 南港四十年
014 ∕ 我寫《他者》
021 ∕ 理論與我
029 ∕ 翻譯的慾望
033 ∕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
035 ∕ 關於跨領域研究
038 ∕《中外文學》四十年後
042 ∕《歐美研究》年屆不惑
【第二輯】
049 ∕ 關注式閱讀:馮品佳的《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
054 ∕ 醫學之為隱喻:陳重仁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
059 ∕ 尋找家的意義:劉紀雯的《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
065 ∕ 知識與文采:張錯的《西洋文學術語手冊》
071 ∕ 知識分子的畫像︰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經典版
080 ∕ 殖民語言的今生來世:讀《後殖民文學的語言》
088 ∕ 雙文化寫作:任璧蓮的《老虎書寫:藝術、文化及相倚互賴的自我》
096 ∕ 書寫與背叛:哈金的《在他鄉寫作》
102 ∕ 恩古吉:清貧理論與解放文學
107 ∕ 阿多尼斯:流放、語言、詩
【第三輯】
113 ∕ 和解:鮑爾溫的《山巔宏音》
131 ∕ 階級與性:麥克尤恩的《卻西爾海灘》
139 ∕ 美國夢碎:莫欣‧哈密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
152 ∕ 都是病毒惹的禍:昆祖魯的《失控》
160 ∕ 在帝國的陰影下:歐大旭的《和諧絲莊》
172 ∕ 冷戰歲月:歐大旭的《沒有地圖的世界》
181 ∕ 解構愛國主義:哈金的《折騰到底》
185 ∕ 布希時代的哀歌:班‧方登的《半場無戰事》
188 ∕ 遺忘的政治:石黑一雄的《被埋葬的記憶》
193 ∕ 怪異建制下的文學
199 ∕ 清純與坦率:歐巴馬的自傳
201 ∕ 裴克與非裔美國論述
203 ∕ 家國想像:離散與華裔美國文學
213 ∕ 臺灣的非裔美國研究
【附錄】
233 ∕ 在學術與創作之間:南方學院座談會紀錄
255 ∕ 臺大歲月:李有成老師訪談錄
275 ∕ 理論的基因:訪李有成談理論、年代與創作
301 ∕ 跋 一座豐盈的海:記與有成交往四十年 張錦忠
序
自序
二○一六年將「他者三部曲」的《他者》、《離散》及《記憶》三書出齊之後,我著手整理多年來累積的散篇文字,同年還因此出版了兩部文集,即《詩的回憶及其他》與《荒文野字》。前者所收諸文多與馬華文學有關,後者的內容則稍顯駁雜,議題也較為廣泛,有評論,有記事,有懷人,有憶往,屬於西方文類定義下廣義的散文。此外另有一批評論文字,與學術研究或英美文學關係較為密切,性質也比較集中,當時就刻意排除在上述兩部文集之外,希望另行單獨成書,因此才有現在這部《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詩的回憶及其他》出版於馬來西亞,《荒文野字》在中國大陸刊行,《和解》則在臺灣印行,這三部文集有機會在華文世界的主要地區流通,也是我的著述生涯中難得的因緣。
這部文集所收各篇文字幾乎全是因應不同場合的邀請而寫的,儘管如此,卻也是我在學術論文與專書之外,另一個可以讓我抒發胸臆的空間。這些文字若有任何微言大義,所反映的大抵也是我多年來所秉持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立場。就這一點而言,這些文字與我的學術著作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書名《和解》原為論非裔美國作家鮑爾溫(James Baldwin)小說《山巔宏音》(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文的篇名,如今借用作為書名,正好與我十餘年前出版的《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一書的書名前後輝映。《踰越》全書所關心的,如副書名所示,為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由於非裔美國人在新世界悲慘的歷史命運與不幸的生存境遇,那本書富於批判意識與抗爭精神不難想像。《和解》這本文集雖然不乏饒富批判性的篇章,但是書中更多的是反躬自省的時刻,這也說明了何以我要以「文學研究的省思」作為書的副書名。在這樣的背景下,書名《和解》因此也許不無意義。正如我在論小說《山巔宏音》的結語時所說的,「寫作《山巔宏音》,挖掘美國黑人的歷史,痛苦地正視美國現實中難堪的一面,並且以愛與救贖面對這樣的美國現實,鮑爾溫其實也嘗試要與美國和解」。事實上,踰越或和解都只不過是策略與過程,目的無非是為了尋找與建立新的秩序。這不也是我們所熟知的眾多文學經典的終極關懷或使命嗎?《紅樓夢》如此,《西遊記》如此,《馬克白》如此,《漢姆雷特》也是如此。
我已經到了孔子說的不踰矩的年齡,平凡生活,隨遇而安,尚知惜緣惜福,與這個世界向來少有爭執,因此我與世界之間也不發生和解或不和解的問題。只不過我一向強調學術研究的淑世功能,我的研究自然投射瞂個人的感情與思想,隱含或展現的是我的生命關懷。我在研究上的省思恐怕不只是為了自我砥礪而已,同時也是為了發現自己,了解自己。《和解》應該是這樣的一本文集。為了方便閱讀,我把全書各篇粗分為三輯。第一輯主要在檢視個人之學術理念與理論立場,可說是對個人學思歷程的省思。第二輯所收乃個人為若干學術著作所撰寫之導讀、序文或評論,這一輯另有兩篇專文評介近年來呼聲甚高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第三輯諸篇則以當代英美小說之書評為主,並有長文反思華裔與非裔美國文學。附錄三篇分別為座談與訪談紀錄,內容也與本書許多議題相關,納入書中或可提供讀者進一步參考。《和解》的眾多篇章反映的可說是我面對理論,介入文本的基本態度。從這個視角看,這也是一本有關閱讀的書,記錄的是我的讀書經驗,也是批評立場清楚一致的閱讀行為的結果。
這本文集有不少篇幅觸及離散的議題,由於之前我出版過《離散》一書,因而這幾年來經常會被問到這個議題。離散涉及的層面很廣,我在《離散》一書中已經多有論述,這裏無法詳說。我最常被問及的是:離散是否應該有個盡期?換言之,離散是否應該設定結束的時間?我對這種機械式的問題其實興趣不大。如果我們對離散的學術稍有了解,就應該知道:非洲人被迫離開黑色非洲已經三、四百年,還是有人在談非洲離散(African diaspora)或黑人離散(black diaspora)。愛爾蘭人離開故土一、兩百年了,不還是有人在談愛爾蘭離散(Irish diaspora)?猶太人的狀況更為大家所耳熟能詳。離散顯然不全是時間問題。我論離散,除了視離散為一種生存狀態外,同時還把離散理解為一種心境,一種心態。離散意識本來就超越國家疆界,召喚的不僅是共時的、平面的生存經驗,同時還有歷時的、垂直的文化經驗;在離散意識的觀照下,這樣的經驗不只具有當下現實的意義,而且還展現了歷史縱深的維度。從這個角度不難看出離散與文化記憶的關係,離散之為方法因此也不難了解。
我在《離散》一書中特意將離散模塑為某種公共領域,以凸顯離散的公共性與批判性。離散介於故土家園與移居地之間,用人類學家柯立佛(James Clifford)的話說,即是在「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因此離散者佔有時空上的便利,可以對家園故土或移居地展開對話或批判。我在書中舉例甚多,尤其以白先勇、哈金、梁志英(Russell Leong)、古雷希(Hanif Kureishi)、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等人的文本為例,以突出離散的批判意義。如果無法看出離散的這一層面向,只能說對離散的了解相當浮面。離散對移居地的貢獻也應該一提,這正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都會觀感與現代主義的冒現〉(“Metropolitan Percep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m”)長文中特意強調的重點,他大力推崇移民現象對藝術與文化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離散不是威廉斯的用語,只是他文中的指涉應為離散社群當無疑慮。在威廉斯看來,外來的「藝術家、作家及思想家從自己的國家或地方文化中解放或掙脫出來,被放置在其他民族語言和民族視覺傳統的全新關係中」,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嶄新而充滿活力的環境,因此也會受到全然不同的衝擊。威廉斯特別以語言為例,說明對外來移民而言,何以新掌握的語言是一種可以自由試驗與塑造的媒介。這容或也是哈金在其《在他鄉寫作》一書〈為外語腔辯護〉一章中所刻意提到的,「邊界是我們唯一可以生存並對這個語言作出貢獻的地方」。哈金所說的「邊界」正是移民作家的離散空間,而所謂「這個語言」無疑指的是美國英語。其實過去二、三十年我們在臺灣乃至於亞太地區從事亞美文學研究,目的之一不也是為了凸顯跨太平洋的離散感性在形塑美國文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這本文集之所以選在我退休前夕出版,主要是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的發行人蘇正隆與出版經理蘇恆隆的美意。編輯張麗芳不僅耐心催稿,在文集的出版過程中更是不辭辛勞,費心費力。我要向這幾位書林的朋友表示誠摯的謝意。文集中有若干篇章在發表前曾經單德興、馮品佳、張錦忠、高嘉謙等過目,我內心十分感激。就像我過去所出版的許多著作,這本文集的文字輸入和校對,助理曾嘉琦貢獻最多。沒有嘉琦的幫忙,這本文集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出版的,謝謝嘉琦的辛勞。在學術界四十年,受惠於師長、同事及同行的地方甚多,我要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說一聲謝謝。是為序。
二○一八年一月八日於中央研究院
二○一六年將「他者三部曲」的《他者》、《離散》及《記憶》三書出齊之後,我著手整理多年來累積的散篇文字,同年還因此出版了兩部文集,即《詩的回憶及其他》與《荒文野字》。前者所收諸文多與馬華文學有關,後者的內容則稍顯駁雜,議題也較為廣泛,有評論,有記事,有懷人,有憶往,屬於西方文類定義下廣義的散文。此外另有一批評論文字,與學術研究或英美文學關係較為密切,性質也比較集中,當時就刻意排除在上述兩部文集之外,希望另行單獨成書,因此才有現在這部《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詩的回憶及其他》出版於馬來西亞,《荒文野字》在中國大陸刊行,《和解》則在臺灣印行,這三部文集有機會在華文世界的主要地區流通,也是我的著述生涯中難得的因緣。
這部文集所收各篇文字幾乎全是因應不同場合的邀請而寫的,儘管如此,卻也是我在學術論文與專書之外,另一個可以讓我抒發胸臆的空間。這些文字若有任何微言大義,所反映的大抵也是我多年來所秉持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立場。就這一點而言,這些文字與我的學術著作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書名《和解》原為論非裔美國作家鮑爾溫(James Baldwin)小說《山巔宏音》(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文的篇名,如今借用作為書名,正好與我十餘年前出版的《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一書的書名前後輝映。《踰越》全書所關心的,如副書名所示,為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由於非裔美國人在新世界悲慘的歷史命運與不幸的生存境遇,那本書富於批判意識與抗爭精神不難想像。《和解》這本文集雖然不乏饒富批判性的篇章,但是書中更多的是反躬自省的時刻,這也說明了何以我要以「文學研究的省思」作為書的副書名。在這樣的背景下,書名《和解》因此也許不無意義。正如我在論小說《山巔宏音》的結語時所說的,「寫作《山巔宏音》,挖掘美國黑人的歷史,痛苦地正視美國現實中難堪的一面,並且以愛與救贖面對這樣的美國現實,鮑爾溫其實也嘗試要與美國和解」。事實上,踰越或和解都只不過是策略與過程,目的無非是為了尋找與建立新的秩序。這不也是我們所熟知的眾多文學經典的終極關懷或使命嗎?《紅樓夢》如此,《西遊記》如此,《馬克白》如此,《漢姆雷特》也是如此。
我已經到了孔子說的不踰矩的年齡,平凡生活,隨遇而安,尚知惜緣惜福,與這個世界向來少有爭執,因此我與世界之間也不發生和解或不和解的問題。只不過我一向強調學術研究的淑世功能,我的研究自然投射瞂個人的感情與思想,隱含或展現的是我的生命關懷。我在研究上的省思恐怕不只是為了自我砥礪而已,同時也是為了發現自己,了解自己。《和解》應該是這樣的一本文集。為了方便閱讀,我把全書各篇粗分為三輯。第一輯主要在檢視個人之學術理念與理論立場,可說是對個人學思歷程的省思。第二輯所收乃個人為若干學術著作所撰寫之導讀、序文或評論,這一輯另有兩篇專文評介近年來呼聲甚高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第三輯諸篇則以當代英美小說之書評為主,並有長文反思華裔與非裔美國文學。附錄三篇分別為座談與訪談紀錄,內容也與本書許多議題相關,納入書中或可提供讀者進一步參考。《和解》的眾多篇章反映的可說是我面對理論,介入文本的基本態度。從這個視角看,這也是一本有關閱讀的書,記錄的是我的讀書經驗,也是批評立場清楚一致的閱讀行為的結果。
這本文集有不少篇幅觸及離散的議題,由於之前我出版過《離散》一書,因而這幾年來經常會被問到這個議題。離散涉及的層面很廣,我在《離散》一書中已經多有論述,這裏無法詳說。我最常被問及的是:離散是否應該有個盡期?換言之,離散是否應該設定結束的時間?我對這種機械式的問題其實興趣不大。如果我們對離散的學術稍有了解,就應該知道:非洲人被迫離開黑色非洲已經三、四百年,還是有人在談非洲離散(African diaspora)或黑人離散(black diaspora)。愛爾蘭人離開故土一、兩百年了,不還是有人在談愛爾蘭離散(Irish diaspora)?猶太人的狀況更為大家所耳熟能詳。離散顯然不全是時間問題。我論離散,除了視離散為一種生存狀態外,同時還把離散理解為一種心境,一種心態。離散意識本來就超越國家疆界,召喚的不僅是共時的、平面的生存經驗,同時還有歷時的、垂直的文化經驗;在離散意識的觀照下,這樣的經驗不只具有當下現實的意義,而且還展現了歷史縱深的維度。從這個角度不難看出離散與文化記憶的關係,離散之為方法因此也不難了解。
我在《離散》一書中特意將離散模塑為某種公共領域,以凸顯離散的公共性與批判性。離散介於故土家園與移居地之間,用人類學家柯立佛(James Clifford)的話說,即是在「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因此離散者佔有時空上的便利,可以對家園故土或移居地展開對話或批判。我在書中舉例甚多,尤其以白先勇、哈金、梁志英(Russell Leong)、古雷希(Hanif Kureishi)、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等人的文本為例,以突出離散的批判意義。如果無法看出離散的這一層面向,只能說對離散的了解相當浮面。離散對移居地的貢獻也應該一提,這正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都會觀感與現代主義的冒現〉(“Metropolitan Percep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m”)長文中特意強調的重點,他大力推崇移民現象對藝術與文化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離散不是威廉斯的用語,只是他文中的指涉應為離散社群當無疑慮。在威廉斯看來,外來的「藝術家、作家及思想家從自己的國家或地方文化中解放或掙脫出來,被放置在其他民族語言和民族視覺傳統的全新關係中」,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嶄新而充滿活力的環境,因此也會受到全然不同的衝擊。威廉斯特別以語言為例,說明對外來移民而言,何以新掌握的語言是一種可以自由試驗與塑造的媒介。這容或也是哈金在其《在他鄉寫作》一書〈為外語腔辯護〉一章中所刻意提到的,「邊界是我們唯一可以生存並對這個語言作出貢獻的地方」。哈金所說的「邊界」正是移民作家的離散空間,而所謂「這個語言」無疑指的是美國英語。其實過去二、三十年我們在臺灣乃至於亞太地區從事亞美文學研究,目的之一不也是為了凸顯跨太平洋的離散感性在形塑美國文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這本文集之所以選在我退休前夕出版,主要是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的發行人蘇正隆與出版經理蘇恆隆的美意。編輯張麗芳不僅耐心催稿,在文集的出版過程中更是不辭辛勞,費心費力。我要向這幾位書林的朋友表示誠摯的謝意。文集中有若干篇章在發表前曾經單德興、馮品佳、張錦忠、高嘉謙等過目,我內心十分感激。就像我過去所出版的許多著作,這本文集的文字輸入和校對,助理曾嘉琦貢獻最多。沒有嘉琦的幫忙,這本文集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出版的,謝謝嘉琦的辛勞。在學術界四十年,受惠於師長、同事及同行的地方甚多,我要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說一聲謝謝。是為序。
二○一八年一月八日於中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