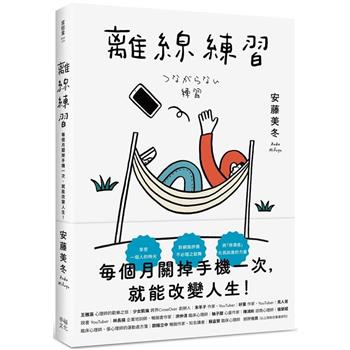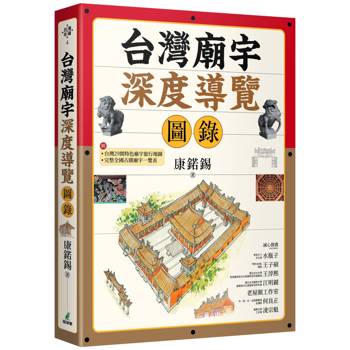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始於七○年代,並在八○年代開始蓬勃發展。本書集結此領域最具代表、品質優異的文章共16篇,文類包含小說、戲劇等,探討議題有種族、階級、典律、殖民,以及性別,研究方法與理論等相當多元,充份展現本土三十餘年在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
全書內容共分六部份:「導論」、輯一「閱讀非裔美國經典」、輯二「理論與非裔美國文學研究」、輯三「閱讀摩里森」、輯四「非裔美國戲劇研究」、輯五「源自加勒比海的非裔美國文學讀摩里森」。其中「導論」提供重要的知識背景與研究脈絡,並詳述非裔美國文學在臺灣的建制史,完整呈現多年來臺灣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整體樣貌,是具有文學研究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本書編選嚴謹、品質優異,是國內第一本非裔美國文學研究成果的合集專書。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再現黑色風華: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79 |
中文書 |
$ 408 |
世界文學總論 |
$ 422 |
英美文學 |
$ 432 |
外國文學研究 |
$ 432 |
文學作品 |
$ 432 |
世界文學論集 |
$ 112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再現黑色風華: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馮品佳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為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合聘研究員,與國立交通大學亞裔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交通大學副教務長、外文系系主任、交大電影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哈佛大學Fulbright訪問學者、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文學門召集人與史丹佛大學人文社會中心國際訪問學者。曾獲得2015年第59屆教育部學術獎,2007年、2010年與2013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研究領域包括英美小說、女性書寫、離散文學與文化研究、少數族裔論述以及電影研究。論文發表於《歐美研究》、《中外文學》、《英美文學評論》、以及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ELUS, Tamkang Review等國內外期刊。著有中外專書數本;譯著有《Love》與《木魚歌》
馮品佳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為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合聘研究員,與國立交通大學亞裔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交通大學副教務長、外文系系主任、交大電影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哈佛大學Fulbright訪問學者、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外文學門召集人與史丹佛大學人文社會中心國際訪問學者。曾獲得2015年第59屆教育部學術獎,2007年、2010年與2013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一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研究領域包括英美小說、女性書寫、離散文學與文化研究、少數族裔論述以及電影研究。論文發表於《歐美研究》、《中外文學》、《英美文學評論》、以及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ELUS, Tamkang Review等國內外期刊。著有中外專書數本;譯著有《Love》與《木魚歌》
目錄
馮品佳 導論:台灣非裔美國文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1
一、 閱讀非裔美國經典
李有成 01 踰越:《道格拉斯自撰生平敘述》中的識字政治27
何文敬 02 蔡士納《傳統精髓》中的種族與階級47
紀元文 03 疏離與認同:約翰‧魏德曼的《兄弟與看守者》69
李有成 04 和解:鮑爾溫與其《山巔宏音》91
二、 理論與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張錦忠 05 他者的典律:典律性與非裔美國女性論述111
蔡振興 06 還以顏色:裴克論歷史、文學理論與非裔美國表現文化131
李秀娟 07 從認知的邊緣出發:德希達和摩里森的文學秘密151
三、 閱讀摩里森
陳東榮 08 童妮‧摩里森與美國黑人文化民族主義──試讀《所羅門之歌》181
劉亮雅 09 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摩里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223
蔡佳瑾 10「歌唱的痛」:論童妮‧摩里森小說《爵士樂》中的凝視與聲音257
馮品佳著 11「咱是女孩倆」:《Love》中的雙人女性成長敘事157
吳哲硯譯
四、 非裔美國戲劇研究
劉雪珍 12 黑人女劇作家甘迺迪的「身體政治」:對異性恐懼之呈現169
姜翠芬 13 非裔美國戲劇中的被壓迫勞工形象──《圍籬》(Fences)的個案研究193
黃仕宜 14 歷史之餘:非裔美國人劇場中缺席的父親們289
五、 源自加勒比海的非裔美國文學讀摩里森
張淑麗 15 牙買加‧金凱德的(後)殖民政治寓言:表演或憤怒?401
馮品佳 16 蜜雪‧克莉芙的成長二重奏:《響螺》與《天堂無線可通》的認同政治433
作者簡介 463
索引 471
一、 閱讀非裔美國經典
李有成 01 踰越:《道格拉斯自撰生平敘述》中的識字政治27
何文敬 02 蔡士納《傳統精髓》中的種族與階級47
紀元文 03 疏離與認同:約翰‧魏德曼的《兄弟與看守者》69
李有成 04 和解:鮑爾溫與其《山巔宏音》91
二、 理論與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張錦忠 05 他者的典律:典律性與非裔美國女性論述111
蔡振興 06 還以顏色:裴克論歷史、文學理論與非裔美國表現文化131
李秀娟 07 從認知的邊緣出發:德希達和摩里森的文學秘密151
三、 閱讀摩里森
陳東榮 08 童妮‧摩里森與美國黑人文化民族主義──試讀《所羅門之歌》181
劉亮雅 09 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佟妮‧摩里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223
蔡佳瑾 10「歌唱的痛」:論童妮‧摩里森小說《爵士樂》中的凝視與聲音257
馮品佳著 11「咱是女孩倆」:《Love》中的雙人女性成長敘事157
吳哲硯譯
四、 非裔美國戲劇研究
劉雪珍 12 黑人女劇作家甘迺迪的「身體政治」:對異性恐懼之呈現169
姜翠芬 13 非裔美國戲劇中的被壓迫勞工形象──《圍籬》(Fences)的個案研究193
黃仕宜 14 歷史之餘:非裔美國人劇場中缺席的父親們289
五、 源自加勒比海的非裔美國文學讀摩里森
張淑麗 15 牙買加‧金凱德的(後)殖民政治寓言:表演或憤怒?401
馮品佳 16 蜜雪‧克莉芙的成長二重奏:《響螺》與《天堂無線可通》的認同政治433
作者簡介 463
索引 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