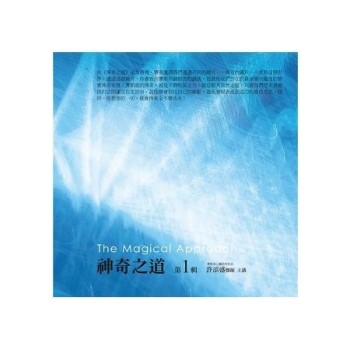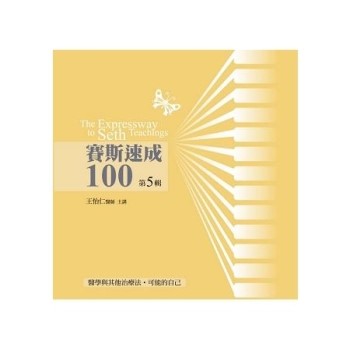自序
溪雲
唐僧皎然(730-799)撰有〈南池雜詠五首〉,其中〈溪雲〉一首自我初識以來,一直在心中盤旋縈繞,個別詩行三不五時幽幽浮現,而詩人彷彿古墳幽魂,也似謎樣精靈或神仙鬼魅,在迷濛夜色中飄然出現,雖然始終沈默不語,但其欲言又止之姿總是讓我一面默念其詩行,一面思索為何與我如此相遇:
舒卷意何窮
縈流復帶空
有形不累物
無跡去隨風
莫怪長相逐
飄然與我同
從年少時期起,對於雲我有一種氣質上的偏執:有雲之時,看雲、觀雲、望雲;無雲之時,想雲、念雲、盼雲。無論雲深雲淺,雲行雲止,各種雲的出現和變化讓習慣孤獨的我在青澀的歲月中有個傾訴的對象,好像擁有知心的秘密朋友,而縱使雲從不言語友情,但我心中總是暗忖,無言的雲必然不會吝惜給孤單的我一絲同情。直至現在我年已過花甲,每次有意或無意遥望天空的流雲,這份密密蘊藏的綿綿感情還是不斷點滴流露。對於皎然的詩,我也抱持一種觀雲的情懷,詩的境界及所言的一切,我未必真正懂得,更别奢言能夠深深體會,但縱使意義仍在雲深不知之處,我只能盼望自身還在唐詩的廬山之中,在詩義瀰漫的飄渺雲霧之中摸索究竟;或者,更重要的是,思索如何從皎然的禪詩中,通過與他者的相遇來理解自己的生命意義。
直展雲
〈溪雲〉之意旨到底為何?我非中文系出身,也不是唐詩專家,倘若恬不知羞,在此胡言亂語,恐遭方家竊竊私語指責。為免遭物議,不妨讓我先仿效閲讀英詩之方式,引介他人(蔣述卓)所為之paraphrase(用散文改寫韻文),以便從事初步的理解:
舒放捲曲你永無止歇,相隨流水又飄飛長空。
你有形,卻從不礙物,你無跡,逝去自隨風。
莫怪我與雲長相追逐,因為它飄飄與我相同。
就翻譯形式而言,上述文字可以視為一種「語内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這是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常見的一個轉換關係,讓古今之間得以貫通流動,方便現代讀者閲讀賞析。然而古今畢竟存在時間距離(temporal distance),任何翻譯,如伽德瑪(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所主張的,皆無法跨越原文和譯文之間的「根本間隙」(fundamental gulf)。我們不必是唐詩專家也可以覺察到,皎然的原文和現代的白話譯文之間──縱使同為中文──顯然存在形、音、義三方面的差異,以及兩者在翻譯美學上所呈現的得失問題。翻譯涉及語言的變化,就算在同一種語言之中相互轉換,變化不會只是平直開展, 因為語言的雲總是變幻莫測, 翻譯若可「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恐怕也只能窺其一二。
對流雲
做為中國文學最顯著的標誌之一,唐詩,無論盛唐、中唐或晚唐詩,在中西比較文學的領域裡總是一顆璀璨明珠,時時吸引文學譯/釋者前來朝聖。在這層意義上,〈溪雲〉是中西文化交流雲層裡的一朵孤雲,因為它並不像其他唐詩那麼顯目而讓人垂青。然而正因為歷來問津者少,一旦難得的英譯者出現,對於原先自以為是單獨一片浮雲的我而言,自然就不必再孤獨的流浪天空,反倒是有了機會和另一片陌生的雲共同形成文學社群的雲。查爾士.伊根(Charles Egan) 在Cloud Thicks, Whereabouts Unknown: Poems by Zen Monks of China(2010)這本書中,以「忠實且優雅的」(“faithful and elegant”)翻譯,將〈溪雲〉以英文再現,同時也賦予了這首詩新的生命:
Stretching and curling to what purpose?
Twining around the stream and belting the void above.
You have born form, but are not an encumbered thing;
Following the wind, leaving no trace behind.
Don’t blame me for always pursuing you:
Floating without roots, you are just like me.
「新的生命」不是指純然de novo 的創造,暗示〈溪雲〉經過了「輪迴轉世」(transmigration)的過程而徹底改頭換面;「新的生命」也不是指〈溪雲〉的物質/物理生命在新的語言宿主身上獲得自然延續;「新的生命」指的是〈溪雲〉不斷被更新的歷史生命,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評論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時念兹在兹的Überleben(afterlife),是語言生命的變化歷史,没有唯一的起點也没有唯一的終點,只有持續的且同時的生/死變化;「新的生命」其實指的是意義的誕生及/即死亡、催(生)及/即摧(毁),是以一種「冥誕」的慶生/死方式,讓意義自由自在的,隨其所遇而存活下去(live on/survivre)。
伊根的翻譯在我看來確實是faithful and ele(ct)gant(源自拉丁文éligere: choosing carefully)──他以研究唐詩所具的堅實信念(fidelity)來從事他所認為忠實的翻譯,而他精挑細選的英文字詞和句法讓他的英譯具有高度的文學性。用個譬喻來説,伊根的〈溪雲〉翻譯,即便其他譯/釋者可能另持異見,像是高雲族裡的卷雲、卷積雲和卷層雲,望之彌高,其成就和歷代西方漢學界所有學者所遺留的成果一樣,值得我等景仰與尊敬。
亂/雨層雲和積亂/雨雲
雲是水循環的一個環節。水吸收了太陽的能量,以蒸發、降水、滲透、蒸散、凝結、昇華等方式轉變存在模式,隨著不同的時間停留、滯留或被截留在所有能儲存蓄水的地方。就質量守恆而言,地球的水不增不減而只是交互變化形態。雲集水氣,可降雨以滋潤萬物,但雨量難以清楚捉摸,時間無法精準預測,更無法完全控制,雲於是潛藏了各種契機和危機。閲讀〈溪雲〉如同觀雲之變化,雖知雲中水氣澎湃,但自知有時亂雲密佈,間夾雷電冰雹,我無論如何細察秋毫,往往墮入烏雲深處,全然不知雲底或雲頂何在。我只能嘗試以皎然之心來和皎然交心相談〈溪雲〉,同時也容許他人一道參與,同入水裡雲中。
「舒卷」具有多義。雲之舒卷不僅是貼切合宜的描述,因為「舒卷」令人聯想到層雲(stratus)和卷雲(cirrus)及其諸多變化(卷層雲、卷積雲、高層雲、雨層雲、層積雲),「舒卷」還影射「展卷讀書」之意。觀雲於是成了讀書的暗喻,而「意無窮」就更具多重雋永之義了。「縈流復帶空」的「流」字或許展現一種「軛式」(zeugmatic)修飾,同時形容了「流水」與「流雲」,而「空」則悠悠的指向上句結尾的「窮」,使得「天空」和「蒼穹」獲得某種意義的張力或連繫,而「空」和「窮」又能藉叶音讓第一、二詩行共同保持虛空無盡無窮的涵義。
第三行的「有形」和第四行的「無跡」是明顯的對仗,但這個「仗」不僅不是文字的争執或戰爭(logomachia),反而是互相的依賴和仰仗;兩者的對照讓個別的涵義更為豐富。「形」和「物」相關,而「累」或許多方指涉積累、累贅、疲累等義;「跡」和「形」對比,但「無」和「去」讓其超越自身,而「隨風」一詞更讓詩行如行雲流水,反映詩僧皎然自由自在、隨遇而安的自然平和心境。風是富於禪意的意象,風動、幡動和心動的禪宗公案也讓皎然之心皎然可得。
「莫怪長相逐,飄然與我同」是/不是個命題或主張(proposition),我們或許不必強加追究,畢竟皎然不是位哲學家僧人。做為〈溪雲〉最未兩句詩行,其意/義總是非比尋常的。它流露了皎然之心,表達了皎然之意,但它似乎也朝向未來呼喚,彷彿詩人和詩(如同舞者和舞)一同召喚歷史中的知音與其相應相和。「莫怪」點出了皎然心境的皎潔磊落,「相逐」的「相」傳達了某種溪雲的「真相」以及它和詩人的「相互」關係:溪雲並非真實的天空之雲,如鏡花水月,如「寫在水上的名字」,溪雲是必要的假/相,因為人若真的執著於所謂的真,就像追逐那所謂真實的雲,執著反成了「累物」的行為,「隨風」自然也就淪為口號。因此,「相逐」是種「雙重的束縳或約束」(double bind),在互相追逐之時,詩人和溪雲也同時相互追(趕)/(驅)逐,讓兩方維持適當的距離。而兩者的共同/通點雖是「飄然」,然而這個「飄然」不是固著、穩定的結構,反而是不依不附,是如浮雲、浮萍、浮草一般,無論有根無根,無論有無地上或地下莖,隨著不同的際遇而展現變化萬千的生命歷程。I change but I cannot die。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翻雲:文學與跨文化翻譯的圖書 |
 |
翻雲:文學與跨文化翻譯 出版日期:2019-04-26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翻雲:文學與跨文化翻譯
翻譯理論是個龐大無比、無邊無界的無限雲系,至今雖有眾多學派,卻難以有人能窺得其全貌。《翻雲》由十三篇有關語言、文學與文化翻譯的專文組成,猶如十三朵飄盪其中的浮雲。各篇雖獨立、各有特色,但屬性相近且相互指涉,構成一幅充滿想像的翻譯天際。
然而,没有任何一套翻譯理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本書存在作者對翻譯理論(及實務)不斷翻動的嘗試、質疑和論證、批判,隱約透過解構的蛛絲馬跡解構深不可測的翻譯──甚至解構自身。
作者簡介:
張上冠
美國德州大學(奥斯汀)比較文學博士。1991年回國前,曾於美國柯蓋德大學、史密斯學院和羅倫斯大學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學。政治大學服務期間先後擔任華語文中心主任、翻譯中心主任和外語學院院長。現為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
作者序
自序
溪雲
唐僧皎然(730-799)撰有〈南池雜詠五首〉,其中〈溪雲〉一首自我初識以來,一直在心中盤旋縈繞,個別詩行三不五時幽幽浮現,而詩人彷彿古墳幽魂,也似謎樣精靈或神仙鬼魅,在迷濛夜色中飄然出現,雖然始終沈默不語,但其欲言又止之姿總是讓我一面默念其詩行,一面思索為何與我如此相遇:
舒卷意何窮
縈流復帶空
有形不累物
無跡去隨風
莫怪長相逐
飄然與我同
從年少時期起,對於雲我有一種氣質上的偏執:有雲之時,看雲、觀雲、望雲;無雲之時,想雲、念雲、盼雲。無論雲深雲淺,雲行雲止,各種雲的出現和變化讓習慣孤...
溪雲
唐僧皎然(730-799)撰有〈南池雜詠五首〉,其中〈溪雲〉一首自我初識以來,一直在心中盤旋縈繞,個別詩行三不五時幽幽浮現,而詩人彷彿古墳幽魂,也似謎樣精靈或神仙鬼魅,在迷濛夜色中飄然出現,雖然始終沈默不語,但其欲言又止之姿總是讓我一面默念其詩行,一面思索為何與我如此相遇:
舒卷意何窮
縈流復帶空
有形不累物
無跡去隨風
莫怪長相逐
飄然與我同
從年少時期起,對於雲我有一種氣質上的偏執:有雲之時,看雲、觀雲、望雲;無雲之時,想雲、念雲、盼雲。無論雲深雲淺,雲行雲止,各種雲的出現和變化讓習慣孤...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1
概要 9
Re(tro)spect:緬懷、翟理思(Herbert Giles)、〈桃花源記〉英譯 19
語言的神話和神話的語言:對ELF 的一個哲學反思 51
詮釋的轉折:偶遇陌生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67
匪夷所思:翻譯他者 85
裸眼:韋努第(Lawrence Venuti)的譯者之隱 95
隨遇:論作者與譯者的翻譯倫理關係 111
天賦──上帝的禮物:一個有關翻譯的聯想 127
荒誕:翻譯十誡 145
昇華:番異及/即翻譯 163
以利米勒:以米樂(J. Hillis Miller)為例再思文化翻譯與翻譯倫理 177
後知之明:全球化浪潮中本土翻譯理論...
概要 9
Re(tro)spect:緬懷、翟理思(Herbert Giles)、〈桃花源記〉英譯 19
語言的神話和神話的語言:對ELF 的一個哲學反思 51
詮釋的轉折:偶遇陌生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67
匪夷所思:翻譯他者 85
裸眼:韋努第(Lawrence Venuti)的譯者之隱 95
隨遇:論作者與譯者的翻譯倫理關係 111
天賦──上帝的禮物:一個有關翻譯的聯想 127
荒誕:翻譯十誡 145
昇華:番異及/即翻譯 163
以利米勒:以米樂(J. Hillis Miller)為例再思文化翻譯與翻譯倫理 177
後知之明:全球化浪潮中本土翻譯理論...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