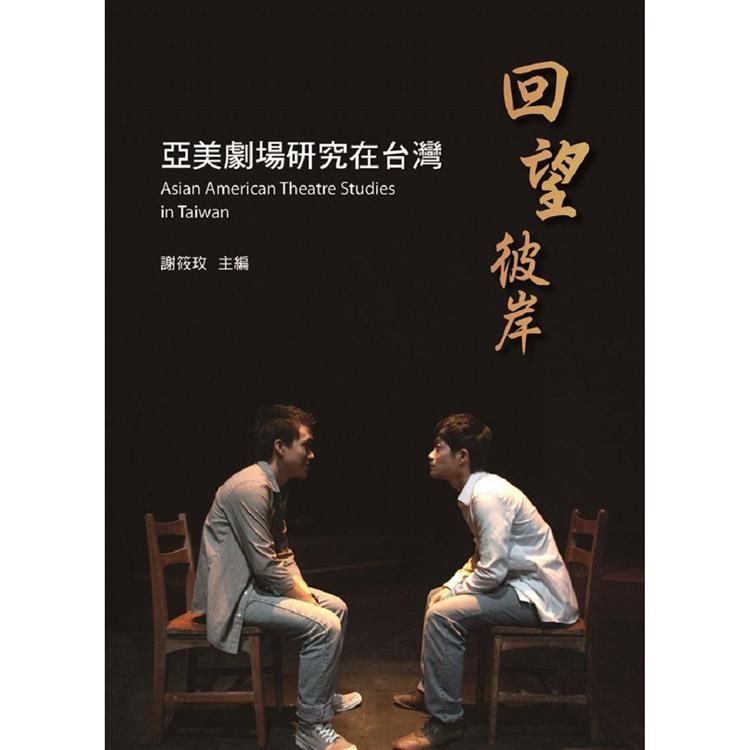導論—話說從頭
喬瑟芬‧李(Josephine Lee)在《展演亞裔美國》(Performing Asian America)一書序論中,曾援引Du Bois對黑人劇場的定義來談論少數族裔劇場:此種戲劇要1. 關於我們(about us);2. 由我們所創作(by us);3. 為我們而作(for us);4. 鄰近我們(near us)(8)。但「我們」又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例如,華裔移民的經驗是否能代表柬埔寨移民的經驗?她在九0年代撰寫該書時,也反覆提醒讀者其間的複雜與不可化約性。新世紀韓裔表演藝術工作者成績斐然,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其他族裔作家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且蓬勃。但九0年代以前,亞美劇場的主要劇作家仍以華裔與日裔為主,所謂的「亞美戲劇」,書寫的主要仍是華裔與日裔的美國經驗。
1965年成立於洛杉磯小東京區的「東西表演家」是美國本土第一個以亞裔為主體的劇團,成立初衷乃提供亞裔演員與導演恣意揮灑創意的平台。但是劇團成員很快就面臨窘境:沒有關於亞裔的劇本可以演出。於是劇團在1968年推動了為期三年的劇本競賽,亞裔前鋒劇作家代表趙健秀(Frank Chin, 1940-),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嶄露頭角,並陸續發表了影響後輩深遠的《雞籠華仔》(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與《龍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E. K. Lee, “Contemporary” 406)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亞美」(Asian American)這個詞彙,是在六0年代美國平權運動中乘勢而起。亞裔美國人作為一個族群,如凱倫‧島川(Karen Shimakawa)所言,因相似的歷史壓迫經驗、種族歧視經歷而相濡以沫,可謂回應在主流社會中被「國家賤斥」(national abjection)的集體經驗而生。也如李(Josephine Lee)在《展演亞裔美國》序論中反覆訴說的,並非因共同的文化或種族血緣而連結存在,而是相似的政治訴求所凝聚的集體意識。亞美劇場第二波代表作者五反田寬(Philip Kan Gotanda)回憶自己最初投身音樂與戲劇創作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民權運動潮流下亞美意識的萌生與勃發,與當時塑造「亞美性」的政治工程密不可分(Shimakawa 284),帶著一種非如此不可的使命感與迫切性。
「中國佬是被造出來的,而不是生出來的。」(Chinaman are made, not born.)趙健秀在《雞籠華仔》中抒發了身為美國華人被種種既定刻板印象所定義、歧視之苦。「東西表演家」成立之際,亞裔人口只占美國總人口數的0.5%,美國大眾對亞裔仍有許多誤解,其認識多來自於影視媒體所傳播的扭曲與刻板形象。趙健秀以文字書寫為武器,對外塑造陽剛的華裔男子形象,抵抗主流文化對亞裔形象的閹割去勢,對內則重砲批判成名亞裔作家為迎合白人所生產的東方刻板印象,致力於論述與捍衛亞裔內部文化書寫與再現族裔的「真實性」問題。他被李金(Esther Kim Lee)歸為第一波亞美劇作家。
同為第一波代表的日裔劇作家山內若子(Wakako Yamauchi, 1924-2018),則多書寫移民經驗,作品充滿濃厚的回憶色彩,取材自年少時身邊的人事物。她寫下經歷經濟大蕭條的童年、在加州帝王谷務農的父母,以及當時的見聞,也記錄二戰時期,青春少女時期的她身為日裔,因此被遣送到拘禁營生活的點滴。第一波劇作家沒有受過專業編劇訓練,其作品通常以情感的真摯質樸、對生活與人物的寫實描摹取勝。第二波劇作家則開始投身劇場正規訓練,多有藝術創作碩士文憑,較第一波創作者更正面樂觀,也具有挑戰主流劇場的野心。筆者在此同意李金在《亞美劇場史》(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 Theatre)中所強調的,使用「波」(wave)而非「代」(generation),蓋「代」一詞有年齡層的暗示,而「波」則可強調不同時期的美學風格與文藝政治訴求(125-26)。
第二波劇作家黃哲倫的《蝴蝶君》於1988年轟動百老匯,並得到該年度東尼獎最佳劇本的肯定。該劇嘲諷西方社會的東方主義迷思,中國男伶假扮女性,成為法國外交官的情婦長達二十年,藉此竊取情報。西方對東方的想像成了盲點,反過來被東方操弄、被狠狠擺了一道。另外,日裔作家五反田寬的《美國狗去死吧》(Yankee Dawg You Die),藉由兩位不同世代的男演員彼此的互動,幽默探討亞裔表演工作者如何在白人主導的演藝產業結構中爭取演出機會,並與行之有年的東方形象協商。除了族裔形象的主題,第二波亞裔作家仍受父祖輩的移民經驗影響,緬懷與訴說中國城、鐵路工人、二戰日裔拘禁營等故事,試圖重建被主流輕忽的歷史記憶。
前兩波劇作家皆意識到他們代表著某個族群,有一種身分自覺與責任感。他們想透過作品教育美國主流社會,透過作品表現「真實的」亞裔樣貌與生命經驗,探討種族歧視、東方主義、女性主義等問題。第一波的趙健秀、山內若子,第二波的黃哲倫、五反田寬等,不約而同地定義了「亞美戲劇」。
不同世代亞裔對身分認同有不同的態度與認知。前兩波亞裔作家皆試圖透過劇場進行社會改革與表達政治訴求,如早期的趙健秀或第二代的黃哲倫,不論是激動怒喊,或四兩撥千金地輕鬆諧擬,作品都透露著族裔意識與使命感。相較於此,九0年代以後興起的第三波劇場工作者則儼然跳脫出糾纏前輩作家的族裔緊箍咒,他們開始訴說個人的故事,其亞裔身分似乎只是碰巧構成個人經驗的一部分,例如在華裔導演作家謝耀(Chay Yew)的《我們的語言》(A Language of Our Own,1997年)中,同志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族裔問題交織,甚至更為迫切。第三波韓裔劇作家戴安娜‧孫道出了這層差異,她認為前幾代的亞裔作家念茲在茲的是爭取能見度,作品往往是一種宣言:「我們在這裡!」(We are here!),亟需受到正視與理解。但是她們這一代亞裔劇作家更想講的是:「我們很搞怪!」(We are weird!)(E. K. Lee, A History 200),強調內容與美學上的離經叛道,具有不願被拘束的開闊氣象。
以戴安娜‧孫2006年的作品《衛星》(Satellites)為例,妮娜一家搬進了布魯克林區的一座大房子,房子還在裝潢整修,隱喻混亂失序,一切正在重建。劇中,族裔血統、性別角色、社會經濟的界線模糊。強勢的建築師妮娜(韓裔)與網路工程師邁爾斯(非裔)是新手父母,手忙腳亂地適應新生兒所帶來的生活轉變,夫妻關係緊繃。邁爾斯那好高騖遠的白人哥哥來訪,更使家裡氣氛一觸即發。邁爾斯自小被白人家庭收養,女兒是亞非混血,女兒要如何認同祖父母的家族,令他深感困擾。劇末,妮娜說「那首他們一直想不起歌詞的搖籃曲,我們可以自己來編歌詞」。作者似乎藉此暗示他們可以為新生兒創造新的未來,無須侷限於過去的包袱。劇中跨族裔收養、混血後代等現象,點出以族裔作為認同標籤的可穿透性。不免又讓我們回到關於「亞美」一詞的定義:「我們」究竟是誰?
華裔移民第四代的余秀菊(Lauren Yee)於2007年創作的狂想喜劇《清窮華仔》(Ching Chong Chinaman),描述完全被白人同化的王家四口。他們不會說華語、不會拿筷子,弟弟阿頓因為想專心打電玩,從美國早期自中國引進廉價勞工興築鐵路一事獲得靈感,雇了來自中國的非法移工幫他寫作業。姐姐黛絲為了能進入長春藤名校,調查祖先背景,卻意外發現自己與弟弟並非父母親生,是父母從韓國領養回來的。此劇除了質疑以血緣為本質的認同,也觸及了跨國與階級的剝削。當亞裔晉身上流位階,也開始複製資本主義的剝削模式,階級問題似乎取代了種族問題。
何為「亞裔戲劇」?這個問題恐怕會愈來愈難以回答,尤其多重混血後代的增加,將使其定義愈益複雜。事實上,亞裔的認同已進入全球化的互動網絡中,亞裔劇作的市場也已不限於北美洲。例如韓裔劇作家盧盛的戲除了在紐約外百老匯上演之外,也在韓國首爾、英國倫敦演出。黃哲倫的《中式英文》(Chinglish, 2011)除了在芝加哥、洛杉磯、紐約等地上演,也到新加坡、香港等地演出。誠如阿帕度萊(Appadurai)在《消失的現代性》(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人們頻繁移動,加上電子媒體和傳播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可以輕易與遠方的人事保持連結(包括通訊、觀看韓劇與日本動畫等),影響人們的想像與認同形塑,造就了有別於國族意識的新的想像共同體。
第三波以後的亞美劇作家在大眾文化、前衛表演、電子媒體、全球化效應之間汲取靈感與素材。越南裔劇作家阮魁(Qui Nguyen)形容他們成立於紐約的吸血鬼牛仔(Vampire Cowboys)劇團為「宅男劇場」,其作品頗受紐約動漫迷喜好與支持(E. K. Lee, “Contemporary” 418)。他的作品常用電玩、武打、動漫、殭屍等元素,近年亦開始為迪士尼旗下的漫威工作室創作。同時,廣受矚目並獲外百老匯獎項肯定的韓裔導演作者李永珍在紐約成立了以自己為名的劇團,從事顛覆與前衛的藝術探索。她的作品除了《飛龍在天之歌》(Songs of the Dragons Flying to Heaven, 2006)外,其他作品與亞裔身分議題幾乎無關。戴安娜‧孫的《停止親吻》寫兩名慢慢確認彼此情感的女同志在紐約街上的第一次接吻,卻遭到恐同的路人攻擊而受傷送院。她曾表示任何族裔的女演員都可以演出這個劇本,她有時在自己作品中特別標註族裔,也只是出於讓亞裔演員有多一點曝光機會的考量。
新世紀亞美作家在內容上並不侷限於族裔政治,性別認同有時可能比族裔認同更為直接迫切;菁英式世界主義的跨國移動與跨國移工的被剝削經驗往往同時並存。長江後浪推前浪,前兩波作家關注、甚至爭論的亞裔真實性問題,已非新世代關懷的重點。新世代作家的作品呈現較多關於本質的質疑與思考,如李(Josephine Lee)在《新世代亞美劇作選集》(2011)引言中所點出的,新一波劇作中的人物「在不同的角色之間游移,他們不單只是受迫害的底層、激進行動派、受害者、加害者、女性主義者、未出櫃的沙文主義者,可能同時包含這些身分,甚至更多」(9)。誠如她觀察到的,亞洲與美國兩者的連結具有多面向,「無法再將之視為亞洲往美國的單程票,或者單向的同化程度。應該說是來自不同地域的多重旅程」(7)。
由此看來,新世紀的亞美劇作家反本質主義,抗拒被貼上族裔標籤,身分認同更形多元開放,不僅限於血緣、出生地或成長地。人們可以跨國定義自我,如此,邊界是否已不重要?族裔藩籬是否已然消弭?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台灣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回望彼岸:亞美劇場研究在台灣
伴隨著六0年代的美國族裔運動,「亞美劇場」成為凝聚、集結北美亞裔表演藝術家,以及他們訴求改變社會、爭取能見度的場域,一路走來,成果豐碩。新世紀北美亞裔劇場蓬勃發展,更形多元開闊,但其作品始終保持身為邊緣少數的抵抗姿態與自覺。這個非既得利益者的身分位置,讓亞裔創作者可以更同理弱勢、更有政治敏感度,時不時仍會從邊緣的位置批判思考,跳出來質疑之、挑釁之。這種帶點刺的鋒芒,正是亞美劇場引人入勝之處。
本論文集收錄十一篇亞美戲劇相關論著,且均為2000年以後發表的作品,希望能將近期的亞美劇場研究風景呈現於華語讀者面前。另外,也希望藉著論文集的出版,將更多優秀的亞裔劇作家與戲劇作品介紹給台灣劇場界,使其進一步思考搬演的可能。
本書特色
1. 台灣第一本亞美劇場研究專書。
2. 適合劇場相關領域教師、學生,以及一般大眾閱讀
作者簡介:
謝筱玫
美國西北大學表演研究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開授課程如「西洋戲劇名著選讀」、「體演文學」、「戲劇裡的性別與愛情」、「當代劇場藝術面面觀」、「亞美劇場」、「跨文化表演專題」、「後殖民文學與戲劇」等。長期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兩廳院、臺北市文化局等單位的評議審查委員,並曾為表演藝術評論台駐站評論,現為特約評論,撰有劇評數十篇。研究興趣包括:當代臺灣劇場、亞裔戲劇、後殖民劇場。中英論文近二十篇散見國內外期刊,如《戲劇研究》、《中外文學》、《清華學報》、Asian Theatre Journal等
作者序
導論—話說從頭
喬瑟芬‧李(Josephine Lee)在《展演亞裔美國》(Performing Asian America)一書序論中,曾援引Du Bois對黑人劇場的定義來談論少數族裔劇場:此種戲劇要1. 關於我們(about us);2. 由我們所創作(by us);3. 為我們而作(for us);4. 鄰近我們(near us)(8)。但「我們」又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例如,華裔移民的經驗是否能代表柬埔寨移民的經驗?她在九0年代撰寫該書時,也反覆提醒讀者其間的複雜與不可化約性。新世紀韓裔表演藝術工作者成績斐然,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其他族裔作家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且蓬勃。但九0...
喬瑟芬‧李(Josephine Lee)在《展演亞裔美國》(Performing Asian America)一書序論中,曾援引Du Bois對黑人劇場的定義來談論少數族裔劇場:此種戲劇要1. 關於我們(about us);2. 由我們所創作(by us);3. 為我們而作(for us);4. 鄰近我們(near us)(8)。但「我們」又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例如,華裔移民的經驗是否能代表柬埔寨移民的經驗?她在九0年代撰寫該書時,也反覆提醒讀者其間的複雜與不可化約性。新世紀韓裔表演藝術工作者成績斐然,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其他族裔作家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且蓬勃。但九0...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論:何為亞美劇場?關於亞美戲劇的再商榷
謝筱玫
PART I 身分認同
展演對立:二十世紀末的亞美劇場
雷碧瑋
從《雞籠華仔》到《清窮華仔》:新世紀亞美劇作中的認同政治
徐紫芸、洪聖翔
英語、華語、「同」言、不同語:謝耀劇作《他們的語言》中的少數族群語言
王寶祥
PART II 刻板印象
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宗教與文化身分:趙健秀與黃哲倫書寫中的關公形象
張金櫻
這是誰的黃面孔?析論黃哲倫《枷鎖》與《黃面孔》的刻板形象操演
張靄珠
亞裔男性演員在美國:五反田寬的《美國狗去死吧》
謝筱玫
PART III 跨...
謝筱玫
PART I 身分認同
展演對立:二十世紀末的亞美劇場
雷碧瑋
從《雞籠華仔》到《清窮華仔》:新世紀亞美劇作中的認同政治
徐紫芸、洪聖翔
英語、華語、「同」言、不同語:謝耀劇作《他們的語言》中的少數族群語言
王寶祥
PART II 刻板印象
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宗教與文化身分:趙健秀與黃哲倫書寫中的關公形象
張金櫻
這是誰的黃面孔?析論黃哲倫《枷鎖》與《黃面孔》的刻板形象操演
張靄珠
亞裔男性演員在美國:五反田寬的《美國狗去死吧》
謝筱玫
PART III 跨...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