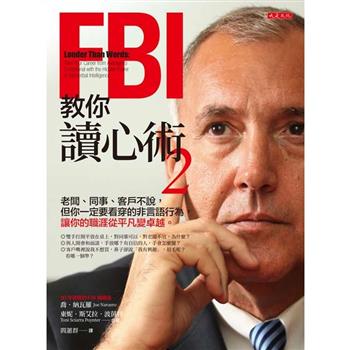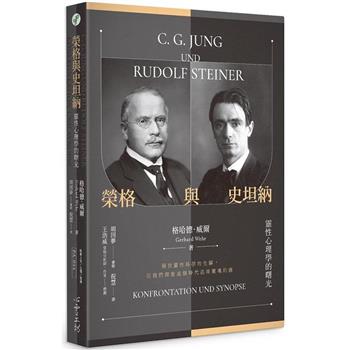我們渾身是刺,而這些刺都是從年幼傷口中長出的。
沒有人願意脫軌,當我們被體制踢出常軌時,我們必須在失序的世界中,一步步找回自我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
當一個人什麼都不是的時候,追求的目標只能是錢。
有時他們那股不尋常的熱血,不免讓懷疑他們是不是吃槍藥長大的。
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們叫痞子,現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們都在考慮今後的出路。有時我常想,為什麼我們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學、結婚、找工作呢?想來想去,才發現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們的腦子都震出了問題……
貧窮的胡同裡,張東在這群孩子裡算聰明,他的成績維持在前三名,如果認真一點,或許可以上大學。只是,他不能接受老師對他們出生南城胡同小孩的輕視,看不慣升學主義制度下的政策,為了爭氣,他選擇「脫軌」。
他們歷經挫折,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張東一再碰壁,在冒險的生涯中成為商業社會的弄潮兒,但也在奮鬥中的波折遇到了之前老師口中所謂的「好學生」,這「三好生」(模範生)兼初戀情人身為醫生,卻因為利益而間接害死了好友……
【本書獨特】
※本書已準備改編為電視劇。
※《北京爺們兒》為庸人的代表作。
※百度百科另稱之為「邪派高手」,寫作獨樹一格。
※貼近瞭解大陸底層人民的通俗小說,熱血的青春故事。
作者簡介:
庸人
原名劉軍,北京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被讀者、媒體、作家、評論家隊伍裏的擁躉譽為「六〇後文字高手」。庸人學的是經濟管理,曾先後從事過業務員、飯店老闆、超市老闆、廣告公司策劃總監。2000年開始文學創作,現為職業作家。
著有《北京爺們兒》、《中國丁克》、《痞爺》、《射雕時代》、《電視》、《我不是人》等長篇小說20部,紀實文學3部,《歡天喜地七仙女》、《幸福來了你就喊》、《鐵爺茶館》等劇本若干,共有近六百萬字的作品問世,圖書銷售超過百萬冊,多部作品已投拍電視劇。
多次接受北京電視臺、深圳電視臺,北京電臺、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中國圖書報、信報等多家媒體採訪。在搜狐、新浪、騰訊等網站有專集。其濃重的生活氣息和幽默風格是作品得以流傳的原因,擅長長篇市井題材小說的創作,小說多以社會的最新視角而創作,題材出奇。
章節試閱
【引 子】
去廣州
最後一次去廣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們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經很冷了,可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脫衣服,到廣州時只剩下一件襯衫了。
實際上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我永遠無法將那次旅行從記憶中抹去,無論是好是壞。
去廣州的路上,我們的心情不僅忐忑不安,而且是極度的惶恐,路上跟熬鷹似的,眼睛都藍了。整整兩天的行程我都抱著那個皮包不撒手,唯恐一不留神它就會長翅膀飛了。山林的手則時刻不離開腋下的刀把,在他眼裡從我們身邊走過的每一位乘客臉上都掛賊像,只有狼騷兒的叔叔溜達過來時,他臉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樣。
那把美國軍刀在山林腰裡已經掛了五、六年,從不離身,連睡覺的時候都不願意摘下來,這也是山林死時身上唯一完整的物件。最後我將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墳裡,不久那片地被國家徵用了,轉移山林的骨灰盒時再也沒找到那把刀。據說兇器都不吉利,名劍的主人很難有善終,操魚腸劍成名的專諸被剁為肉泥,揮元戎劍策劃十面埋伏的韓信被一群騷娘們亂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終連全屍都沒落下。
其實那把刀本來就是山林搶來的,它的前任主人連刀都沒拔出來就給弄了個半死。
那是初一寒假前發生的事。那時我還是個老實孩子,從沒在外面打過架,大頭正領導著他的「武工隊」橫行南城。
80年代初龍潭湖附近修了個旱冰場(溜冰場)。當時的娛樂設施少,年輕人的剩餘精力無處發洩,不久旱冰場就成了最時髦的場所,常常人滿為患,有時候連冰鞋都租不到。我們這樣大的孩子,口袋裡有點兒錢就往那兒跑,實際上旱冰場是現代社會在我們面前開啟的第一條縫隙。在那兒我們第一次領略了風馳電掣的感覺。
由於到旱冰場玩兒的社會青年特別多,所以這裡也是最容易打架鬥狠的地方,學校和家長從來都是禁止我們去的。難怪大人們不放心,離旱冰場很遠就可以聽見瘋狂滾轉的塑膠軲轆(輪子)與地面摩擦出的「嘩嘩」聲,那聲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煩意亂,幾乎每幾天都有人被抬著出來。旱冰場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點盯防單位,可能是太影響治安管理了,沒幾年旱冰場就給拆了,連一片水泥台都沒留下。
滑旱冰的消費並不高,三毛錢滑一場,可每禮拜我們只能去一次,因為大家都是窮光蛋。我們在旱冰場玩過幾年,從沒人在旱冰場欺負過我們,大頭是那兒的場霸。那時大頭他們最喜歡玩兒的遊戲是幾個人排成一串兒,肆無忌憚地在旱冰場裡穿來穿去,他們的技術片兒湯得很,人串兒中的最後一個常常被甩出去。
誰在附近誰倒楣,經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幾年裡他們一直這樣,從沒人敢把鞋脫下來砸他們,倒是他們動不動就掄鞋打人。他們另一個愛好是五、六個人手把手圈成大半個圓,滿場轉悠,往往一圈兒下來隊伍裡就多了個姑娘。頭兩年旱冰場還有些正經人來鍛鍊身體,後來連到旱冰場玩兒的女孩都叼著菸捲了。
龍潭湖南面是一片很密的松樹林,面積相當大,一直到護城河。每到傍晚,灰黃色的陽光疏懶地在樹梢間遊走著,空氣裡彌漫著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樹林是我們的根據地,沒事兒我們就在樹林裡拍婆子(男孩勾搭不相識的女孩),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時連課都懶得上。讓人難以想像的是,有一次我們這些地頭蛇在樹林裡差點讓人家洗嘍。
那天風特大,下午天就颳黃了。我們在旱冰場折騰了兩個鐘頭,出來時天色有些晚了,我們累得兩腿發軟,嗓子眼裡都是黃沙。那次是累壞了,我們稀稀拉拉地在樹林裡穿行著,相隔有好幾十公尺,誰都懶得說話。
我和二頭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公尺後跟著,樹林裡的風像吹哨一樣,一陣陣的颳得臉生疼。這時樹林裡突然出現了三個膀大腰圓的小夥子,他們像地裡鑽出來似的,徑直向我們走來。幾個傢伙邊走邊四下張望,來到近前,個子最高的當中站定,另外兩個人分立旁邊,一個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頭圈在中間。
「嘿,哥們兒,挺自在的?」中間那個大大剌剌地說道,他穿著件的確良(時髦)襯衫,裡面的跨欄背心捲到胸口,碗大的肚臍眼兒像個黑窟窿。他應該比我們大幾歲,嘴唇上新長出的一層黑絨毛特別茁壯。「有錢嗎?弄點兒花。」
我和二頭對望一眼,那時我還算老實,碰上這種事竟感到自己的腿肚子直哆嗦。二頭倒很沉著,他使勁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點兒錢還不容易,可你們是哪條道兒上的?」
劫道者呵呵笑了兩聲,他把手抬到自己耳邊,手指頭向下點著我們:「呦呵,還碰上岔子啦。」說完,劫道者兩腿稍息,雙手扠腰,故意把腰帶上的一把軍刀露了出來。
我一下就被那把刀吸引住了,刀把上纏了不少黑膠布,霸道地在腰帶上翹著。刀座上泛著藍油油的光,那光芒詭異而透著股殺氣,暗黃色的皮套已經磨光了,在皮套上都能看出深溝一樣的血槽來。
「認識大頭嗎?」二頭開始和佩刀者盤道了。
佩刀者搖搖頭。
「那你知道大竿兒跟我什麼關係嗎?」
我瞥眼向後望去,原來一直跟在後面的山林已經不見了。
「廢你媽什麼話?小崽兒也敢叫板(不服挑戰)?老老實實把錢掏出來,要不,大爺楔死你!」佩刀者已經急了,他朝另外兩個一揮手,三個人立時陰著臉圍上來,我甚至能聽見手上骨節活動的「啪啪」聲。
「我說,我說。」二頭突然抱著頭喊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不就是錢嗎?你們等著。」說著,二頭一把拉住我的手,我們倆同時蹲下了。
這時一塊半頭磚「呼」地從斜側裡飛過來,「咚」的一聲,像石頭砸在磚牆上,磚頭正好打在佩刀者後腦勺上,佩刀者連白眼都沒來得及翻就像個麵袋似的「砰」的一聲趴在地上了。另一塊磚頭緊跟著飛過來,平拍在另一個傢伙臉上,他號叫著轉身便跑。還有個沒被打中的眼看勢頭不對,假裝向我們踢了一腳,趁我們閃身躲避時一下子從我身邊竄了過去。
二頭反應特快,他縱身飛起一腳,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後背上,那傢伙連跑帶爬,手腳並用地衝出去十幾公尺,嘴裡還喊著:「你們等著,有種你們等著。」沒喊幾聲他就沒影了。這時,山林舉著兩塊磚頭從旁邊的樹林裡衝出來,朝佩刀者的臉上又是一下,此時佩刀者身下已經紅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雜草都嚇得支棱(挺立)起來。
山林的刀就是從那傢伙身上摘來的,刀背上帶鋸齒,跟藍波的軍刀一模一樣。此後這把刀一直沒離開他。山林將它視為至寶,不到危機時刻從不拔出來,可一拔出來就有人要倒楣了。
女人突然悶聲吼起來:「李二頭,你給我出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們家我都去過了。打了人有種別跑哇,整個一個三青子……」
這時在廚房做飯的父親推門走進來:「你們倆惹事了吧?」
二頭趕緊說:「沒東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親無奈地看了二頭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槍藥長大的?這趟街就數你能折騰,三天兩頭地給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條路哇?」
二頭盯著自己的腳不說話。
中年女人在街口罵得更厲害了:「李二頭你個有人生沒人養的東西!老老實實出來,還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來,我罵你八輩兒祖宗……」
父親拽住二頭的脖子:「走吧?真等人家來揪你呀?」
二頭看看我:「別忘了給小歡子餵食。」小歡子是他養的一條板凳狗,好幾次打狗隊來都倖免於難,大人們都說這條狗上輩子肯定是大官。
父親噗哧一聲笑了:「走吧,還以為你能當烈士呢!」
二頭像隻被拔掉鉗子的螃蟹,他躲在父親後面,還不時地看看我。不知怎麼,我當時竟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經微微有些顫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褲腿兒,使勁撚,手指都撚熱了,好像不這樣就得找個東西打幾下。
我們走出胡同口,就見狼騷兒正被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拉著領子,女人後面有個獐頭鼠目的孩子,腦袋上包了塊白布,似乎剛哭過,臉上是一道兒一道兒的黑印兒。狼騷兒灰頭土臉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裡哼哼唧唧地說:「我真不認識他們家是哪個門,這不是二頭的家。」那女人突然扯著嗓子又喊起來:「李二頭,你個小噶畚兒的,有種打人,沒種出來,是你媽養的你就給我出來!」
「行啦,大姊,歇會兒,歇會兒。」父親笑呵呵地走過去:「哪兒那麼大火氣,也不怕傷了身子。」
女人立時不說話了,她瞪圓眼睛,眼珠車轂轆似的打量起父親來,也許是父親還算長得氣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後來她看見了我和二頭,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頭,她指著二頭道:「這就是李二頭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個好東西。」她轉過臉問父親:「他跟您什麼關係?」
「他是我侄子。怎麼啦?兩個孩子掐起來啦?」父親拉過被打的孩子,掰著腦袋看了一陣兒:「還疼不疼?多大口子?」父親順手拍了幾下他的肩膀,回頭瞪著二頭道:「二頭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沒輕沒重,你看看,還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頭跟木樁子似的站在那兒,他眼睛惡狠狠地瞪著地面。
「瞧他一臉橫肉的,長大了也不是個好東西。」女人咬牙切齒地說:「我們家孩子多老實,你憑什麼欺負他?把我們孩子打成這樣,你還有點兒人心沒有?」她越說越激動,身子竟向二頭靠了過去。
父親趕緊過去用身體擋住了女人的去路:「不過是小孩兒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護犢子了嗎?」說著,他凶巴巴地對二頭發起了狠:「怎麼回事?你怎麼動手打人哪?人家怎麼招你啦?」
二頭愣瞌瞌地一手指著狼騷兒,一手指著挨打的小子:「他欺負他。」
父親故作鄭重地問狼騷兒:「是嗎?二頭是不是說瞎話?」
狼騷兒回頭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廁所裡撒尿,他說我跟他犯照(挑釁的對視)來著,要打我……」
「胡說!」中年婦女橫著蹦了起來,腰上的肉呼呼直顫,她誇張地掄著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們這麼說我們家孩子成流氓了,我們挨了打倒成活該啦……」
此時胡同口已經聚集了幾個看熱鬧的鄰居,大家說什麼的都有,有兩個起哄駕秧子竟說二頭打得輕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潑了,父親趕緊上去勸住她:「大姊、大姊,別跟小孩子一般見識。」他回手給了二頭後腦勺一巴掌:「狼騷兒還沒動手,你拔什麼橫?就你能格兒。」然後他從口袋掏出十塊錢,塞給中年女人。「行了,您別跟孩子一般見識,這是醫藥費。您放心,待會兒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這臭小子一頓不可!」
女人看見這張大團結,臉色立刻緩和下來。「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術員,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們特重視孩子的教育。現在的學校裡什麼人都有……」
父親趕緊笑著說:「是、是,您的孩子以後能當工程師。」
女人聽了這話臉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擠眉弄眼道:「今天是沖您,要不我非給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裡的孩子就沒好樣的!」
此言一出,還沒等父親說話,看熱鬧的鄰居先罵了起來。
「嘿,你說什麼哪?找死啊?」
「胡同裡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別從這兒走。」
「就她爺們兒,我認識,一身鹹帶魚味兒,還技術員呢!」
「弄個橛子(短木樁)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兒堵上!」
「你們家不就住四樓上嗎?磚頭能砍上去……」
後來幾個年輕人居然嚷嚷著要把女人的舌頭剌下來。
女人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她下意識地往父親身後躲。父親臉色也不太好看,他鐵青著面孔對女人說:「二頭的叔叔在青海揹鹽呢,他要是聽見您這句話非把您的寶貝兒子騸了不可。您的兒子比二頭大一屆都挨打了,以後他要是天天挨打我可管不了,您還想不想讓他上學了?」
女人被嚇得直喘粗氣,她幾乎是驚恐地抱住自己的兒子,此時她兒子腦袋上那塊白布已經向外殷血了。
◎我們的小學◎
小學生活沒給我們留下任何好的印象,有時想起來,如果不是那幫小學老師太過勢利眼的話,也許我成不了痞子。但時事難料,也許我成不了痞子當流氓也說不定呢。
我們的小學離家也就是幾百公尺,那是一座普通的三層樓,50年代蓋的,據說那時的水泥品質好,水泥地板總是黑亮黑亮的,光線好的時候能當鏡子用。以當時的標準來看,學校的設施、環境還是不錯的。只是小學的生源(學生來源)比較複雜,家長社會地位的懸殊巨大。物以類聚,獸以群分,學生們愛紮堆兒(聚集在一起),不算大的學校裡儼然存在著幾個小幫派。我們當時歲數都小,鬧不出什麼大事,頂多是課間休息時相互撞幾下,幾年中倒也相安無事。
學校的生源主要分成三大塊兒,胡同排子房的、附近樓群的,還有一群學生是軍隊大院的。樓群孩子的生活條件相對好些,但他們終歸是地方雜牌軍,不在組織,平時也比較分散,對我們沒什麼威脅。軍隊大院可不一樣,他們人多勢眾,裝備還特別好,這群孩子是我們的死對頭。
北京的軍隊大院大多在西北部,偏偏我家附近也有個軍隊大院。大院門口有哨兵站崗,一副戒備森嚴的樣子,我二十歲之前就從沒進去過。軍隊大院的孩子最牛,他們穿的軍裝都是四個兜的,老媽攢一個月錢為我買了個軍挎包,他們硬說顏色不正是廢品,我回家跟老媽吵了一架,老媽氣得兩天沒吃下飯去。這群孩子是天生的群居動物,走起路來總怕掉隊,而且保證是一臂間隔。他們覺著自己高人一等,我們平時更是懶得跟他們來往。
我們四、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導師)是個女的,姓劉,因為個子矮得不像樣子,四肢像縮在身體裡似的,伸不出來,狼騷兒便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小個劉。聽說小個劉是軍隊大院裡某個營級幹部的老婆,這女人平時的樣兒可大了去了,眼睛只看房頂,脖子上一道道的青筋總是立著的。
小個劉長得差勁倒也罷了,這女人會變臉,而且技藝高超。上課提問的時候對軍隊大院的孩子總是百般呵護,一道題她能掰開揉碎了講上好幾遍。可要是換了我們,保證是橫眉冷對,一言不發,此時教室裡的寧靜簡直讓人覺得恐怖。
那回放學時她把山林留下了:「你的作業是怎麼回事?誰給你寫的?」說著小個劉將作業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顴骨上立刻紅了。山林正要說話,此時一個男同學走過來:「劉老師我走啦。」小個劉整張臉都紅了,她笑得面若桃花,呵呵直喘:「回家問許參謀好,路上慢著點。」
小個劉太招人恨,平時我們沒少扎她的自行車胎。大家都盼著她能住幾回院,可這女人的身體出奇的好,有一次下雪她摔了個半死,可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擻來上課了。不過那回開家長會,小個劉的人可丟大了,這事多虧了狼騷兒他爸。
那次的家長會是五年級第一學期期中考試的總結,全班同學都站在後排罰站,家長坐在我們的位置上。其實要說也難怪小個劉生氣,班裡成績表的後五位全是胡同裡的孩子。小個劉越嘮叨火氣越大,最後她突然蹦出一句:「胡同裡的孩子就是沒好樣的,升學率都讓他們帶下去了……」
這句話就像扔進茅坑的磚頭,教室裡「嗡」的一聲就炸了。要知道屋裡至少坐了一半胡同裡來的家長,狼騷兒的父親第一個跳了出來。他有三件看家本領——燒鍋爐、喝酒、侃大山(長時間沒完沒了地說一些瑣碎、不恰當的話),不喝酒時是胡同裡第一大貧蛋,鄰居們都管他叫哨爺。
「劉老師,您是姓劉吧?」他挺費勁地從學生桌裡鑽出來,一直走到講臺前。「您是姓劉吧?是不是劉鄧陶的劉?」他居高臨下地看著小個劉,講臺上像是一對相聲演員在進行表演。
小個劉點點頭,她已經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
「您什麼出身?」狼騷兒爸爸瞇著眼睛看她,看得小個劉直扭屁股。
「我們家貧農。」小個劉說這話時底氣很沖,那時成分論的遺毒還很重,動不動就會有人站出來說自己是貧農,應該如何如何。
「貧農出身怎麼當老師了?」
「我考的師範。」
「那你們家以前住哪兒?」
小個劉張著嘴,她連眨了幾下眼:「這位家長請您回到座位上去,我們在開家長會。」
「咱今天得把話說清楚,人民群眾的優秀子弟到了您們學校給教成這個樣子,咱得挖挖思想上的根源,看看錯到底在哪兒?對不對?」
下面立刻有幾位家長大聲應和著:「對!得刨刨根兒。」有個人居然小聲嘟囔著:「上樑不正下樑歪,壞老師能教出好學生?」
狼騷兒的爸爸一臉得意,他接著問:「貧農怎麼住大院裡去了?」
「我愛人是營級幹部。」小個劉的臉色很難看。
「你愛人是軍人,是人民的兒子,那我們是誰?」狼騷兒爸爸看著下面的家長:「我們是誰呀?」
「我們是人民。」胡同裡的家長跟著起鬨道,那時我們在後面的已經笑得不成樣子了,二頭更是擠眉弄眼、洋相百出。
狼騷兒爸爸手指著小個劉:「您看看,您看看,胡同裡的人民是最基本的群眾,是無產階級,是革命的,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的孩子怎麼到了您的手裡就成膿包了?我估計您父親住的地兒還不如胡同吧?您說胡同裡孩子沒好樣的,這麼說您和你爹就更不是好人了,對不對?再說胡同裡真沒好樣的?那東子怎麼考了個第三吶?他不是胡同裡長大的?」他抬手指著我,那次我的確考了個第三。
小個劉一個勁嚥唾沫,她的手指死命地摳住講臺。可事到如此她還是不甘心認錯,眼珠拚命往窗外翻。
哨爺本來想說幾句就算,可人家沒給他臺階下,於是越說越惱:「您還不服氣是不是?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墮。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是希望他們能學好,可現在的老師素質太低,人民拿錢養活著你們,人民拿錢養活著軍隊,可你們說什麼胡同裡的沒好樣的。這是什麼階級觀?黨是怎麼教育你們的?胡同裡沒好樣的你們吃誰喝誰哪?天上能掉下糧食還是能掉下來鋼鐵呀?我看你們這些老師首先得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幹部掉過來念是『不幹』,你們思想成問題了你們,校長呢?把你們校長叫來……」
那天小個劉是哭著跑出教室的,第二天,另一個老師來到教室,他成了我們新的班主任。新班主任的第一件事是率先走到狼騷兒的桌子前:「以後再開家長會,讓你媽來就行了。」說著他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
家長會雖然罷了小個劉的官,卻並不能改變胡同學生在老師們眼中的地位,大院同學的優越感一點沒減弱,他們依然是老師們的寵兒,三好學生一直是他們的專利。可能是看他們在老師面前屁顛兒屁顛兒的樣子生氣,二頭、山林背地裡拿搶他們的軍帽當成了樂子,可他們的軍帽像搶不完似的,總搶總有。我則較著勁地學習,一心想在成績上壓過他們。
【引 子】
去廣州
最後一次去廣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們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經很冷了,可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脫衣服,到廣州時只剩下一件襯衫了。
實際上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我永遠無法將那次旅行從記憶中抹去,無論是好是壞。
去廣州的路上,我們的心情不僅忐忑不安,而且是極度的惶恐,路上跟熬鷹似的,眼睛都藍了。整整兩天的行程我都抱著那個皮包不撒手,唯恐一不留神它就會長翅膀飛了。山林的手則時刻不離開腋下的刀把,在他眼裡從我們身邊走過的每一位乘客臉上都掛賊像,只有狼騷兒的叔叔溜達過來時,他臉上才...
目錄
【目 錄】
引子 去廣州
第一部 胡同人家
第二部 歃血為盟
第三部 作鳥獸散
第四部 南下之路
第五部 南方之南
第六部 發跡的結果
【目 錄】
引子 去廣州
第一部 胡同人家
第二部 歃血為盟
第三部 作鳥獸散
第四部 南下之路
第五部 南方之南
第六部 發跡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