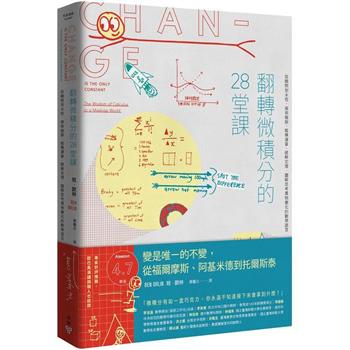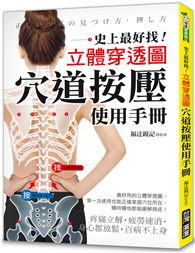★艾琳古威爾
艾琳古威爾在她第一年擔任高中教師時,進入南加州一個種族隔離的社區,發現她被分派到一個人稱「無可救藥」的班級,沒有人認為這班的學生有學習或成功的可能。
這位堅強的老師決心證明教育系統的錯誤,她發展出創新的課程──透過文學與寫作來教導學生寬容。她讓學生們記錄自己面對貧窮與歧視的掙扎,並自稱為「為自由寫作者」,以向民權時期對抗種族隔離的「為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s。編註:1961年起為抗議美國南方仍有種族隔離陋習,發起的黑白人種共乘巴士的活動,許多參與者在抵達保守的南方後被捕或被攻擊受傷,其中一位成員約翰路易士的故事在本書的第x頁)致敬。
課程的成功有目共睹,不僅這些「無可救藥」的學生都從高中順利畢業了,他們之中許多人現在還任教於國內環境最困難的幾間學校。
艾琳古威爾相信美國沒有所謂「無可救藥」的學生。透過提供獎學金、教師培訓與其他由艾琳古威爾基金會贊助的課程,這位老師盡一切力量讓身處險境的貧困孩童能有機會得到應得的教育。
★艾琳古威爾的英雄──梅普吉斯(協助安妮法蘭克一家躲避納粹追捕的女子)
當我首次讀到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安妮的日記》(Diary of a Young Girl編註:一名叫安妮的猶太女孩,全家在納粹追捕猶太人時藏身於閣樓,安妮在這段期間寫下的日記,在她過世後被出版,是最知名的集中營文學)時,得知我住在郊區的家裡,有著修剪整齊的草坪,社區還有隔絕外界的圍牆。這本書讓我大開眼界。
在那之前,我以為英雄都是騎著白馬,而好人永遠會贏得勝利。但在這本書卻沒有快樂的結局,反之年輕的英雄最後還死在集中營。
對於導致安妮法蘭克死亡的歧視與不公,讓我非常悲傷與憤怒,然而她的誠實與這本書的存在又帶給了我希望。這是我首次見識到文字的威力──安妮法蘭克的文字存活了下來,並擁有改變他人生命的力量。
這本書之所以存在,我們要感謝梅普吉斯(Miep Gies),這位勇敢與公義的女子幫助安妮與她家人躲避納粹。吉斯不僅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提供安妮一家人食物與庇護,也是她找到了安妮的日記並加以保存,最後與全世界分享。
一九九四年,我開始在加州長灘的高中當老師。身為菜鳥老師,我被指派到無可救藥的一班,班上都是被別的老師放棄的學生。我的許多學生成長於暴力相向、種族歧視與仇恨的環境,很多人參與了羅尼金審判的大暴動(編註:1991年在洛杉磯發生的警察暴力案件,導致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
他們多數人都不期望自己能生存下去,更別說畢業了。於是我使用這本《安妮的日記》作為教具之一,讓學生知道文字的力量。教導他們瞭解如何運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孤立與恐懼──文字遠比噴漆或汽油彈更有力量。
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我的學生沒有教科書,因為校方擔心他們將書撕毀。我動用自己聖誕節的過節預算,為一百五十位學生每人買一本安妮法蘭克的日記,我認為,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書,會帶來很深遠的影響。
我很震驚許多學生根本沒聽過納粹大屠殺。於是我想辦法讓歷史課更生動。由於沒有經費進行校外教學,我又接下了兩個工作──當管理員以及賣內衣,讓我能存下足夠的錢帶學生去洛杉磯的寬容博物館(Museum of Tolerance)。這趟旅程對我們每個人都產生很深的影響,也讓他們明白學習不只發生在教室裡。
痛苦的經驗是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生們開始對年齡相仿的安妮產生認同感。也開始明白他們也活在自己所謂「未被宣告的戰爭」中。長灘的街道固然非二次大戰的歐洲,但就像安妮法蘭克,我的學生也受到歧視,也常在暴力事件中失去朋友與親人。
雖然安妮也被可怕的暴力環繞,但她選擇以文字而非武器來反擊。透過她的示範,我的學生開始瞭解文字能長存,且可以帶來改變。他們開始寫自己的日記,這是一種淨化與解放,同時也是令人害怕的體驗,因為當他們把這些經歷化為文字,一切彷彿顯得更真實了。
當得知梅普吉斯還健在,我們決定把這些故事寄給她,並邀請她來我們的學校。而她真的來了,她成為安妮日記上白紙黑字與我們追憶想像間的一道橋樑。她的到來,讓發生在閣樓的那個故事顯得如此真實,她鼓勵我的學生要「尊重安妮的願望,好好生活,不要讓安妮死得徒勞」。
與梅普見面,在我的學生身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她非常謙虛與高雅,對於任何外界的注目總回說:「這比我更偉大。」但事實上她是賭上了自己的生命來行善。她並不需要這麼做,她做好事時並沒有攝影機在旁拍攝也沒有簽出書合約。她是在拯救人性,同時她也讓我們仍然能夠心懷希望。在被捕前,安妮法蘭克寫下:「儘管發生這一切,我仍相信人心本善。」我相信她在寫下這些字時,心裡想的是梅普。
梅普來班上演說時,一位學生特別被她的故事所感動,站起來表示她是他的英雄。她有點不高興的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我必須做的,因為這是正確的事。」這句話成了我與班上學生的格言──「做正確的事」,做決定時還有什麼更好的準則嗎?
我與學生一起讀《安妮的日記》已經十年了,也與我們的英雄梅普吉斯見了面。學生們寫的故事已經出版,所得用來幫助這些作者們上大學。現在,這些「為自由寫作者」成為了教師、社工、醫生與律師。他們常在電視上與國會裡發言。
最令我興奮的是,當我們應邀去學校演講,看到我的學生們讓新世代的青少年也把他們自己的故事寫下來。透過安妮法蘭克的文字與梅普做的一切,我與我的學生真正學到了文字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20.不知道怎麼做,就自己發明~~探討全球糧食環保方案的作家法蘭西絲摩爾拉佩(Frances Moore Lappe)
★法蘭西絲摩爾拉佩
俗語說「吃什麼像什麼」,但很少人像法蘭西絲摩爾拉佩那樣,切身瞭解這句話的意義。
拉佩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食物供給時,突然得到了一個啟示。她的計算讓她得到一個結論──世上每個人都可以有足夠的食物與營養,只要大家少吃魚、肉,多吃蔬果。她的洞見之作《小小星球的減食方案》(Diet for a Small Planet),開始了一個創造健康與更有效率方法的運動,來滋養地球上的所有人。
拉佩繼續出版了《糧食優先》(Food First),讓世上的窮人有資源以環保的方式來餵飽自己,還有「小小星球學院》(Small Planet Institute),鼓勵一般人有創意地在日常生活中參與「生活裡的民主」。
她的著作提醒我們,我們選擇吃下的每口食物都會帶來極大的影響。透過這些選擇,我們可以幫助同胞,積極地創造我們想要的世界。
★法蘭西絲摩爾拉佩的英雄──肯亞民運人士旺嘉莉馬泰
不久前,我很興奮得知科學家在我們腦中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當我們看到其他人做事時,就會觸發這些神經元,彷彿我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想像一下!所觀察的事物竟成為自身的體驗。這表示我們注意的對象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為我們會變成他們。
因此我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肯亞民權人士旺嘉莉馬泰(Wangari Maathai)身上。二○○四年,她加入曼德拉、卡特總統及其他世界的知名人物,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不是因為她得了諾貝爾獎才成為我的英雄,而是她一直擁有我想要學習的優點──力量、勇氣與希望。旺嘉莉馬泰是我的英雄,因為她是一個「不聽話的女人」。
在一九七○年初期,旺嘉莉成為東非第一位獲得生物科學博士學位的女人,她看到撒哈拉沙漠逐漸往南移。在一個世紀內,肯亞的叢林就縮減為不到以前的百分之五。旺嘉莉知道全國的生態都受到威脅,將有惡劣的後果,村民(主要是女人)必須走更遠才能拿到水與柴火。所以旺嘉莉決定採取行動。在一九七七年的地球日,她種下了七棵樹,發起了「綠腰帶運動」(Green Belt Movement),這個鄉村種樹運動的影響遠大於樹木本身。
當她開始時,由英國人所成立的肯亞林業服務處嘲笑她。「什麼?未受訓練的村婦種樹來扭轉沙漠入侵?不行,那需要受過訓練的林業人員才行!」但旺嘉莉沒聽從他們。
「林業專家們很不高興,」旺嘉莉告訴我們,「他們說我在玷污這個行業。我告訴他們:『我們需要百萬棵樹,你們林業人員人數太少了,永遠種不出來。所以你們應該讓所有人都成為林業人員。』我都稱參與綠腰帶運動的女人為沒有文憑的林業人員。」
因為旺嘉莉沒聽話,肯亞現在才會多了三千萬棵樹,全由未受訓的村婦所種植。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我的英雄,許多人讚美她堅定的意志,驚人的成就與她熱情的感染力。他們稱旺嘉莉為環保人士,他們稱旺嘉莉為人權與女權鬥士,民主鬥士。這一切都很正確。但旺嘉莉是我的英雄,因為她瞭解真正的戰鬥並不是為了權利或環保本身。她瞭解真正的戰鬥是發生在內心,當凡人在內在做出改變──去瞭解屬於我們自己的力量,不管這改變多麼令人恐懼。
「我們打破了陳規。」當我與女兒安娜在二○○○年時來到肯亞訪問旺嘉莉時,她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告訴女性:『使用妳們知道的方法,你們若不知道,就自己發明。』她們使用破掉的陶罐,把種子與土壤放進去,看種子發芽。如果發芽了,很好;如果沒有,再試一次。」
換言之,她告訴婦女們要信任自己。
由於她的努力,教導成千上萬村婦挺身面對酋長、丈夫、殖民官與跨國企業人員,表達她們自己的傳統與常識,獲得勇氣來邁向光明。她們說:我們有解決的方法。我們可以承擔責任。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村莊與國家,還有我們的世界。
有一晚,在奈洛比,旺嘉莉告訴我們一個故事,完美描述了觀點的轉變。「我在大裂谷長大,」旺嘉莉告訴我們,「在山谷兩側都是懸崖。我曾經以為那些懸崖,那些有雲的山峰就是世界的盡頭。我曾經相信我看到的就是全世界。」
「然後有一天,我們出去旅遊,我這輩子最遠的一次。我第一次來到了懸崖的頂端,我發現後面還有東西。我非常高興知道整個世界不只是那個峽谷,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小旅行讓我想起了後來的很多旅行。在出發以前,你以為世界只有如此,然後你來到懸崖邊緣,看到還有其他世界。生命中有許多懸崖,你若願意爬上去,就會看到背後另有天地。但你若不願冒險爬上去而停留在安全之地,那麼你當然永遠無法看到懸崖之外的天地。」
五年前在肯亞與旺嘉莉道別時,我的心情十分沈重,因為她的運動缺乏資金。當我回家後,得知她因為反對非法伐木而又遭到監禁,我更是心痛。朋友們都說我是樂觀主義者,但連我都無法想像,更別說預測後來幾年所發生的改變。在二○○二年,旺嘉莉勝選進入了國會,比最接近她的對手票數多了五十倍。不久之後,她被提名為副環保部長,婦女紛紛在奈洛比街頭舞蹈慶祝。
綠腰帶運動的女人穿著簡單的白圓領衫,上頭印有簡單的標語:「至於我,我做出了選擇。」每次看到,我的心頭都會為之一震。這是旺嘉莉所教導我的──為了創造我們想要的世界,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儘管沒有成功的保證;儘管可能面對譏嘲與失敗。
我以前會開玩笑說,只有膽小鬼才需要懷抱希望,因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困難的真相。但旺嘉莉讓我知道其實是相反的──希望是勇者才有的。因為希望無法在現有的證據中找到。我現在才明白,只有當我們傾聽自己最深的瞭悟,並決定採取行動,才能擁有希望。
34.言語之力能抗刀槍~~拯救盧安達難民的飯店經理保羅盧西沙巴金納(PaulRusesabagina)
★保羅盧西沙巴金納
一九九四年春天,胡圖族(Hutu)極端份子佔領了盧安達街道,有組織地屠殺同胞圖西族(Tutsi)與溫和派的胡圖族。三個月內,豪華的米爾柯林斯大飯店(Mille Collines Hotel)成為一千兩百名盧安達難民的家,許多人全家躲在飯店裡避難。保羅盧西沙巴金納是飯店經理,他運用機智與國際關係及談判技巧來保護難民。
他的故事被好萊塢拍成電影《盧安達飯店》,保羅的姓「盧西沙巴金納」是一個戰士名字,意思是「打敗敵人獲勝的戰士」。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個姓的確名符其實。幾乎有一百萬盧安達圖西族人與溫和派胡圖族人在這一百天的大屠殺中喪生,但保羅盧西沙巴金納努力庇護的一千兩百六十八人,包括他的圖西族妻子與四個子女,都平安生還。
★保羅盧西沙巴金納的英雄──父親魯弗瑞湯瑪斯、尼爾森曼德拉
我有兩個英雄。第一個是我父親,魯弗瑞湯瑪斯(Rupfure Thomas);第二個是尼爾森曼德拉。
我父親塑造了我的生命。他教導我對鄰居朋友誠實與真誠。在記憶所及,人們都需要我父親。他們都知道當鄰里間有了麻煩,找他就對了。
當我在盧安達長大時,有一種解決紛爭的作法叫「草地正義」。一群長者會聚集在一棵樹下,討論村莊裡的問題。在盧安達發生的糾紛通常與土地或財產有關,長者組成的法庭會聆聽爭議,然後我父親會來解決問題。村莊裡的人會告訴我,「等你父親來了,他就會解決這個問題。」所有人都知道他會說出真相。
有時候那些說謊的人聽到他要來了,就突然坦承一切!這就是我父親的威力。他對人直截了當。他成為了我的英雄。
他也眾所皆知能為爭議的兩方說話。雖然他很善於言詞,他也是個好聆聽者。因為他真誠地聆聽,村裡的人相信他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後來,我上了大學取得學位。他們教導我基本的企業管理原則──只要傾聽,你就解決了一半的問題。但我已經知道這個道理。這是我在草地上坐在父親膝蓋上時學會的。
我父親教導我,若想長久認真的過日子,就必須誠實。在盧安達有句諺語:「你可以靠著說謊吃到一次飯,但終究無法因此餐餐飽足。」然而人每天都必須吃飯。誠實是最基本的。
眾所皆知,我父親不僅慷慨分享他的智慧與領導,也與需要的人分享他所擁有的,來建立社區的信任。我母親會送牛奶給沒有牛的鄰居,送食物給飢餓的人。
父親對他身邊的一切事情都很關注,特別是他的孩子們。即使兄弟姊妹都已經在外成家,我們仍會在新年前夕到父親的居所聚會。他會告訴我們,他對於我們近況的想法──「你還不夠努力、你做得很好、你只做到一半。」他對我們非常坦白。他有九個孩子,但他很清楚我們每個人的情況。
他的關照讓我們瞭解彼此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很強悍,我們尊敬他,但不會畏懼他。我與我妻子的關係就很像我父親跟我母親。他們在一起四十九年,直到我母親過世。在婚姻中,每一方都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每一方都要給予與讓步。我父親也非常善於這樣的交涉!
我父親的教誨跟隨著我。他教育我的方式也是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我父親曾經告訴我們:「不與父親交談的人,永遠無法得知祖父說了什麼。」對我父親而言,交談是最重要的。在傳達訊息上,交談是一種特殊的權力。
我另一個英雄是尼爾森曼德拉,我小時候在學校讀書就知道的。
我從曼德拉學到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永遠不要改變你傳遞的訊息。從一九四六年到現在,他一直忠於自己所傳遞的訊息──為了權利而抗爭,同時也要尊重其他人的生活。他關注黑人的權利,但讓他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他同樣尊重白人。他知道南非是一個有白人、黑人、中國人、印度人──所有人的土地。
後來,當他在一九九四年得到政權後,他知道他老了。成為南非領導人是他的驕傲,但他也懂得要交出權力,不要把持。我非常敬佩這樣的品格。曼德拉一直都告訴他人:「你有你的權利,但我們也有我們的權利。」要看到事實,要公平。
曼德拉從年輕時就為爭取他自己及所有人的權利而奮鬥。就算身陷囹圄也從未改變他的立場。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做得到。我沒有如此的信念。
但我感覺到他倆都陪伴著我度過大屠殺──我面臨自己的真理考驗。除了留下來幫忙我別無選擇,若是父親,也絕不會逃離這樣的處境!我只能效法他。如我從曼德拉身上學到的,希望我也的確做到堅持自己的立場了。
大屠殺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晚上爆發。翌日早晨有二十六名鄰居躲藏在我家中。我們本來以為戰事只會持續一週或數天。所以他們住到我家,他們感覺比較安全。
當士兵前來把我帶到飯店時,我立刻知道我不能讓鄰居留在家中。我唯一的選擇是說服士兵,我的鄰居也是我的家人。我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帶我去飯店,這是個好主意,但我不能讓家人留在這裡。」
在路上,我們被同樣的士兵攔下,他們威脅我們。我說,「我知道你們很渴,很餓,很累。你們都對這場血腥的戰爭感到厭倦,但你們相信你們的敵人是這個老人嗎?是這個寶寶嗎?你們願意手上染著這個寶寶的鮮血嗎?殺戮有什麼利益?如果今天要面對歷史,你們會說什麼?」
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可以帶我家人與二十六個鄰居跟我去飯店。
當我有機會離開米爾柯林斯大飯店時,我面臨了最困難的選擇。我知道有些人會被撤離。我看著飯店中的那些人,那些難民──當時大約有八百人,還有更多人要來。我看著他們。我知道我可以第一批被撤離,但我也是唯一能夠跟民兵打交道,來幫助難民的人。如果我撤離了,我可能不會被殺害。如果我沒有被殺害,我不知道我將來良心是否能平安?如果我留下這些人,而他們被殺害了,我要如何活下去?
我找來我妻子與孩子,告訴他們:「聽著,你們明天就會被撤離。」他們說:「那你呢?」我告訴他們:「我不能跟你們一起離開。如果我離開這裡,這些人會被殺害,我將永遠食不知味,夜裡也永遠無法安心入眠。我會一直有罪惡感。」我說:「請接受我的決定,離開這裡。」
我護送我妻子與孩子們上卡車。幫助他們坐好,送他們離開。那真是心碎的一刻,非常困難的抉擇。
最後一輛卡車離開時,收音機已經播報出卡車上的撤離名單。我聽到了處死我家人的命令——聽到他們說出我妻子的名字;聽到他們提到我一歲半大的兒子崔索(Tresor)。他們說:「這些蟑螂都要離開,他們都要逃走。他們是被聯合國從米爾柯林斯大飯店撤離。這些蟑螂中,有一個叫崔索盧西沙巴金納。他假裝要去比利時。但他不是要去比利時!他是要去敵人那裡,然後回來攻擊我們!」
他們就是這樣說我只有一歲半大的兒子。
我家人與其他撤離的人並沒有走很遠,在距離大飯店不到兩公里的地方,他們被攔下,被毆打。大多數人都受傷,包括我妻子。等她回來時,她幾乎無法站起來。她只躺在那裡,像死掉的人一樣。但她活了下來,其他在米爾柯林斯大飯店避難的人也都活了下來。
想像你開車經過你的村莊,聽到人們被屠殺的聲音,看到熟悉的鄰居屍體。你說,「這是保羅,那是彼得!」有人過來對你說:「你這個叛徒!你很幸運,我們今天不殺你。但拿下這把槍,殺掉這裡的所有蟑螂。清理這些害蟲。」這些蟑螂就是你的妻子、孩子、鄰居。
這時候你沒有選擇,只能開始行動,開始溝通。於是我就開始了。我從來不想動用刀槍,我想靠辯論溝通來打這場仗。有時你佔上風,有時落下風,從中你會學到認可與尊重,有時候終能說服另一方。我從我父親與曼德拉身上學到,言語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即使當我見識到最猙獰的人性面目時,他們的力量也帶給了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