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羅浮宮
1972 年到巴黎讀書,我與羅浮宮就結了不解之緣。我當時修藝術史的課,憑著一張學生證,任何時候,不用買票,隨時可以進羅浮宮。
羅浮宮在巴黎市中心,我又喜歡在巴黎走路,常常經過羅浮宮,想到一張畫,就進去看一看。只看那一張,看完,做了筆記,出來在塞納河邊坐一坐,看看河水,想一想剛才畫裡的色彩光影,再繼續做其他的事。
後來我才發現,進博物館,只看一件作品,是多麼奢侈的事。
大概在 1973 年開始,我就接了一個旅行社兼職導遊的工作,專門接待到巴黎旅遊的華人。其中多半以台灣的遊客為主,偶爾也接到香港、新加坡的華人團體。
到巴黎旅遊,羅浮宮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站。
旅行社也看重我對藝術史的專業,可以在講解羅浮宮作品上發揮我的所長。
1970 年代,台灣的歐洲旅遊才剛剛開始。一組旅行團的人數通常在四十人左右。為了吸引顧客,常常要找一位豔星作號召。時間的安排更為奇特,常常是三十天跑十八個國家。
一個社會在富有的初期,從封閉走向開放,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渴望在最短的時間看到最多的東西,渴望用最低廉的價格買到最多的物品,「俗擱大碗」的價值觀因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的工作常常是在巴黎的奧利機場──當時還沒有戴高樂機場──接團。他們通常已經去過倫敦,從倫敦飛巴黎,台灣的時差還沒轉過來,睡眼惺忪。我在車上介紹巴黎,在後視鏡裡看他們或向窗外張望,或疲倦到沉沉睡去,心裡有許多不忍。
這樣的旅遊團通常在巴黎的時間只有一天,有些景點是指定一定要去的,例如:艾菲爾鐵塔、凱旋門、凡爾賽宮、蒙馬特紅磨坊,而且一定要有一張自己與景點標誌的照片。
羅浮宮當然也是一定要去的景點,時間連頭帶尾一共兩小時。指定要看到的作品,有蒙娜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勝利女神雕像,所謂的「鎮館三寶」。
當時羅浮宮還沒有改建,只有一個入口,陰暗陳舊,動線很呆板,因此看完米羅的維納斯,要走出希臘館,上樓梯到二樓,穿過大長廊,為了爭取時間,一路用小跑步,跑到長廊中段右轉的一個小房間,看到人山人海的觀眾密密麻麻簇擁在「蒙娜麗莎的微笑」面前。
當時台灣的遊客很勇敢,理直氣壯,用台語說「惜.、惜.──」如同摩西分開紅海,一路分開各國遊客,走到畫前面,在眾人還搞不清狀況的時候,獨得先機,拍到一張自己與蒙娜麗莎微笑的合影照片。
領隊一直催促他們,因為他知道要跑出羅浮宮,在杜勒麗公園找到遊覽車起碼還要四十分鐘的時間。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知道能夠進羅浮宮,沒有時間壓力,只看一件作品的幸福。我也知道,看完一件作品後,走到塞納河邊呆坐,回想畫中色彩光影的幸福。
羅浮宮像一套滿漢全席的大餐,琳瑯滿目,沒有好的導引,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從何下手。
許多人去了羅浮宮,只留下在裡面小跑步的經驗記憶。不只台灣遊客在小跑步,全世界的遊客都在小跑步。美國人跑完,日本人跑,日本人跑完,台灣人跑,這幾年是韓國人在跑,又加上剛開始的中國大陸人也來小跑步了,人數之多,更為壯觀。
上一世紀七○年代羅浮宮的故事,給我許多反省:我所學習的「藝術」,我所學習的「美」,我所留戀徘徊的「羅浮宮」,究竟是什麼?究竟有什麼意義?對一般大眾,「羅浮宮」應該只有在裡面「小跑步」的記憶嗎?只有與「蒙娜麗莎的微笑」合影留念的記憶嗎?
那一個年代到歐洲旅遊的台灣遊客,多是白手起家中小企業的第一代。他們平日辛勤工作,省吃儉用,在巴黎的旅途中看到他們帶著泡麵,帶著年老出身農家的父母,站在米羅的維納斯雕像前面。老太太無法瞭解為什麼一個裸體女人是「鎮館之寶」,我講了很多,關於維納斯,關於希臘神話,關於希臘對身體的歌頌,來自台灣鄉下農家的老太太還是無法瞭解,她忽然轉頭用台語問我:「這啥人ㄝ某?」
「這是誰的老婆啊?」
我愣了一會兒,我知道維納斯的丈夫是武器之神福爾坎,但老太太顯然不是要知道這一故事。她或許是無法瞭解維納斯「美」在哪裡?一個赤裸裸的女人,沒有丈夫管嗎?她心中充滿疑惑。是的,羅浮宮對她而言只是一個滿滿都是疑惑的奇怪地方。
我學習「藝術史」,我學習「美」,有一天,如果我無法回答這樣一位老太太的疑惑,我的學習有何意義?
藝術與美,在學術專業的領域討論,使用專業術語,其實並不困難。兩個都在寫藝術博士論文的學生彼此談維納斯也不會有溝通上的障礙。
但是,「這啥人ㄝ某?」這句問話一直盤旋在我心中,這個老太太當然極可能就是我的母親。我學習的專業,有一天,能不能為自己的母親解開一點「美」的疑惑呢?
1976 年回到台灣,在大學教書,教建築系、美術系的學生,講解羅浮宮,講解維納斯都不會有「這啥人ㄝ某?」這樣尷尬的問題。
但是,教學到了沒有「尷尬」,其實也就沒有「挑戰」,沒有「反省」。
我的心裡一直還迴盪著老太太那一句石破天驚的問話。我所鍾愛的「藝術」,我所鍾愛的「美」是要說給老太太這樣的眾人聽的。
在東華書局出版過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與「西洋美術史」,「寫給大家」的「大家」是從老太太的問話發想的。
離開大學專業領域之後,可以更放膽去寫自己的書,在廣播做美術介紹,各處演講與「美」相關的主題,在大眾面前,我雙手合十敬拜,總是覺得那對「美」充滿疑惑的老太太就在台下。
這些年常常重回巴黎,每一次去巴黎,也還是會去羅浮宮。密特朗執政時代羅浮宮經過改建,貝聿銘設計了玻璃金字塔的入口,羅浮宮有了新的中心點,動線從中央放射到各個不同展區,分類更清楚,節省了很多在裡面「小跑步」的時間。但是能夠悠閒地在羅浮宮看畫的人還是少數,能夠看幾張畫,走出來在塞納河邊坐著,看看河水,回想畫的色彩光影的人,更是有莫大的福氣。
2008 年,有一些朋友跟我去巴黎,他們都是台灣經濟發展到成熟時期的企業家。常常去巴黎,有一種不慌不忙的從容。我們在羅浮宮一件作品前停留很久,談一談自己的感覺,到很古典的餐廳喝一杯咖啡。沒有用「小跑步」看羅浮宮,他們覺得很幸福,但是談起來,大家都曾經有過「小跑步」的記憶。
「美」是奢侈的,因為需要時間累積。需要從貪婪地狼吞虎嚥,慢慢地轉變為看一件作品,感受一件作品,心中只被這一件作品充滿,有共鳴,有滿足,有喜悅。
我因此想寫一本羅浮宮導覽的書,按照年代的分期,從最古老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 、波斯開始,看到希臘、羅馬,看到中世紀、文藝復興,看到巴洛克的富麗堂皇,洛可可的細膩精緻──羅浮宮事實上是一個縱觀人類文明漫長美術史最好的地方,每一個段落,都有作品,使人忍不住要停留、沉思、讚嘆。
我設想一個閱讀華文的遊客,可以帶著一本書,慢慢在羅浮宮裡倘佯欣賞,不慌不忙,但也不會遺漏最重要的作品。羅浮宮建築本身是偉大的藝術品,我總建議朋友看完畫,走出羅浮宮,應該在「方庭」(cours carree)坐一坐,「方庭」的建築是羅浮宮巴洛克形式的經典。坐在「方庭」可以遠遠看到貝聿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框在圓拱門裡,像一張畫。羅浮宮在傍晚以後的打光極美,與白天不同,沒有太多遊客的黃昏,從新橋或藝術橋越過塞納河,走進方庭,聽到巴哈長笛演奏,幽微的暮色之光,玻璃金字塔倒映在水池中,一層一層透明的光,璀璨華麗,又如此安靜,可以一直走到杜勒麗公園,走到香榭麗舍,看最繁華如夢的巴黎。
許多朋友知道我在巴黎的黃昏有這一條穿越羅浮宮的「私密路線」。我把這條「私密路線」寫在這本書裡,給年輕朋友一個夢想,在成年後可以實現。
去走羅浮宮,去讚歎世界文明最美的一條「私密路線」。
蔣勳
2009 年 7 月 7 日於八里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 二版(隨書附贈經典「羅浮宮導覽」手冊小摺)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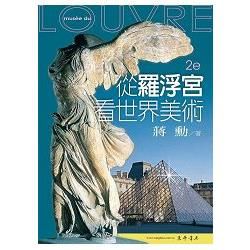 |
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二版) 作者:蔣勳 出版社: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7-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10 |
二手中文書 |
$ 379 |
藝術美學/欣賞 |
$ 408 |
社會人文 |
$ 432 |
中文書 |
$ 432 |
美術 |
$ 459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 二版(隨書附贈經典「羅浮宮導覽」手冊小摺)
.由建築、歷史、經典名作,深入了解羅浮宮
.依獨具代表的典藏品之年代及地區,詳盡介紹世界美術的演變
.精美的藏品圖片,並附有局部放大圖可看到作品細部
.深入介紹作者的創作背景,洞悉羅浮宮代表作品隱藏的含義
.隨書附贈經典「羅浮宮導覽」手冊小摺,貼心設計的隨身攜帶尺寸,讓您更方便參觀,不怕留下任何遺憾
作者簡介:
蔣勳(1947年-)台灣知名畫家、詩人與作家。出生於西安,祖籍為福建長樂。以花卉、水景繪畫受台灣人歡迎、以美感的教學和省思受到學子喜愛。他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和藝術研究所。於1972年到法國留學,1976年返台。在繪畫創作之餘,蔣勳也在文學界勤勞耕耘,他出版過多本詩集、並曾擔任台灣早期美術刊物《雄獅》的主編輯。他是現任的《聯合文學》社社長。
蔣勳曾得過全台灣小說比賽第一名、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以及吳魯芹文學獎,他從青年時代就是個文藝青年。1966年參加耕莘青年寫作會舉辦的寫作班,後來進而成為授課教師。他還有另一個特色就是曾經做過廣播節目《文化廣場》、此節目由台灣警察廣播電台播出,相當受到好評,獲得了1988年的金鐘獎。自2004年起,於IC之音.FM97.5(竹科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主持每週五晚間八點「美的沉思」節目,並以此節目再度獲得2005年廣播金鐘獎最佳藝術文化主持人獎。
作者序
我與羅浮宮
1972 年到巴黎讀書,我與羅浮宮就結了不解之緣。我當時修藝術史的課,憑著一張學生證,任何時候,不用買票,隨時可以進羅浮宮。
羅浮宮在巴黎市中心,我又喜歡在巴黎走路,常常經過羅浮宮,想到一張畫,就進去看一看。只看那一張,看完,做了筆記,出來在塞納河邊坐一坐,看看河水,想一想剛才畫裡的色彩光影,再繼續做其他的事。
後來我才發現,進博物館,只看一件作品,是多麼奢侈的事。
大概在 1973 年開始,我就接了一個旅行社兼職導遊的工作,專門接待到巴黎旅遊的華人。其中多半以台灣的遊客為主,偶...
1972 年到巴黎讀書,我與羅浮宮就結了不解之緣。我當時修藝術史的課,憑著一張學生證,任何時候,不用買票,隨時可以進羅浮宮。
羅浮宮在巴黎市中心,我又喜歡在巴黎走路,常常經過羅浮宮,想到一張畫,就進去看一看。只看那一張,看完,做了筆記,出來在塞納河邊坐一坐,看看河水,想一想剛才畫裡的色彩光影,再繼續做其他的事。
後來我才發現,進博物館,只看一件作品,是多麼奢侈的事。
大概在 1973 年開始,我就接了一個旅行社兼職導遊的工作,專門接待到巴黎旅遊的華人。其中多半以台灣的遊客為主,偶...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先談一談羅浮宮的建築歷史
羅浮宮走向現代
羅浮宮文化軸線的起點
沒有錯過的遺憾
從哪裡看起?
第二章 埃 及
書記坐像
霍茹斯立像
Wahibre石雕蹲像
蘭姆西斯二世
獅身人面
書記夫婦像
木雕夫婦像
哈托女神與塞特一世
蘭姆西斯三世石棺
托勒密法老王
阿克那屯像
第三章 西亞兩河流域文明
納蘭辛勝利紀念碑
漢摩拉比法典石碑
亞述帝國人面牛身城門石雕
波斯彩磚城牆與弓箭手
第四章 希臘藝術與羅馬藝術
巴特農神殿浮雕
米羅的維納斯
薩摩特拉斯勝利女神
戰士雕像
羅馬時代阿波羅
羅...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勳
- 出版社: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7-08 ISBN/ISSN:978957483819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6頁 開數:16開
- 類別: 中文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