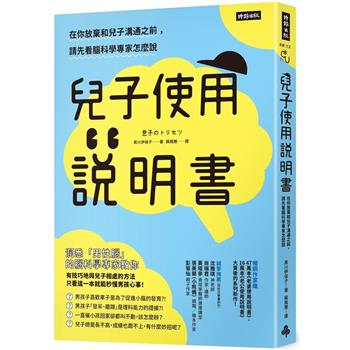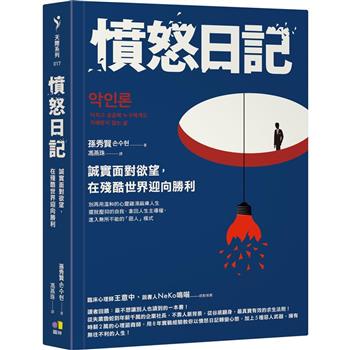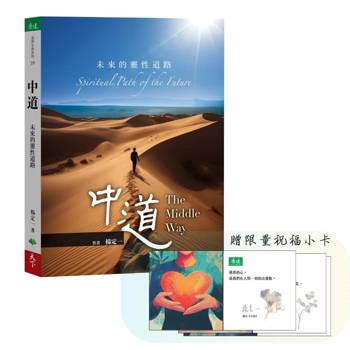苦命的序
石齊平新書「中國:大趨勢,大博弈」,請李大哥寫序。序寫好後,長江文藝出版社說審查通不過,只好斷頭求生。我笑著說:五十年前,我寫的「蔣廷黻選集」序和李鼎彝「中國文學史」序,就被國民黨掐死過,這種斷頭求生的經驗,我太豐富了。五十年間,我首事兩端,誰說歷史不重演啊?
還有,四季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全集」,本是有序的,那篇序標題「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還沒印好前,先發表在「四季雜誌」第十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日)裡。不料一發表後,由於措辭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為了全集得以順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刪除了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沒有序的大書。序和正文,身首異處,相隔千里,正像關老爺的下場一樣!
在廢墟上蓋小建築
三十年前,我讀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我最喜歡這麼一段:「苦難當前,我們正置身廢墟之中。在廢墟中,我們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這當然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但已沒有更好的路通向未來了。我們要迂迴前進,要爬過層層障礙,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罷,我們還是要活。」(The cataclysm has happen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這段文字,可說是我在島上處境的最好描寫。我的確是在「廢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可是一次又一次被摧毀了。在每一層的「廢墟之中」,都有我「小建築」和「小希望」的殘跡,恰像那一層蓋在又一層上面的特洛伊(Troy)古城,你會發現:自己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過去已經化為塵土,可是,就憑那些塵土,你活到現在;不但活到現在,還從現在朝向未來。
我的祕密正業
我笑我自己「不務正業」。我笑我的「正業」不是思想、文學、歷史,而是中國藝術品的鑑定。張大千說他畫山畫不過張三、畫水畫不過李四,但是鑑定藝術品本領五百年他是第一。張大千死後,這頭銜我私下承受了。唯一不同的,我的本領不只第一而且唯一而已。
由我發現並收藏周越墨跡一事上,便足證明。自啟功以下,大陸七大專家都被我比下去了。啟功用文字表示周越的墨蹟世界沒有了,但我卻說不但有,還在我手裡。七大專家劉九庵、楊仁愷來台灣,到我家看到真貨,都嚇到了。最後,啟功修改了他的書,並在他主編的「中國法書全集」第六冊裡,正式收錄了我的收藏。書前列有七大專家的名字,以示肯定:謝稚柳(原上海博物館問、書畫家)、啟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書法家)、徐邦達(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畫家)、楊仁愷(遼寧省博物館名譽館長、研究員)、劉九庵(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傅熹年(建設部高級建築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謝辰生(原國家文物局顧問)。最後,李敖的大名進入了「中國書法史」。我可是登記有案的大咖呢。
「進廣告」寫書法
電視節目看得正起勁,突然來了一句「現在我們進廣告」、「現在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我這本「李敖風流自傳」就是這樣寫法。談得興起,突然中斷一下,插播進來又相關又不相關的一節一段或幾節幾段。像演講中停下來,喝口水、潤潤喉。也像說書的,在緊要關頭,突然停了,拿出帽子,倒過來,傳來傳去,收起錢來了。我為什麼不這樣寫本書呢?為什麼要為章法所限、正經八百呢?請你習慣我寫這本書的花樣吧。廣告時候,請別去小便,因為我可能正在小便。我跟棺材板連戰一生沒講過話,但他跟我講過四個字。競選偽總統時,他忽然走過來,向我情急拜託「借過借過」,原來他被尿憋得急,要小便,而我正站在洗手間門口。(至少那天連戰很規矩——他沒鑽進女廁所!)
「小Y」
一九六七年春天,在文星被迫改組、和我分手後,文星資料室和我家之間的門也封死了。在官方壓力下,文星開始「從良」,編起與政治無關的字典來,成立小組,組員之一,就是「小Y」,那時她是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在這之前兩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評我,她來過文星,可是和我緣慳一面。這次到我隔壁上起班來,一天下班,在路上,我認識了她。她是個有深度又漂亮的大學女生,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立刻勃起「強姦」之念,因為她太迷人了。我約她在東門「美而廉」餐廳吃飯,她同意了,可是臨時寫信來,說不來了。我失望之下,仍開車到東門,結果在「美而廉」對面,看到她在看我來不來。她看到我,滿意的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由於我的邀請,她終於同意到我家來。她進門的第一個動作很怪異:拿起我的煙斗,並且把它擦乾淨。我們談話的時候,她宛如一個夢遊中的少女,說著許多「飄在雲裡」的話,飄呀飄的,從此我們之間寫了許多情書。
顯然的,「小Y」是又懲罰我又十分寵我的:懲罰我,為了我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她在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離我而去好多天;寵我,為了我的一封信,她會剪下全部長髮送給我,並在我生日時做卡片過來,把她的小照片,暗嵌其中。最後,她終於放鬆了一點,答應跟我進浴室,但她不肯脫光,只是寵我,像個古典女奴般的,為我洗遍身體,當她顯然漏洗了什麼,我提醒她,她背過臉去,還是為我輕輕的洗了。
號外
一九六八年五月,「小Y」寫了一篇文章,歷數她的情人,在「號外」一節寫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問我要去那裡,我說,我還不知道。
你問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臉上閃著很多開玩笑的表情,沒想到我竟認真的點起頭來,我說是的,我喃喃的說是的,我在等你,號外。
我從來不曾肯定什麼,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剛認識你的時候,你笑著問我,你該排在第幾號?我笑著,我的笑代表了我的驚愕,我想了一下才說,你排在十三號吧,或許我曾給了你為男孩編號的感覺;我沒問你,也沒認真的解釋,你呵呵的笑了兩聲,你說你連十三號都不是,你是號外。對嗎?
我開心的笑起來,我不要說不對,從此,我便認真的對自己喊起你號外來。
我喜歡同你說話,喜歡同你開玩笑,喜歡聽你說笑話,可是,這只是我喜歡而已,你的回應是淡淡的,有時候我對自己說,號外也許一點也不喜歡我吧!號外一定不會喜歡陪我在風中散步,號外也不會和我在雨中撐一把傘,號外多麼不同。但這種不同是當然的,因為他不喜歡我。
號外,你一定也有過很著迷的時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時候嫌晚了一些,而對我來說,遇到你卻是太早了一些,那時,我還不懂得抓住一點點自以為是的愛情,雖然,那種愛情也沒什麼用! 我應該有很多你的記憶,但是,我抬起眼睛,覺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陽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實在該走近你,但我還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聽到夢碎裂的聲音,夢的破碎在無形中我還經受得起,我怕我還要固執一個沒有回覆的愛情,我又望見你的年輕在陽光底下煥發著,我輕輕的閉上眼睛,我讓心一陣接一陣的抽著痛。你讓我懂得什麼叫心痛。 號外,如果我對你有過幻想、有過渴望,那麼讓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這樣死去,死去從你身上,讓我的愛情連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許,你真的是號外吧,還好你說過你是號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該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寫「號外」時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終於有一天,她回來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實在該走近你。」我們手牽手,依偎著,一起走進陽明山「新薈芳36」,在溫泉旅館中,她給了我處女所能給出的一切。——「讓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這樣死去,死去從你身上,讓我的愛情連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後,她一語成願,真的埋葬在我身上。當我「強姦」她的時候、當她迷茫中喃喃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時候,回想起來,那的確是一種「死去從你身上」,我彷彿覺得:這可愛的小處女,正在被蹂躪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靈肉邊緣、在生死線外,人間還有更好的死法嗎?
……
名牌三帖
一、世界上的服裝設計師,十分之九都是屁精、男同性戀者。他們喜歡男人,不喜歡女人。他們為女人設計服裝,十分之九都是醜衣服,但女人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敢拆穿,因為設計師太有名了。男同性戀者不斷以醜衣服給女人,女人縱使穿對了一件,也抵銷不住那十分之九的醜衣服的暗傷或明傷。多蠢啊。
二、大家講究名牌。名牌一出,一擁而上。一開始擁的,是厭食症的模特兒,她們人人瘦高,所以名牌上身,「其間綽約多仙子」,不好看也好看。但名牌上市,效顰者或癡肥、或傻胖,噸位太重,穿起來,名牌兩個改裝成一件,也難掩其陳菊狀。蒼天不仁,我於陳菊見之。
三、世界上總該有人自告奮勇,告訴王效蘭;你不能那樣畫眼睛,因為你太像一隻交配錯誤的熊貓了;總該有人自告奮勇,告訴陳文茜;你不能那樣戴帽子,因為你太像鳳飛飛了。但是找來找去,世界上沒人這樣大膽,所以,人間只好看她們兩個在作怪。當然陳文茜才華四溢,王效蘭卻香水四溢,但香水是香水,她是她。
意淫
老去的祕密情懷不在回憶而在重現、在用新角度細看過去的匆匆。我更會詮釋過去,並且提升了過去。我會用經驗做底子,加上重現與意淫。靈肉會越來越拉開距離。肉已淡出、已老去;靈卻更提升、昇華、絢麗。十七歲永遠不會老去,因為她已凝結在圖像裡、剎那在寫真裡、鮮活在記憶裡。而我已越來越神化、精神化,走向意淫與 fade away。十七歲永不fade away,我會,但是「還有精神」。
我十八歲時候,在我前面有太多太多八十歲以下的老年人;我八十歲時候,在我後面有太多太多十八歲以上的青年人;在我十八歲到八十歲之間,有太多太多的意淫。
難忘陳碧君
那年交通大學請我演講,由學生活動中心學術部長陳碧君出面函邀,並約好由一位吳姓男生親來接我。時間到了,出現的卻是陳碧君本人,一位青春美麗的小女生。到學校後,他們請我吃晚飯。飯後陳碧君陪我看看校園,在細雨中、在夜幕中、兩人走在校園的路上。陳碧君對我說:「李先生,這條路有一樣特色,就是它是循環的。你走下去,會又走回原點。」我回答她:「這樣也好,你永遠循環,永遠不會迷路。」
演講的情況還不錯,為了答覆問題,兩個小時外,又延長了二十五分鐘,前後都由陳碧君主持。在演講中,我帶聽眾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但我始終在兩個世界。陳碧君坐在左邊第一排,我幾次稱她作「陳部長」。她的笑容是優雅的,我想,「阿麗思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中那隻貓如果看到,一定剽竊她的笑容。
過了幾天,朋友送我一支名貴鋼筆,我轉寄給陳碧君,並寫信指出,從她給我的信上,看出她用的鋼筆該換了。陳碧君收下我的禮物,並用新鋼筆,寫信向我道謝。
又過了幾天,陳碧君又寫信了。告訴我,每年一度的「梅竹賽」(清華與交通大學的競賽)在某一天開場了,她是交通大學的排球隊選手,盼我到新竹看她比賽。
我沒有回信,也沒在當天去看球賽。但是,我在球賽過後第二天獨自去了新竹,走在空無一人的球場,為之駐足,然後返回了台北。
我沒再見過陳碧君,此生也恐難見到。我到了路的原點、走回路的原點,我永遠循環,我迷了路。
我的模特兒
唐朝大詩人杜甫,寫大畫家曹霸,說:「將軍畫善蓋有神,每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為什麼要在馬路上找路人去畫呢?因為創作者需要模特兒寫真,作品才能飛揚生動。一般刻板印象只以為畫家需要模特兒、雕塑家需要模特兒、攝影家需要模特兒、服裝設計師需要模特兒,殊不知文學家也需要模特兒。
模特兒的範圍很廣,當我為老兵喊話時,滿身傷痕的是我模特兒;當我為慰安婦義賣時,滿腔悲憤的是我模特兒;當我為小雛妓仗義執言時,滿眼憂傷的是我模特兒。
當然,我也有正點的模特兒,當我寫「虛擬的十七歲」,我的實體模特兒真的確有其人、確有其形,她是傳統說法的模特兒,跟畫像藝術品配合,必要時,也跟畫家藝術家上床。
在文星時,林絲緞出版「我的模特兒生涯」,絕大部分是我改寫的,黃三也改寫了一部分。我從沒見過林絲緞,但她作為攝影模特兒,太健康了。但我看了許多外國的攝影集,都覺得模特兒太健康了。而我所欣賞的、所需要的,悉屬羽級。身高一六八,卻四十公斤以下,才是我通過的尺碼。
赤裸的十七歲
在寫「虛擬的十七歲」前,我的構想是寫「赤裸的十七歲」。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寫出大綱:
「赤裸的十七歲」這本書,以赤裸為書名,有人會大驚小怪,其實他如看過美國作家巴洛茲(William Seward Burroughs)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或諾曼.梅勒的「赤裸的和死亡的」(The Naked and the Dead),就知道赤裸的真義不在黃色,而在萬紫與千紅。
岳飛十七歲做了爸爸、賀子珍十七歲做了革命黨,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十七歲不到死於集中營,魂歸成為名家;歐仁妮(Eugénie de Montijo)十七歲方至自言心已碎,老去成為皇后⋯⋯多少的萬紫與千紅,都來自赤裸、來自十七歲。
「赤裸的十七歲」,是我以十七歲為主軸的小說,也是由模特兒穿插其中的高情遠致的小說。這模特兒是台北朱崙街的一位高中女生。我在「虛擬的十七歲」書中,創造了「朱崙症」和「朱崙現象」。因為「朱崙症」,淒豔的高中女生成了抵抗科技瘋狂的犧牲者;因為「朱崙現象」,這一犧牲給了人類最後的餘光。如今,十年過去了,那遠去的十七歲,名字是C.J.周,她在朱崙街念了高中,她是「虛擬的十七歲」的模特兒,我寫下「朱崙」,一如寫下了她的名字。“Deliver a real novel along with a mystery.”這是我的最後感覺。小說那麼真實、「朱崙」那麼神祕。沿著神祕,我告別了真實的十七歲。
書成後記
寫這本「李敖風流自傳」,其實我自己並不怎麼贊成。直到我八十歲生日前四個月,我還反對。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記:「八十年來,除美麗的回憶外,都是六十五年在島上的腌臢事,忘了最好,不值得一寫。從風流水準言,一說就俗。行年八十,要把餘生花在令自己快樂的事上,俗人俗事都不值得花時間。」雖然我如此反對,但也轉念一想:一、我八十歲了,應該出本書來表示表示;二、如把書寫成一本紀功碑,把一些一說就俗的事寫得別有施教作用,寫了也好。轉念一想後,我還是寫了。限時四十天完成,因為我在忙著寫別的大書,花四十天以上的時間寫,就不值得了。
給他們時間,但我不再給我時間了
我一生被蠢人罵,自台灣而海外而海內而大陸,不知凡幾。最近最流行的罵法,是我應該慶幸被蔣介石關。這真是賤種邏輯。若說李敖應該慶幸被蔣介石關而沒被毛澤東關,因為毛會殺他。同一邏輯:應該慶幸被毛關而沒被希特勒(Hitler)關,因為希特勒會放毒氣毒他。更應該慶幸被希特勒關而沒被阿敏(I. Amin)關,因為阿敏會吃人肉吃他。依此類推,只要找個更狠的王九蛋、王十蛋、王十一蛋,就可開脫王八蛋了。怪哉怪哉!他們這些蠢人,太怪了吧?一位女士問猶太宗教哲學家馬丁.布勃(Martin Buber):時間與永恆之別在那裡?布勃說:即使我肯花時間說給你聽,你也得經過永恆去了解它(It would take an eternity for you to comprehend it.)。對先知說來,他必須有心理準備:蠢人可能跟不上你,他們尚在永恆中浮沉,要給他們時間來罵你。雖然,我已八十歲,能給出的罵我時間也不多了。但罵不罵我,已被我「耳順」掉了,我的人生方向,顯然已經意不在此。我要把我的餘生主力,用在永恆的、世界性的文學作品上,像我一九九一年寫的「北京法源寺」、二○○一年寫的「上山.上山、愛」、二○○三年寫的「紅色11」、二○○八年寫的「虛擬的十七歲」、二○一○年寫的「陽痿美國」、二○一一年寫的「第73烈士」。除了這類頂尖的書,我將「老棄台灣」、也「老棄祖國」。也不是很多話不該說,只是不該我說了。我給他們時間,但我不再給我時間了。八十歲了,我更朝前走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李敖風流自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524 |
社會人物 |
$ 545 |
社會人文 |
$ 552 |
文學人物傳紀 |
$ 615 |
中文書 |
$ 629 |
作家傳記 |
$ 629 |
作家傳紀 |
$ 629 |
社會人文 |
$ 629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李敖風流自傳
繼《李敖回憶錄》17年後第三部自傳
宋朝有個風俗,叫「八十孩兒」。小孩出生,為了盼他長壽,在他腦門子上寫「八十」兩個大紅字,以討吉利。現在我真的活到八十歲了,腦門子上要寫,得寫「八百」才過癮了。看來「八百」是活不到了,但寫幾百條浮生雜憶是沒問題的,於是我花四十天寫它幾百條。隨筆而為,盡得風流。唐朝詩人寫「文采風流今尚存」,是吹牛的,實際上,他們的「文采風流」,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實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視昔」者,我也;「後人視今」者,有乎哉?沒有也。千山獨行,千古一人,廣陵之散,從此絕矣!
吾愛孟夫子,
風流天下聞.
我找李大師,
雲端不可尋.
前兩句是李白讚美孟浩然的詩.
後兩句是電腦雲端找不到的詩.
本書顛覆李敖以往的書寫模式:信筆所之,不計較章法、文體、均衡感、首尾相顧,但得徜徉自然,不怕亂七八糟、不怕不連貫。有時用瓜蔓式,有時長話短說,有時短話長說,囉唆一下。有時用跳躍式。跳躍式寫法最自然。看來沒頭沒尾,其實自成單元。別出心裁的體例,展現出李敖爐火純青的功力。
作者簡介:
李敖
一九三五年生於哈爾濱,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
李氏文筆自成一家,被喻為百年來中國人寫白話文之翹楚。發表著作上百餘種,以評論性文章最膾炙人口。《胡適評傳》、《蔣介石研究集》為其代表作。
西方傳媒更奉為「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批評家」。
近作《李敖回憶錄》獲選為一九九七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其續作《李敖快意恩仇錄》亦擠身暢銷書榜,一九九九年五月,來台五十週年,出版《李敖禍台五十年慶祝十書》,一九九九年八月,獲新黨提名參選二○○○年中華民國總統,二○○一年五月新作《上山‧上山‧愛》甫一推出即引起讀者熱烈迴響。
章節試閱
苦命的序
石齊平新書「中國:大趨勢,大博弈」,請李大哥寫序。序寫好後,長江文藝出版社說審查通不過,只好斷頭求生。我笑著說:五十年前,我寫的「蔣廷黻選集」序和李鼎彝「中國文學史」序,就被國民黨掐死過,這種斷頭求生的經驗,我太豐富了。五十年間,我首事兩端,誰說歷史不重演啊?
還有,四季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全集」,本是有序的,那篇序標題「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還沒印好前,先發表在「四季雜誌」第十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日)裡。不料一發表後,由於措辭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為了全集得...
石齊平新書「中國:大趨勢,大博弈」,請李大哥寫序。序寫好後,長江文藝出版社說審查通不過,只好斷頭求生。我笑著說:五十年前,我寫的「蔣廷黻選集」序和李鼎彝「中國文學史」序,就被國民黨掐死過,這種斷頭求生的經驗,我太豐富了。五十年間,我首事兩端,誰說歷史不重演啊?
還有,四季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全集」,本是有序的,那篇序標題「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還沒印好前,先發表在「四季雜誌」第十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日)裡。不料一發表後,由於措辭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為了全集得...
»看全部
推薦序
「李敖風流自傳」破題
宋朝有個風俗,叫「八十孩兒」。小孩出生,為了盼他長壽,在他腦門子上寫「八十」兩個大紅字,以討吉利。現在我真的活到八十歲了,腦門子上要寫,得寫「八百」才過癮了。看來「八百」是活不到了,但寫幾百條浮生雜憶是沒問題的,於是我花四十天寫它幾百條。因為是浮生雜憶,不求齊全,隨筆而為,盡得風流。書名原擬「李敖八十風流錄」,嫌八十太老氣,改為「李敖風流自傳」。唐朝詩人寫「文采風流今尚存」,是吹牛的,實際上,他們的「文采風流」,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實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視昔」...
宋朝有個風俗,叫「八十孩兒」。小孩出生,為了盼他長壽,在他腦門子上寫「八十」兩個大紅字,以討吉利。現在我真的活到八十歲了,腦門子上要寫,得寫「八百」才過癮了。看來「八百」是活不到了,但寫幾百條浮生雜憶是沒問題的,於是我花四十天寫它幾百條。因為是浮生雜憶,不求齊全,隨筆而為,盡得風流。書名原擬「李敖八十風流錄」,嫌八十太老氣,改為「李敖風流自傳」。唐朝詩人寫「文采風流今尚存」,是吹牛的,實際上,他們的「文采風流」,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實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視昔」...
»看全部
目錄
「李敖風流自傳」破題 一
「李敖風流自傳」凡例 三
一 兩位老太太 一
二 時——一九三五 一
三 地——我住在中國 二
四 人——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 三
五 鬼——日本鬼子 四
六 原來我就是上帝 五
七 上帝管兩頭,我管中間 六
八 視——息眼之所 七
九 聲——日本女人蝴蝶夫人 八
一○ 色——日本女人與叫床 九
一一 A片與夢幻 九
一二 書房之被 一○
一三 「虛擬的十七歲」 一一
一四 我寫「虛擬的十七歲」 一三
一五 願——我願我是馴獸師 一五
一六 壽——一百歲前的八十感言 一七
...
「李敖風流自傳」凡例 三
一 兩位老太太 一
二 時——一九三五 一
三 地——我住在中國 二
四 人——曾經走過這樣一位血肉之軀 三
五 鬼——日本鬼子 四
六 原來我就是上帝 五
七 上帝管兩頭,我管中間 六
八 視——息眼之所 七
九 聲——日本女人蝴蝶夫人 八
一○ 色——日本女人與叫床 九
一一 A片與夢幻 九
一二 書房之被 一○
一三 「虛擬的十七歲」 一一
一四 我寫「虛擬的十七歲」 一三
一五 願——我願我是馴獸師 一五
一六 壽——一百歲前的八十感言 一七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敖
- 出版社: 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4-23 ISBN/ISSN:978957510141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776頁 開數:15*21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社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