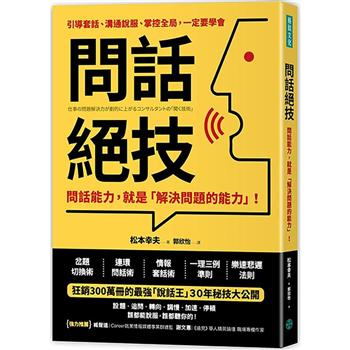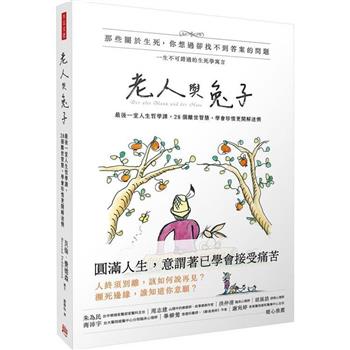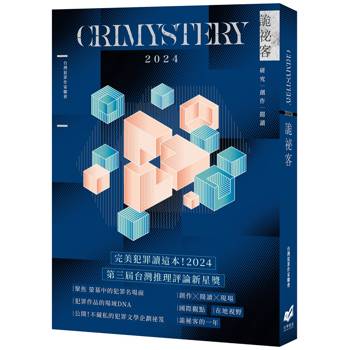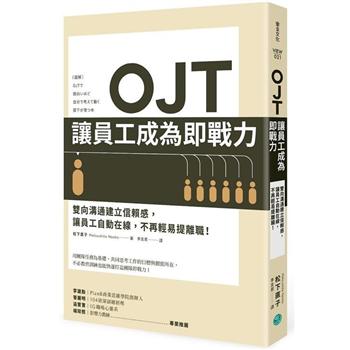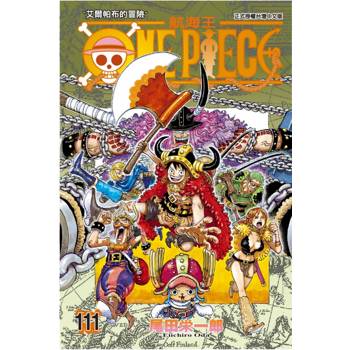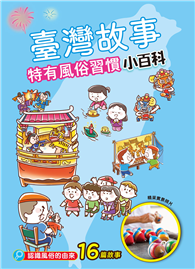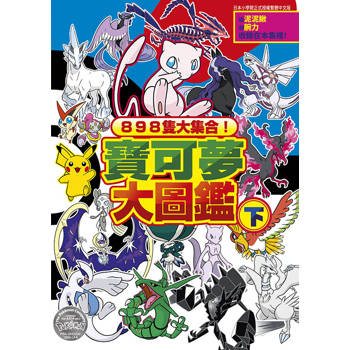再版序
司法獨立是所有民主體制所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包括大法官在內所有的一般法院職司審判的法官,都應該不受政治權力,以及政黨的權力誘惑。大法官作為最終有權解釋者,在制度上僅能期盼大法官有自律及良知。
不過,學者時期對黨產議題有特定立場的部分現任大法官,被黨產條例的受害者(如救國團、婦聯會)聲請迴避,大法官只以這些關係人非聲請人,因當事人不適格,故程序上駁回,另說明釋憲案結果對這些被聲請迴避之大法官本身無利害關係,故不能認為有偏頗之虞。然而,迴避制度要避免的不只是心有定見的「偏頗」,而是只要有偏頗的高度可能性(「之虞」),就足以摧毀社會對大法官的信任。
更可惜者,學者時期對黨產議題讜論侃侃的部分大法官們,於憲法法庭言詞辯論過程中似乎已心有定見而未發一語,未能形成憲法對話。在此情況下,大法官已失去司法中立及超然立場,作出全部合憲解釋是可預期之結果,雖不意外,但令人悲嘆,前大法官湯德宗甚至以「當大法官作為『憲法守護者』的神話破滅」評價,可謂恰如其分。
值得欣慰的是,本案的釋憲聲請,史無前例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後共有八位法官,基於對於憲法合理的確信,秉持「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挺身捍衛法治憲政,提出釋憲聲請。其中,更指出:「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由黨產會主動進行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等同不問原權利人之意願,剝奪其依司法程序請求救濟之訴訟權。……黨產會以聽證程序,取代法院以司法程序判斷決定財產權之變動,不僅非功能適當之機關,且已侵犯司法權核心,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大法官竟然在解釋中認為「相關人仍得依相關訴訟途徑尋求救濟,並未排除司法之審查……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犧牲了法治國家之下人民財產強制移轉之「法官保留」,實難以置信係出自於以捍衛基本權保障為職志的「大法官」之口!
理由書認黨產條例所規定「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不違反明確性原則,在我國法制上尚非陌生,實質控制或類似用語在彰顯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存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且已具體明定實質控制之判斷面向,故從文義、目的與體系關聯性觀之,其意義應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在司法審查上,則指出:「實質控制之涵義最終亦可由法院依一般法律解釋之方法予以確認。」闡明行政法院可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來確認是否具有「實質控制」;另也強調對政黨是否實質控制人民團體,法院可從「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來判斷政黨與該人民團體間是否具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並審查「政黨以捐助、出資或其他方式實質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為該組織等所充分知悉」。
面對公益性「曾為附隨組織」如救國團、婦聯會、救總等在訴訟中,解釋黨產條例援用公司法領域之「實質控制」要件發生困難時,期許現在承審的行政法院法官,可秉持其一般法律解釋及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以守護憲法及保障人民權利的高度,就具體個案情形作出合法公義之判斷。
本人曾擔任救國團、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之黨產會聽證會鑑定人,又應大法官邀請,擔任釋字第793號解釋憲法法庭鑑定人,前後發表之鑑定意見書均未見黨產會在處分書中予以辯駁,在大法官解釋理由書亦未見說明。本書再版,將原書內容略為修改、增補(如第二章增補第五節「東德處理黨產:從形式意義法治國到實質意義法治國之歷史背景」,詳細說明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之判斷標準),列為第一編;並將掛在司法院網站之鑑定意見書,列為第二編;就釋字第793號解釋之評釋,列為第三編。於第二編、第三編更明白指出黨產條例立法理由錯誤引用德國「實質意義法治國」,曲解威權時期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均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得下命返還、追徵;在德國是因為兩德統一,西德評價當時受共黨統治的東德,均是「形式意義法治國」(惡法亦法),而沒有「實質意義法治國」的概念。為了統一後的民主選舉,鞏固政黨政治下之機會平等,統一後德國在兩德統一條約中明訂「實質意義法治國」,甚至是為了保護原東德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只要他們原先取得的財產是符合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該財產皆返還於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保障該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基本權(結社權及政治自由),繼續參與統一後德國之政黨政治活動。所以,「實質意義法治國」與「形式意義法治國」原則並非相互對立衝突,而是相輔相成。
誠如詹森林大法官指出,當立法者及行政機關激情地高擎轉型正義大纛時,大法官接棒揮舞,將造成「打擊過廣而殃及無辜」株連九族之後果。審判獨立在各級法院,有賴各位法官們捍衛及堅持,在個案中具體實現,本書所述之比較法、歷史性觀察,以及各種學理及實務見解之闡述,希冀對相關人員有所助益,並為「校正回歸」我國已被黨產條例歪曲的民主法治,克盡學者良知,略盡棉薄之力。
董保城
於臺北東吳大學寵惠堂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