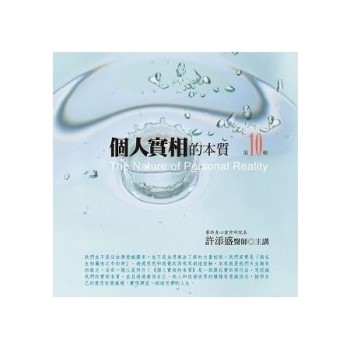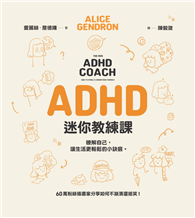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二章 綁架
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昏暗的小屋子裡。
這間小屋子有點特別,好像是倉庫或者儲藏室,因為四面都沒有窗,只有一扇門,而且牆壁全都是金屬製的。
屋子裡有一張鏽跡斑斑的折疊鋼絲床,床邊擺放著一張破破爛爛的圓木桌。
我並沒有躺在那張床上,而是像雜物一樣被扔在了牆角,雙手被麻繩死死地反綁在身後,我用力掙扎了一下,發現完全掙脫不開,不過所幸,雙腿還能自由活動。
我看了下四周,確定旁邊沒有人在監視之後,費力地從地上坐了起來,身體感覺十分虛弱,口乾舌燥四肢無力,頭腦也昏昏沉沉的。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胸前中彈的地方,可是並沒有發現什麼傷口。
我想之前的那一槍,應該是麻醉針。也就是說,我現在是被綁架了?
麻醉尚未失效的大腦在遲緩地轉了一圈之後,才將自己目前的處境做了個總結,可是繼而,又有一連串新的疑問冒了出來。
是誰綁架了我?為什麼要綁架我?綁架我的人,就是把雪洺姐推下樓的人嗎?
--是的,事到如今我已經很肯定,方雪洺,是死於謀殺。
二哥失蹤了,二哥的女友死於非命,而我現在又被人莫名其妙地綁架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
我愣愣地坐在地上發了一會兒呆,等到麻醉效力稍微過去一點,終於,可以蹭著牆壁慢慢站了起來。
我走到那扇緊閉的金屬門前,大喊了一聲:「外面有人嗎?」
可是門外靜悄悄的,沒有任何回應。
我又一連喊了好幾遍,仍然沒有人理我,於是我開始用肩膀撞門,撞得非常用力,整扇金屬門連同門框一起「匡匡」作響,但卻沒有成功撞開。
顯然,門肯定是從外面被反鎖住的,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在把守。
我又喊了幾嗓子,直到確信不會有人來搭理我之後,才不得不安靜了下來。
就這樣,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有人來開了門。
那是一個看上去年紀很輕的大男孩,大約才十八九歲的樣子,長著一張挺斯文的臉,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端著餐盤走進來。
餐盤裡有一塊圓麵包,一杯清水。
我看著他,問:「你們打算把我關到幾時?」
他沒有說話。
我又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抓我?」
他仍是沒有回答,放下餐盤後說了句:「快點吃,半個小時後我來收盤子。」
我冷笑了一聲,道:「我雙手被反綁著要怎麼吃?」
他看看我,居然頭也不回地走掉了。
半個小時後,他再次進來,看到桌上的麵包和清水一點都沒用動過,不禁愣了一下,問:「你為什麼不吃?你不餓嗎?食物裡面沒有下毒。」
「廢話,我知道,如果你們想要弄死我的話,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現在。」我說著,轉頭用下巴指了指身後的手,道:「你不幫我解開我怎麼吃?」
他怔了怔,似所有動搖,不過想了想之後還是沒有行動。
這個人,一看就是個沒什麼用處的小嘍囉,幫著打打下手的角色,他的任務大概只是要給我送飯,以保證我不會餓死吧。
我看著他,說:「其實你可以先幫我解開,等我吃完再綁回去不就好了麼?」
他猶豫著,看了看我。
我哼笑著說:「這裡是你們的地盤,你有什麼好擔心的?倒是如果我就這樣活活餓死或者渴死,你會被懲罰的吧?」
他遲疑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輕聲說了句:「好吧,反正就算你從這間屋子裡跑出去也是逃不掉的。」
說完,他便來替我解繩子,而就在繩子鬆開的剎那,我忽然飛起一腳踹在了他的胸口,他反應不及,沒有躲掉,整個人向後撞在牆壁上。
我趕緊奪路而逃,迅速衝向虛掩的房門,就在跑出屋子的那一刻,我回頭看了他一眼,卻發現那個人並沒有追上來,只是坐在地上用一種微妙的眼神看著我,那樣子就彷彿在說--沒用的,你是跑不掉的。
我不禁覺得奇怪,卻也沒時間多想。
衝出房門,我看到眼前是一條狹窄的走廊,走廊的盡頭處有一架向上的旋轉鐵梯。
我忽然間意識到,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好像是在地下?
於是我拼了命地跑向鐵梯,「登登登」地踩著臺階衝上去。
一瞬間,耀眼的陽光,清新的空氣,微醺的暖風,全都撲面而來。
我反手擋了一下刺眼的光芒,再放眼望出去,卻一下子懵住了。
現在,我終於明白那個人為什麼沒有追上來,也終於明白他所說的「就算跑出屋子也是逃不掉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環繞在我四周的,竟是一片無邊無際的蔚藍海洋,而我,就這樣傻呆呆地站在一艘遊艇的甲板上,擺著一臉震驚過度的表情,愕然地望著眼前那層層疊疊向我湧來的浪潮。
靠!有沒有搞錯!我居然被綁架到了一艘船上?我現在是在哪裡?太平洋嗎?還是地中海?
我簡直欲哭無淚,上天無路遁地無門,該怎麼辦才好?
我走到圍欄邊,低頭往下看了看,腦中天真地閃過一個念頭--如果這艘船起航還沒有超過兩個小時的話,興許,憑著我的水性和體力還有可能游回去?
如此想著,我不要命地一腳跨上了欄杆。
就在這時,身後突然響起一個懶洋洋的聲音。
「海裡有鯊魚喔,你是打算當牠們的免費午餐嗎?」
我一怔,猛然回頭,卻看到在靠甲板另一側的船舷上居然掛著一張晃晃悠悠的吊床,吊床上躺著一個約摸二十五六歲的年輕男人,那個男人正一邊怡然自得地翹腳曬著太陽,一邊轉眸對我揚了下嘴角。
我皺著眉,立刻如背毛倒豎的貓一樣,渾身戒備地看著他。
「不過,瞧你這副營養不良沒幾斤骨肉的樣子,大概給鯊魚剔個牙縫都不夠吧?」男人笑嘻嘻地調侃著,突然一個翻身,動作極為靈巧地從吊床上一躍而下。
「你才他媽的營養不良!」
我白了他一眼,轉回身,一條腿還跨在圍欄外,低頭看了看那暗濤洶湧的深藍色海面,一咬牙,剛準備跳下去,卻突然被人一把扯住了胳臂。
「嘖嘖,到底是卓家的三少爺,脾氣就跟那老頭子一樣倔,我都說了這裡的海域有鯊魚,你就這樣跳下去肯定不出十分鐘就會被吃掉的。」
聽到這話,我不由地心裡暗暗一驚,這個人居然……認識我父親?頓時,我不禁對眼前的男人又多了三分厭惡。
可他卻一直在望著我笑,笑得我心頭燃起了一把無名怒火。
不過說實話,這個男人其實長得倒是挺帥,臉廓棱角分明,眉眼深邃鼻梁挺直,目測身高至少在一百九十公分,很隨意地穿了條鬆鬆垮垮的迷彩褲,下面是一雙軍靴,上身則是一件很悶騷的黑色背心,露出了手臂和肩膀上線條流暢而緊實的小麥色肌肉,如果那一頭凌亂的黑髮能夠稍微再收拾得乾淨整齊一點,相信走在大學校園裡肯定會引起那些花癡女生們的尖叫和追捧。
只不過有點可惜,他笑起來的樣子太過邪氣,給人一種很「不良」的感覺。
望著那一臉痞痞的壞笑,我用力掙了一下手臂,卻沒有從他的掌心裡掙脫出來,於是只能忿忿地瞪了他一眼,低喝了聲:「你他媽的給我放手!」
「咦,我聽說卓家的家教很嚴,沒想到你居然滿口髒話?」
男人呵呵笑了起來,笑得十分欠揍,卻仍然沒有半點要放手的意思。
我頓時火冒三丈,突然抬起左手一拳猛擊過去。
男人卻仍然在笑,面不改色,只是稍稍一側頭,便很輕易地避開了我的全力一擊。
我趕緊收回拳峰,彎起胳臂,用堅硬的手肘又往他腹部用力一撞。
他終於鬆了手,向後輕輕一躍,仍舊是躲開了,我緊追著不放,衝上兩步,一個轉身迴旋踢,一腳踹上了他的胸口,卻沒想到,居然被他一掌接住了。
「唷,真有兩下子嘛,看不出來啊,居然還會跆拳道?照剛才那一記漂亮的迴旋踢來看,我猜,應該有黑帶級別了吧?」
男人輕佻地吹了聲口哨,捏著我的腳踝,笑意漸濃。
我咬著牙,突然一個伏地挺身,撐著地面,用另一隻腳踢開了他的手,緊接著又是一記低掃腿,男人向後仰了一下,跳開了,我又接連兩個力道兇狠的側踢,將他逼至圍欄處,他的身後已經無路可退。
我冷笑了一聲,豁然抬腿,對準那張流氓似的笑臉用力踹了過去。
我倒要看看,被我一腳踢中臉面他是不是還能笑得出來。
可是沒想到,就在我抬腿的瞬間,他突然往我下腹伸手過來。
我不禁疑惑地低頭一看,卻看到……看到這傢伙竟然在解我的皮帶扣!
靠!他想要幹什麼?
而就在我的驚疑之中,剎那間前襟拉鍊一鬆,牛仔褲往下一沉,我趕緊收腿,一把提住了掉落的褲子,可是整個人卻因此失去了平衡,狼狽地一屁股跌坐在地。
「下流!」我氣急敗壞地瞪著他,一邊趕緊將牛仔褲的拉鍊皮帶全都扣回去。
男人哈哈大笑了起來,說:「你呀,基本功倒是挺扎實,可惜一招一式太過死板,缺乏臨場經驗,對付那些蝦兵蟹將還行,但是遇到我這種高手就要吃虧了。」
「哈!高手?」我被他氣到不怒反笑,冷哼著說,「只不過是用了些卑鄙無恥的下三濫手段而已,就自詡為高手?臉皮真是厚到豬都要發笑!」
「哦?豬是怎麼笑的?你笑給我看看。」
男人看著我,戲謔地挑了下眉梢。
這種人,我根本不想跟他浪費口水,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之後,便不再搭理。
這時,甲板上走來五六個人,我回過頭,一眼就看到了那個黑西裝。
這個人,正是之前在雪洺姐墜樓的命案現場看到過的男人。
就是他,殺了雪洺姐嗎?
我皺了皺眉,未及細想,就看到那個黑西裝已經氣勢洶洶地走了過來,伸手想要抓我,我一個閃身避開了,黑西裝再次撲過來,我被迫與他過了幾招,但卻立即發現,自己與專業級保鏢的實力實在是相去甚遠,幾乎不到一分鐘,我便被打趴了下來,連續挨了幾記重拳的腹部泛起一陣陣胃酸。我撐著地面,吐出一口混著血絲的唾沫,搖搖晃晃地想要站起來,卻又被對方狠狠一腳踹了下去。
黑西裝很粗暴地扯住我的頭髮,把我拖到了船艙邊,用力按在了艙壁上。
「是不是你……把方雪洺……推下樓的?」我喘息著,斜眼看著他,四肢百骸疼得無法動彈。
黑西裝沒有回答,卻是轉身挪開了一個位置,從後面走上來另一個人。
那是個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他從閃著寒光的玻璃鏡片後看著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很直截了當地問了句:「卓少天在哪裡?」
我愣了一下,隨即呵呵笑了兩聲,道:「這個問題,我還想問你們呢。」
「別跟我耍花腔,說,卓少天在哪裡?他有沒有跟你聯絡過?」
隨著這兩句話問出來的同時,一管漆黑冷硬的方形槍口抵上了我的額頭。
我心口猛然一跳。
這已經是我在短時間內第二次被人用槍指著了,二哥到底是惹上了什麼人?
冷汗,從額頭滾落了下來。
我咬著牙,硬撐著沒有表現出害怕的樣子,很平靜地回答說:「就算你現在一槍打死我也沒用,我真的不知道二哥在哪裡。」
「哦?是麼?」
中年男人微微湊近了點,那雙如鷹勾般銳利的眸子筆直地注視著我的眼睛,彷彿是要想從中讀出我說的究竟是真話還是假話。
沉默了片刻,他又問:「那麼,卓少天給你的東西在哪裡?」
我豁然吃了一驚。
他為什麼會知道二哥給過我東西?那個深夜「快遞」來的包裹,除了雪洺姐之外,我沒有告訴過別人……
難道、難道是雪洺姐……不,不會的,雪洺姐不會出賣我的……
我立刻否認了這個想法。
「卓少天給你的那個東西,你家裡沒有,應該是已經藏起來了吧?」
「你們去過我家?擅闖民宅是犯法的!」我憤怒地瞪著他。
不過這些人,既然隨身帶著槍,恐怕也不會在乎法律。
中年男人用槍口抬起了我的下巴,頓了頓,又緩緩問道:「你把那東西藏在什麼地方了?或者還是,交給了什麼人?」
我看著他,沉默著沒有做聲。
一秒,兩秒,三秒,突然,「砰」地一聲巨響。
子彈從槍膛裡射出,打在了我臉側的金屬艙壁上。
我嚇得渾身一震,耳鼓膜「嗡」地一聲,近距離的爆響使得我一下子失去了聽覺,飛濺出來的子彈碎片從臉頰擦過,火辣辣地疼。
白色硝煙在空氣裡漸漸瀰漫開來。
我微微發顫地看著他,背後的衣服已經被冷汗濕透了。
等到聽覺稍微恢復一點,我聽到中年男人說了句:「看清楚了嗎,這次可不是麻醉槍,剛才那顆子彈,會要了你的小命,說,東西在哪裡?」
我很用力地咬住嘴唇,已經沒有辦法克制住內心的恐懼。
我渾身都在發抖,但是仍然堅持著說了句:「我不知道。」
我不能把樂辰說出來!絕對不能!死也不能!我在心底裡暗暗發著毒誓,繼而,卻看到那管槍口抵在了我右腿的膝蓋上。
「你如果再回答我說不知道,那麼這條腿就廢了。」
「哢擦」一聲,子彈上了膛。
中年男人滿臉狠戾地看著我:「最後再問一遍,東西,在哪裡?」
我不敢假想後面會發生的事情,只能驚恐地閉上了眼睛,手心裡捏著冷汗,沉默了幾秒,輕聲說了句:「我不知道。」
話音甫落,「砰」地一聲槍響。
我突然膝蓋一軟,整個人跌坐了下來,可是卻意外地沒有感覺到任何疼痛。
子彈居然打偏了,我腳邊的甲板上多了一個冒著硝煙的黑色小孔。
我顫慄著睜開雙眼,緩緩抬眸,卻看到中年男人手裡的槍已經被之前那個厚臉皮流氓男穩穩地按住了,他痞笑著看了我一眼,回過頭,說:「喬四爺,您在這一行裡也算是個有頭有臉響噹噹的人物了,何必這樣為難一個孩子?」
喬四爺?
我不禁愣了一下,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這才忽然發現,在甲板的另一頭,站著一個骨瘦如柴極其矮小的駝背小老頭,穿了一身毫不起眼的灰布衫,手裡拄著根龍頭拐杖,而他臉上那層層疊疊的皺紋,簡直令樂辰家的沙皮狗都甘拜下風。
靠,這老頭子幾歲?都老成這樣了還跑出來坐遊艇?
不難顯然,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老頭,地位肯定在我的想像之上,因為至少甲板上的這些人,看上去都得聽命於他。
只見小老頭雙手搭著拐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用一種沙啞得快要斷氣似的聲音緩緩說道:「蕭然,我花了那麼多錢請你來,不是讓你來管閒事的。」
原來這個卑鄙下流無恥的厚臉皮流氓男叫蕭然,真是可惜了這個詩情畫意的好名字。
蕭然卻仍舊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樣,說:「喬四爺,您這話可就不對了,我這哪裡是管閒事,您想想,現在我們這些人裡,唯一見過那東西的人,就是這個孩子,而那東西又是能找到卓少天的唯一線索,您現在如果一個不小心把這孩子弄死了,那就等於是線索全斷了,還不如留著他慢慢找線索,您說對不對?」
我忽然皺了皺眉。
那東西是能找到二哥的唯一線索……同樣的話,雪洺姐也說過,可是我想來想去卻始終想不明白,那隻斷手和二哥的下落到底有什麼聯繫?
聽到蕭然這樣說,那個「喬四爺」不再說話了,在甲板上佇立了片刻,隨後便在旁人的攙扶下慢慢轉身走下了艙房。
蕭然回頭看看我,伸出手,笑著問:「還站得起來嗎?」
「別假惺惺的,滾遠點!」
「啪」地一聲,我毫不客氣地打掉了他的手,自己扶著艙壁,咬牙站了起來,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我聽到蕭然似乎帶著一種欣賞的語氣說了句:「不錯,還挺有膽識的。」
我愣了一下,抬起頭,卻看到他輕輕一揚嘴角,笑得非常邪氣。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闇獵者(1):荒漠迷蹤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58 |
幻奇冒險 |
$ 158 |
科幻/奇幻小說 |
$ 170 |
奇幻/科幻 |
$ 170 |
中文書 |
$ 180 |
文學作品 |
$ 323 |
文史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闇獵者(1):荒漠迷蹤
繼《怪物刑警》之後,四隻腳+Leila強強聯合新作!
熱血炸毛小弟槓上流氓盜獵師,驚險刺激的尋兇(?)兄(?)之旅,出發!
別人的炸毛就是他的快樂
雙面獵人與單純獵物的心機攻防
斷手,血衣,沙子……一切,從那個凌晨兩點半,
考古狂二哥叫人快遞來的包裹開始,
而他,彷彿就此人間蒸發。
為了找到二哥,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必須和綁架我的組織合作,
而那個以整我為樂的痞子盜獵師,卻與二哥有過交集?!
各懷鬼胎的一行人深入沙漠腹地──烏邙,尋找蛛絲馬跡,
然而,令人膽寒的TA們,卻讓我們深刻的了解到──
這個世界上,從來都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片荒蕪的大地上,我們究竟是獵人?還是獵物?
人物介紹
卓靜流
性別:男
年齡:22歲 身高:181cm
身分:被迫牽扯進一系列神祕事件的倒楣主角。
性格:正直善良,易炸毛。
蕭然
性別:男
年齡:25歲 身高:193cm
身分:盜獵師
性格:亦正亦邪、玩世不恭
卓少天:男,考古學家,卓靜流的二哥。
方雪洺:女,考古學家,卓少天的女友。
卓少安:男,卓氏企業繼承人,卓靜流的大哥。
樂辰:男,卓靜流的死黨。
河邊:男,喬四爺的手下。
黑西裝:男,喬四爺的手下。
胡胖球:男,喬四爺的手下。
青青:女,沙漠旅店老闆的小女兒。
周文旭:男,考古學家,卓少天的同事。
作者簡介:
四隻腳
家裡養著十二隻腳(三隻雪納瑞)的超級宅人一枚。
喜歡探究各種各樣的神祕未知事物,喜歡異想天開,喜歡做白日夢。
喜歡用文字來記述自己的突發奇想。
喜歡編織怪獸+美男的故事。
章節試閱
第二章 綁架
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昏暗的小屋子裡。
這間小屋子有點特別,好像是倉庫或者儲藏室,因為四面都沒有窗,只有一扇門,而且牆壁全都是金屬製的。
屋子裡有一張鏽跡斑斑的折疊鋼絲床,床邊擺放著一張破破爛爛的圓木桌。
我並沒有躺在那張床上,而是像雜物一樣被扔在了牆角,雙手被麻繩死死地反綁在身後,我用力掙扎了一下,發現完全掙脫不開,不過所幸,雙腿還能自由活動。
我看了下四周,確定旁邊沒有人在監視之後,費力地從地上坐了起來,身體感覺十分虛弱,口乾舌燥四肢無力,頭腦也昏昏沉沉的。
我低...
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昏暗的小屋子裡。
這間小屋子有點特別,好像是倉庫或者儲藏室,因為四面都沒有窗,只有一扇門,而且牆壁全都是金屬製的。
屋子裡有一張鏽跡斑斑的折疊鋼絲床,床邊擺放著一張破破爛爛的圓木桌。
我並沒有躺在那張床上,而是像雜物一樣被扔在了牆角,雙手被麻繩死死地反綁在身後,我用力掙扎了一下,發現完全掙脫不開,不過所幸,雙腿還能自由活動。
我看了下四周,確定旁邊沒有人在監視之後,費力地從地上坐了起來,身體感覺十分虛弱,口乾舌燥四肢無力,頭腦也昏昏沉沉的。
我低...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深夜包裹
第二章 綁架
第三章 駢涼古邑
第四章 TA們來了
第五章 消失的古城
第六章 來自荒漠的求救
第七章 鹽殼之地
第八章 迷失
第九章 墳墓
第十章 孩子
第十一章 夜襲
第十二章 沙民
後記
第二章 綁架
第三章 駢涼古邑
第四章 TA們來了
第五章 消失的古城
第六章 來自荒漠的求救
第七章 鹽殼之地
第八章 迷失
第九章 墳墓
第十章 孩子
第十一章 夜襲
第十二章 沙民
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四隻腳
- 出版社: 長鴻出版社(小說) 出版日期:2015-03-31 ISBN/ISSN:978957516629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