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維城四紀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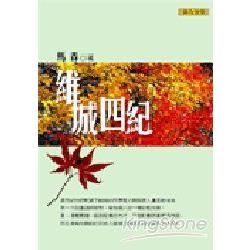 |
維城四紀 作者:馬森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3-19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8 |
中文現代文學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現代散文 |
$ 180 |
現代散文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讀著〈秋日紀事〉平常而不乏情趣理趣的文字,深深感覺到散文在這冷暖不定、變化無常的世間,所起的親切平靜的作用,讀之如晤如水之交的故人,一文而引起數十年傳奇或不傳奇的回憶,乃有很大的滿足與欣喜。-黃維樑 《維城四紀》收錄〈秋日紀事〉、〈冬日紀病〉、〈春日紀遊〉、〈夏日紀趣〉等篇章,非但記錄了加拿大維多利亞的四季風光,也敘述作者重返維城後第一年的遭遇與感想。在閒話家常,描繪親情、友情中,亦不時蘊涵哲思。 馬森歷經無數遷居,深諳知足常樂的道理,在他融會眾多人緣、地緣機遇的作品中,呈現無窮的機趣。
作者簡介:
馬森著名戲劇家與小說家。 一九三二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曾於濟南、北京、淡水、宜蘭等地就讀中學。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一九六一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IDHEC)研究電影與戲劇,並在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ersityofBritishColumbia)博士學位。 先後曾執教於台灣師大、巴黎語言研究所、墨西哥學院、加拿大亞伯達及維多利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私立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校,並曾一度兼任《聯合文學》總編輯。 著有學術論著《馬森戲劇論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當代戲劇》、《東方戲劇?西方戲劇》、《戲劇──造夢的藝術》、《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與友人合著)、《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劇作有《腳色》、《我們都是金光黨?美麗華酒女救風塵》等,小說有《夜遊》、《生活在瓶中》、《孤絕》、《海鷗》、《巴黎的故事》、《北京的故事》、《M的旅程》等,散文有《愛的學習》、《墨西哥憶往》、《大陸啊!我的困惑》、《追尋時光的根》、《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等,文化評論有《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文學的魅惑》等四十餘部。
- 作者: 馬森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3-19 ISBN/ISSN:9789575226817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