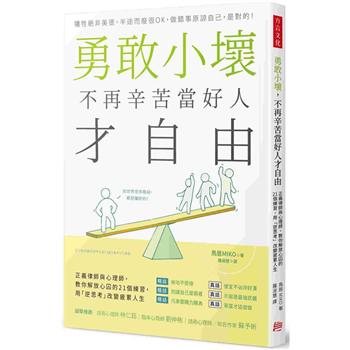華麗的冒險∕李昂
童小吃過一樣東西,至今仍令我念念不忘,因為往後不論在台灣、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僑社、更不用講在歐美華人社區,都不曾再吃過。
東西其實簡單,早年的鹿港,由小攤販手推著車沿街叫賣,燒著炭火中等的大鍋裡,一鍋咕咕冒泡的滾燙濃稠糖汁,餵養著一個又一個白又肥茶杯口大的扁圓麻糬。說定要幾只,攤販從熱糖汁撈起煮得甜膩軟肥的麻糬,在花生或芝麻粉裡一滾,便成。
現在可以明白,舊時手工捶打出來的麻糬方如此Q,糖汁花生或芝麻粉古法照規矩煉製,原汁原味香甜好吃一定不在話下。
當然更可以說,念念不忘的是當中的懷舊與鄉愁。每個人基本上都有一兩樣兒時的美食記憶、「媽媽的味道」,大都永難再重複回味、不能完整再現,方最為珍貴。我們也都知道,即便時光倒流真能重吃到那東西,多半也不是那麼好吃。
事實上,我們的美味記憶不斷的更新、甚且竄改──特別是當不再能品嚐到、不再能擁有時。
是的,更新、竄改,不只在我們的美味關係裡,在我們個人的人生裡,甚且在大的歷史敘述裡。只是在過去,我都還不知道這更新、竄改,可以如此輕易。
那是我開始使用電腦後。
一定要非常感謝同是故鄉人「宏?」施振榮先生,推出可以在電腦螢幕上手寫的「平版電腦」,並送我一部,解決了我一想到要打字輸入便腦中一片空白、無從使用電腦的困境。
是的、是的,《鴛鴦春膳》是我用電腦寫的第一部小說,還是個長篇小說。
使用電腦於我最大的感動是,可以如此方便更新,甚至竄改。
《鴛鴦春膳》寫作的時間更是長達六年,包括一開始全世界性的追逐美食尋找材料、當中停下來寫了《花間迷情》。單篇之間也陸續有機會在報紙、雜誌發表,時間的流長使得有些修改成為必需。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幾年台灣政局的變化。
我將部分寫好發表的篇章再十分關鍵性的作了修改,我成了一個「竄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以後,也會因不同地區的出版,有不同的版本。
更新、竄改的作品用來書寫同樣更新、竄改的美食記憶,誰又能說不也是種極佳組合。然作成這幾個不同版本的背後,豈只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值得特別提出的另個「竄改」,是本書中關於飲、食的書寫。由於寫的是小說,關係到小說虛構的個別經驗與記憶,自然不能死硬的用一般食物的歷史、典故、作法來加以論斷所謂年代、考證、對錯。
要作這類功夫,針對的應是其他類別的飲食寫作吧!在此特別提出,以免有人「小題大作」。
這一切的基本,最始初並非來自那麼實質的飲、食,或與食物相關聯的高深文化、文明,也不是因此顯而易見的飲、食與政治、社會、階級、性別等等的探索。
而無寧是一種十分羅曼蒂克的憧憬。
是啊!比如深愛香檳的我,聽聞仍有不少上個世紀初的老香檳,流落在俄羅斯現今的高官富豪大亨手中。這些原來自舊日貴族、紅色政府官僚收藏的香檳,像王謝堂前的燕子,飛入的雖非尋常的百姓家,在新貴甚且是黑社會大亨的手中,也無寧十分傳奇與滄桑。
就坐趟飛機到莫斯科,可以不為紅場上壯烈的革命,也不為俄羅斯政經的變革,只是為了喝那我最鍾愛的香檳,以及,當中可以有的浪漫情懷。
是這些撼動了我。
又或者,坐在由舊日宮殿改裝的米其林三星餐廳,香檳、紅、白酒、甜酒、白蘭地交錯的酩酊中,恍惚之間,總願意相信,自己有一世是那公主、貴婦、甚且只是個小僕從,曾經在此用餐,才會有那麼強烈的似曾相識。
是這些讓我不惜全然投入、以身相許於飲食。
然「吃」基本上是一件十分殘忍的事:我們吃掉的事實上是我們能掌控、或巧取豪奪來的別的生命──動物自然是有知覺,但誰知道植物會不會流淚?
在「吃」這件生∕死最極致殘忍的事上,我們還要講究美食、講究餐桌禮儀、氣氛情調,甚且無限上綱成最高深的文化、文明的表徵。事實上,呈現出的不正是慾望、制約、禁忌與消失。
中年作家寫作飲食,更能體會人生不正是五味雜陳?而「五味雜陳」交相混雜,不就是飲食!
美食,或者更簡單的說,對飲食的追逐,也協助我度過前陣子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刻,並開展出新的人生體悟。
要感謝的首先是我的父親,以今日的標準,父親稱不上是個美食家,了不起與我一樣只能當個「愛吃鬼」。但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女時代,甚且之後來到台北,因著父親的愛吃,我們有過一段十分奇特的「美食」時光。
也使我有能力書寫這部小說,並將它獻給父親。
原寄望會只是個單純而美好的飲食小說,好作為對父親的紀念。寫成後並非如此,也只有希望父親在天之靈能接受吧!
當然還要感謝這多年來在美食、美酒上提攜我的諸多前輩、老師、朋友。在此就不一一列名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