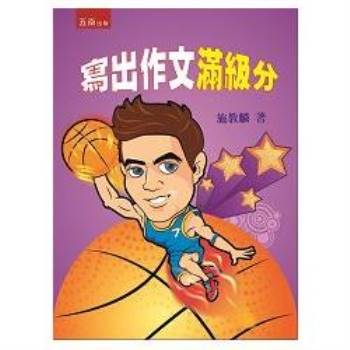Ⅰ︰ 橡膠園
1.洞
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日漸衰退的視力,還是像一根倒刺那樣朝著錯誤方向伸展的記憶力,釀成了米安的景況。
她的視線就這樣停定在某一點之上,像是被一根看不見的釘子牢牢地拴著,即使日光暗淡,無數身影在她眼前掠過,蚊子在她的附近繚繞,她始終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沙發上,眼神呆滯地盯著前方。令人們感到不安的,並不是她一成不變的姿態就像一臺沒上發條的時鐘,而是出現在她臉上像漣漪般不斷擴大的笑意,漸漸蔓延至臉的每一部分。她的女兒看見她張得老大的嘴巴,露出缺了許多牙齒的口腔,就像一個對世界所知太少的智障兒,他們便發現自己的母親,距離自己非常遙遠。
「老人就是這樣子。」她那年長的女兒終於說出了一句話,緩和餐桌上凝滯而尷尬的氣氛。
自那夜開始,米安再也沒有跟他們一起用餐,沒有人會知道,她那麼專注於眼前的一切,以致忘掉了身體最基本的需要。她沒法向女兒清晰地闡明眼前的景像,要是她們能活到她那種年紀,或許便會有相似的體悟,然而她們是否理解,其實並非她所關注的事。最初,那只是一個黑色的小圓點,彷彿依附在她瞳孔的四周,隨著她的視線在不同的物件上流動,那圓點的範圍漸漸擴大。那天下午,她從午睡的夢裡醒來,面前事物的線條便異常分明,她以為自己仍然身處在一個頑固的夢裡,因為很久以來,她一直活在模糊不清的世界,甚至沒法辨別女兒的臉,只是憑藉他們的聲音和氣息,呼喚不同的名字。可是當她睜開眼睛,便看見黝黑的石洞,洞口傳來微冷的風,石塊上細緻的紋理,在她的眼中,比皺紋來得更張狂。有一個面目跟她相仿的女子把她抱在懷裡,她感到女子的身體非常溫暖,彷彿她根本就是那女子身體的一部分。那女子看著洞口以外很遠的地方對她說︰「留在裡面,別走。」然後她被安置在狹小的洞裡,她的手腳並沒有活動的餘裕,可是當她的耳根緊貼在冰冷而粗糙的石塊上,便聽到一種靜謐。
米安幾乎遺忘了那女子是她的母親,甚至想不起她的臉容,唯有那石洞深沉而安穩的黑暗,經常毫無先兆地侵擾她,譬如說,在她清洗一大籃子衣服、孩子嚎哭不休,或挽著許多蔬果和肉類,而面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才會看見家裡的木門時,那洞穴都彷彿再次出現在她身旁,她總是像在壁櫥內發現螞蟻那樣,迅速地把它從紊亂的腦子裡驅趕。
可是在那個昏睡過後的下午,她躺在沙發上,任由石洞的影子把她完全籠罩。她能肯定那並非衰老帶來的疲憊,而是在睜開眼睛的瞬間,忽然感到以往那種驅逐的姿態,就像田間的稻草人那麼徒勞無功,而懊悔的感覺已經滿溢至令她無從迴避的程度,她乾脆讓它湧出來,浸沒了她的鼻子和眼睛。
米安常常懷疑記憶中最初的時光是否存在,正如她總是認為自己的出生地已經徹底地消失,即使它在地圖上仍然占據著相同的位置。她愈來愈肯定,錯誤源於她最後離開了那石洞。
她記得透過石洞陰涼的牆壁,會聽到鞭炮頻繁的爆炸聲,聲音彷彿帶著齒輪,在她的頭顱拖曳出許多裂縫。以往,人們總是被鞭炮吸引而紛紛上前圍繞著它,直至它散落成一堆紅色的灰燼。但那個奇怪的夜裡,米安發現人們的臉上凝結了一層薄膜般的陰暗,就像看見屍體時會出現的神情。
那是一個起始,她原來熟知的世界,逐漸分裂成許多各不相干的部分。
不久以後,她知道人們早已洞悉,那個晚上從沒有出現鞭炮,只是軍隊的槍和空投的炸藥,轟掉了許多途人的腿、手臂、半截身體,或頭顱。因此,當他們再次聽到那種熟悉的聲音,便會跑到屋外,尋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米安曾經認為,那裡的每一個人,包括她的父母、哥哥、姊姊、伯父和鄰居,都找到各自的石洞,屈曲身體坐在那裡。直至掩蓋洞穴的石塊被推開,他們就像她再次看見母親憔悴的眼睛那樣,發現微亮的晨光,鋪展在他們的身前。
實在,除了她以外,沒有人能找到足以藏身的洞穴,那裡並不缺乏塌掉的樹木或溝坑,只是無論他們如何費盡力氣,也無法把已經完全成熟的身體摺疊起來塞進任何一個凹陷的位置。他們只能跑到屋子後方的丘陵,俯伏身子,把自己隱沒在低矮的灌木叢之中。轟炸的聲音有時接近得似乎在他們腦袋掠過,有時好像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房子裡,遠處時而升起亮麗的火焰。米安的母親便感到自己的身子輕得可以飄起來,好幾次,她以為自己已經碎成了一堆粉末,在空中浮蕩,可是火光暫時熄滅了以後,她又感到自己正緊緊地捏著幾根濡濕的青草。
米安的兄長米田感到地面搖撼得非常厲害,因而不得不把頭部深入自己的兩腿之間,直至骨頭格格作響。爆炸的聲音靜止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米安的姊姊米里把自己的身子直起來,看見發白的天空,嗅到空氣中硝煙的氣味,使她的眼睛異常乾澀,除了微微地擺動的野草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散落在她身旁不遠處有幾個緊縮著的身子,以及僵硬的背部。她從沒有那麼仔細地觀察每個人的背部,有的在顫抖、有的在抽搐,有的直挺挺的像死了那樣。她不忍打擾他們,彷彿他們仍在睡夢之中,直至黃啡色的排泄物從她哥哥米田的背部之下流溢出來,匯成了一道小溪流,直達草堆的另一端。
他們並沒有看見任何穿著軍服的人走近。河流裡沒有漂浮著屍體,水源也沒有沾上血污和腥臭,他們便收到戰事結束的消息。米安的母親始終相信自己強烈的預感。在那裡過活的人,都知道被逮著的人從不會俐落地被殺掉,反而會被炸藥塞進他們的口腔、耳孔、鼻孔或眼睛,然後引爆,或被指揮著在坑道前一字排列,頭部被整齊地割下,以測試刀鋒是否仍然銳利。米安的母親仍然記得在橡膠園工作的陳嫂,帶著四顆紅彤彤的雞蛋,探望生病而無藥可服的她,並低聲在她耳邊說,她家的媳婦剛誕下了兒子,令人煩惱的,不止是軍人愛吃嬰孩的嫰肉,要是給他們看見任何女人,便會設法把槍柄塞進她們的身體裡。
那天,陳嫂帶著四顆染紅了的雞蛋,走遍了整個山頭,逐一探訪她的鄰居以後,又攜著四顆完好無缺的雞蛋回到自己的家,剛好看見母牛順利地產下了小牛。她看著沒有一絲裂縫的蛋殼,臉上綻開了愉快的笑容,暴露了發亮的金牙。那算命的告訴她,不曾破碎的雞蛋和懷孕的牛會帶她逃離厄運。
米安的母親看著陳嫂的身影離去之後,頑強的病很快便痊癒了。她展開了周詳的計畫,一旦看見軍人的身影在窗前掠過,便會逐一弄死兒女。她決定要扭斷他們的脖子,據說脖子是身體上最脆弱的部分。自此,她便時常看著他們的脖子嘆氣,她知道自己的想法總是比實際的情況簡單。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宰雞的經驗裡,她知道自己的力氣拗不過他們,他們的頸骨非常堅固。她的子女總是以為她憂慮戰事,卻從不知道是為了他們的頸項。
轟炸結束以後,米安的母親從山丘回到自己的房子,常常從屋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並且拉上了黑色的窗簾,堅執地守候炮火再次響起的聲音。
她的兒女都抵受不了飢餓,紛紛跑到荒廢的田裡栽種木薯,那些帶毒的植物在肥沃的土壤裡迅速冒起。不久以後,他們便在屋子的角落煮一鍋沸水,把剛剛收割的木薯丟進水裡煮熟。米安的母親看著他們急不及待地狼吞虎嚥起來,像一窩奔竄中的老鼠。
米安的兒女就像她母親那樣,企圖把她從洞穴的深處拉拔出來。其中一個女兒坐在她面前,遊說她到醫院去,躺在病床上,讓醫師在她的眼皮四周注射麻醉劑。她說,只消打一個瞌睡的時間,她眼眶內混濁的水晶體便會被抽取,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的水晶體,她便能回復清晰的視野。米安只看見一團影子,無法分辨那是兩個女兒中的哪一個。另一個人坐在她附近,她嗅到衣服沒有完全晾乾時發霉的氣味,那個人並沒說什麼,只是不斷更換坐姿,末了對她說,家裡孩子眾多,是個切切實實的煩惱,她恨不得抓著他們的頭顱,把那統統塞進他們母親的子宮裡。
然而米安的臉上始終掛著不深也不淺的微笑,她決意要留在那裡。漆黑的中央像一個漩渦那麼耐人尋味。
2.蛇
很久之後,米安仍然能感到自己的左手快要給扯斷。下雨的日子,痠痛尤其劇烈。她知道痛的來源,是她的母親站在石洞以外,像船上的水手用力扯著纜索那樣把她的左手往外拉。
那一年,米安九歲,她無從肯定這是不是一個遊戲,但她不願意走出石洞,因為右方石頭的表面,積聚了一團灰塵,最初她以為那是被蜘蛛遺下的結網。她定了定神,卻看見動物柔軟的毛。後來,她發現那是灰灰尾巴的顏色。牠在她身前發狂地奔跑,肥大的尾巴拖在身後,企圖要擺脫她的視線範圍。
當米安帶著老去的目光審視那石洞,才能察覺那裡縱橫交錯的裂縫,像掌紋那樣令人不解,卻沒法弄清楚自什麼時候開始存在。然後她慢慢地想起來,那像一頭狐狸的眼睛。
偶爾,灰灰會銜著斷掉了脖子的麻雀、失去了頭顱的蟑螂,和縮成很小一團的蝸牛放在她的腳前,她便嗅到了一種鬱悶的腥氣,只能把下巴擱在屈曲的膝蓋上。
軍隊的車輛開進城內以後,糧食的供應便緊絀起來,他們不得不謹慎地掌握進食的分量。但米安的胸口和胃部之間,還是湧起了嘔吐的衝動,或許與死去動物的氣味無關,只是臉頰凹陷的米禾一直蹲在不遠處用手支著下頷盯著他們,她認出了那猶豫不決的神情。在每天上午,橡膠園的休息時段,他會從樹林回到家裡,在屋外的空地挑選那天將要屠宰的動物,試圖從為數不多的豬、雞或鴨子中,撿出沒那麼乾瘦的一隻,那時候,那種神情便會慢慢地爬到他的臉面上去。
米安的母親把她帶進滿布綠色陰霾的橡膠園林裡,她看見眾多兄姊各自占據著一棵樹,聚精會神地低頭以用子小心地刮樹皮,把從樹皮溢出的白色汁液引向瓶子。可是她的母親禁止她走向任何一棵樹,只是拉著她蹲下來,俯伏在布滿樹葉和垃圾的地面。
「把耳朵貼在泥土上,聽到什麼?」她的母親命令她這樣做,她幼嫰的臉頰緊貼著黏濕的土堆,便看見一個倒過來的叢林,天空是那世界的底部,工人低垂的眼睛都有蒼鬱的倒影、叱喝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工人的鞋子踏在掉落的葉片上,似乎還有一些東西在土堆下竄動,她感到腦裡一片混沌,找不到字詞代表她所聽到的,最後只有一個字迸出了她的牙齒,「風。」她說。
「不,」她的母親立即糾正她︰「這下面全都是還沒有出生的嬰孩。」
實在,米安對於自己或別人的來歷,都沒有強烈的好奇,只是在那個幼小懵懂的階段,她的母親便急不及待地告訴她。她並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她的母親說,適合繁殖的季節,大部分的種子都會隨著風而散播,如果那些種子並沒有落到人們的肚腹內,就會掉進泥地裡,被另一層砂礫掩蓋,然後發芽和生長。「因此,這是機會率的問題,要不,你長成了一個人,要不,你成了一棵橡皮樹。」為了使米安更確切地體驗成為一棵樹的感受,她的母親把泥石堆放在她的四肢上,直至她的手和腳都被埋沒。「那些在母親的肚腹內夭折了的孩子、還沒有到達發育期便死去了的,以及從沒有機會孕育成胚胎的,都落到泥地的深處,轉化成另一種物質。」米安只是感到手腳麻痺而冰冷,血液湧向她的頭部。
米安的母親像發出一項指令那樣告訴她,待她長至合適的高度,便要在凌晨時分,提著鐵桶走進樹林裡,劃破樹皮收集樹汁,在陽光下,鐵桶內奶白色的汁液逐漸匯集成一個湖泊,再送到提煉塑膠的車子去。「那麼,我們能換來白米、餵養牲畜的飼料,還有修建房屋的金錢。」她的母親無神的眼眸裡突然閃過一陣奇妙的光。白天,他們隨著晨光起來工作,夜裡,他們在夢中醒來,便走到那個在風中搖搖欲墜的便所,讓食物的渣滓從他們的身體排出。不久後,他們會把發酵了的排泄物,融進泥土裡,潤澤那些愈長愈高的樹。
年老後把身子長期陷進沙發裡的米安,益發感到那洞穴的圓融,她只是沒法明白為什麼它會永遠地關閉,而且毫無徵兆。她想起那一段日子,他們每天只能進食一次,雖然那時候,她還搞不清楚那些跟她身處在同一所房子裡的人,口中常常叨嘮著的「餓」是怎樣的意思,她唯一深刻的感受,只是在那濕熱的村子裡,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的一陣一陣的冷。(倒是多年以後,日復日的勞動使她的肚腹異常空虛,她才感覺遲緩地逐一想起了那所房子裡的許多已經模糊了的人面。)
某個夜裡,他們聚集在屋子中央圓形的飯桌前,吃著煮得稀爛的粥,米禾盯著在坑上沉睡的灰灰,跟他的弟妹討論烹調貓的不同方法。米安記得灰灰奔跑的速度總像在逃命,仿彿牠其實是老鼠而被一窩大貓追趕著。她走在牠身後,腦子裡便會不由自主地蹦出各種獵殺牠的場面。灰灰扭過頭來看她的眼神從沒有畏懼,只是惘然。
只有在米安熟睡了以後,身子散發的溫熱,能誘使灰灰跳上她的床,主動靠近她。她們睡在彼此的附近,互相索取對方的體溫。無論她的睡眠由於何種原因而中斷,只要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再次看到灰黃的紗帳圍繞著她的床,頂部打結的部分呈現出年月留下的斑點,而她能觸及灰灰暖洋洋地在微微顫動的身軀,便會重新知道自己又躺在熟悉的地方。
那個早上比以往任何的早晨都更冰涼,她做了一個不快的夢,當她伸手撫摸身旁鼓脹的身體,就像她所期望的那樣,她醒了過來。紗帳外有晃動的人影,最初他們散落在很遠的地方,慢慢便靠攏在一起,連成了一個令她透不過氣來的影子,像突然翻過來的浪,而且湧向她的床,忽然她又感到那全是體型過大的蒼蠅。為了不致窒息,她奮力支起自己的身子,而身旁的動物恍惚被驚動了似的甦醒過來。
「有蛇。」紗帳外有一把低啞的嗓音在喊叫,令她感到狐疑的並不是蛇的位置,而是那副陌生的嗓子使她想到某個破門而入的人。當她把頭轉到另一旁,便發現紗帳隆起了一角,一道黑色的溪流從她的身旁,衝向地面,迅速滑過客廳,消失在門的背後。她這才發現,她的貓灰灰端立在火爐的頂部,以透徹的眼睛睥睨著她。
他們說,那是一條偷偷溜進來的蛇,乘眾人不察覺,企圖霸占米安的床。他們沸沸騰騰地討論蛇的時候,忘記了米安的存在。而米安終於辨別出那喊叫的聲音屬於她那寡言的父親,他說要在屋子的四周灑遍硫磺。
她並沒有說,那條蛇的身體是暖烘烘的,是她一直想要接近的溫度。
幾天後,那把低啞的聲音再次響起,他宣布︰「我們要離開這裡,再也不能回來。」
米安覺得那條蛇的舌頭穿破了一個孔洞。起初,她以為那破洞在橡皮樹的葉片上,或在屋子的牆壁,後來她才知道,那孔洞在他們的眼膜上,而且不斷擴大,變成了她的眼睛,使她能看見幾個體格壯碩的男女把她和她的沙發重重圍困著(而沙發已滲透了她的氣味,二者如同一體)。他們看著她和沙發時手足無措的姿態使她感到愛莫能助。她嘗試凝神細看他們的臉,可是除了疏淡的眉毛,幾個人的五官,也沒有明顯的特點,這使她生出了更大的疑竇,認為面前的幾個男女,跟洞穴內輪廓含糊的眾多兄姊,很可能存在著親屬關係。
「就讓她在這裡一直安睡,反正從很久以前開始,她就喜歡窩在這裡看電視。」米安的大女兒說。
她的小女兒卻質疑︰「你能肯定她在睡覺嗎?她的眼睛睜得老大,而且這裡有風。」
過了半晌,她的大女兒說︰「或許我們應該讓她自由。」可是她的聲線太低,低得幾乎沒有被聽見。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灰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小說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灰花
跌入韓式卡夫卡的小說世界,自我的存在彷彿在疏離的灰鬱世界中荒蕪,又像從灰泥裡冒出的花朵那麼奪目……這是一個橫跨了三個不同世代的故事,自外祖母米安開始,人們如樹帶著自己的根部在不同地域之間流徙,卻始終找不到一片合適的土壤。米安的女兒陳葵生在一個被限制睡眠的時期。入睡後的人們總會做出踰越規則的舉動,要是他們睏了,只能走到大廈附設的地窖,並為無法自制的睡眠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在那裡,他們再也不相信執法部門和律法。而陳葵的女兒感到,生者懷著的往往就是對死的想望。在那個死者太多,而墓地不敷使用的時期,骨灰便被製成各種家具和器物,摻進混凝土,成了堅固的牆壁,也埋在土裡,長成了鮮的花朵。那些花朵會發出奇異的香氣,令人產生對未來不實的期待……
作者簡介:
韓麗珠生於1978年的香港。著有《風箏家族》、《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及《HardCopies》(合集)。曾獲2008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2008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第20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http://silencehole.blogspot.com不定期更新。
章節試閱
Ⅰ︰ 橡膠園1.洞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日漸衰退的視力,還是像一根倒刺那樣朝著錯誤方向伸展的記憶力,釀成了米安的景況。她的視線就這樣停定在某一點之上,像是被一根看不見的釘子牢牢地拴著,即使日光暗淡,無數身影在她眼前掠過,蚊子在她的附近繚繞,她始終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沙發上,眼神呆滯地盯著前方。令人們感到不安的,並不是她一成不變的姿態就像一臺沒上發條的時鐘,而是出現在她臉上像漣漪般不斷擴大的笑意,漸漸蔓延至臉的每一部分。她的女兒看見她張得老大的嘴巴,露出缺了許多牙齒的口腔,就像一個對世界所知太少的智障兒,他們...
»看全部
目錄
Ⅰ︰橡膠園1. 洞2. 蛇3. 黑簾4. 失收5. 使者6. 欄柵7. 椰子殼8. 軌跡9. 時鐘10. 停頓Ⅱ︰種夢1. 遺腹2. 不倒3. 泥窪4. 生產線5. 牆6. 無夢7. 審查8. 圓環9. 共謀10. 麻醉11. 胎記12. 編號Ⅲ︰灰飛1. 黑眼圈2. 花卉節3. 間隙4. 煙霧5. 骨灰工場6. 穴7. 偷竊8. 罷工9. 飛蛾10. 火種11. 收箱者12. 蝴蝶13. 火山Ⅳ︰花開1. 圈套2. 泅泳3. 破土4. 春泥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韓麗珠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7-10 ISBN/ISSN:9789575228408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