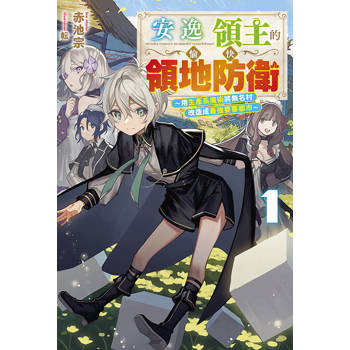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西藏流浪記的圖書 |
 |
西藏流浪記 作者:柴春芽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8-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2 |
歷史小說 |
$ 253 |
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西藏流浪記
我就是想當一個流浪漢,願望非常簡單,我就是厭倦了都市生活。——柴春芽必須要上路了,像個沒落時代的莽漢,拋棄中產階級的空洞無聊和小布爾喬亞的矯揉造作,到西部去,到遠方去,到異域美人和孔武有力的男子組成的自由國度去。一部洋溢著濃郁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因其有過在戈麥高地上與康巴藏人一同遊牧四野的傳奇經歷,作為一個漢人,柴春芽才敢於書寫他對中國西部農牧生活的緬懷;因其漫遊了西藏大地並最終皈依了藏傳佛教,他才勇於坦露心跡,探索靈魂的深度與載力。柴春芽的小說時時複奏凱魯亞克式的反叛與抒情。藉由荒涼旅途上的流浪,追尋精神王國的自由。不同於美國「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消極與頹廢,柴春芽的小說更多地體現人道主義者的悲憫、禁欲主義者的清潔和宗教徒般的救贖。
【作者簡介】
柴春芽,一九七五年出生於甘肅隴西一個遙遠的小山村,一九九九年畢業於西北師大政法系,曾在蘭州和西安的平面媒體做過深度報導的文字記者,後來在廣州做過副刊編輯和圖片編輯。二○○二年進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先後任《南方都市報》攝影記者和《南方週末》駐京攝影師;攝影專題「沿途的祕密」(Something on the Way)曾參展二○○四年平遙國際攝影節;舉辦過兩次圈內的攝影展。二○○五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一個高山牧場義務執教,執教期間完成大型紀實攝影《戈麥高地上的康巴人》。現居北京,為獨立作家和自由攝影師。著有《西藏紅羊皮書》、《西藏流浪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