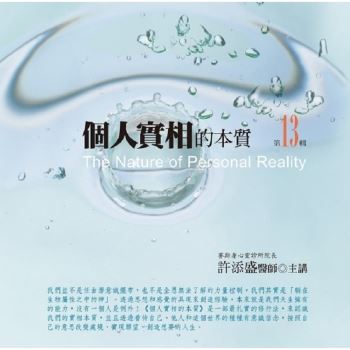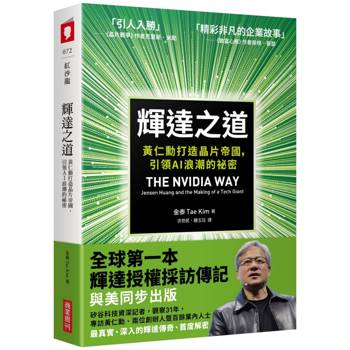吳億偉──新生代作家中的赫拉巴爾
以赫拉巴爾式笑中帶淚的詼諧,卡夫卡式的變形精神,
將平凡的芭樂人生,瞬間扭曲
諷刺的筆法,平實的語言,近乎寓言的荒唐情節,勾勒無生命的人物
故事在當下發生,荒謬與唐突也隨之進行
吳億偉在平實的語言上承載無垠的豐富想像,在日常生活中尋找荒謬的縫隙、唐突的時刻,對他來說,那當下是人生最清澄的瞬間。所有事情皆無法掩埋,人非得誠實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不可。符號拼貼下,你我都是吳億偉小說中的「他」,也過著驚惶弔詭的「芭樂人生」,無法自拔陷入「借貸家庭」裡的金錢遊戲,或隨「跳舞機」的箭頭無意識地晃動雙足……,一覺醒來,竟發現自己和小說人物一樣「吳名字」。人生被符號黏貼,拿掉符號,僅存的是什麼?你要接受現實?還是迎接另一次變形?
作者簡介:
吳億偉曾經獲得一些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梁實秋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也做過一些事情,國小老師、《自由時報‧副刊》編輯。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一九七八年台北出生之後,不停轉彎的人生。分別在台北、高雄、嘉義,經歷了四間國小,三間國中,完成了他的國民義務教育。大學時念語文教育,本以為自己將會執教鞭一生,卻在畢業後不知哪來的衝動,賠了公費轉彎去念了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戲劇碩士;本以為自己會去日本念書,成天努力背著五十音,卻意外轉彎到了歐陸,如今人生暫時休憩在德國,為海德堡大學歐亞跨文化研究所與漢學系博士班學生。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郭強生──
我彷彿看到的是一個林野間長大的孩子,好奇又困惑地走進了城市,對自己的青春消逝於商品消費網路虛擬水泥叢林感到哀傷,我會將他的小說處女作結集看成是一部青春「物」語,是物化時代的青春輓歌。
◎郝譽翔──
在《芭樂人生》中,正常的理性只是被規範的瘋狂,而億偉彷彿是在後現代的喧譁噪音之中,發出了一股與時人不彈同調的、冷冷的輕笑。我喜歡他的不煽情、不耽溺,對於現實有一種直覺的哲學穿透力。
◎孫梓評――
每次一群朋友聚會聊天,億偉總是安靜聆聽他人話語,偶爾冷不妨爆出一句,往往精準地使話題加溫、沸騰──他的作品也類於此:低伏冷靜的觀察,但一出手,總能給出最關鍵的一擊。
◎楊佳嫻――
我認為吳億偉的小說和人是一致的。
不是一揭開就知道是甚麼,而是需要往下讀的,往裡讀的。
他向茫漠的世界擲出人生的泥土,想知道世界的回禮是甚麼。
他的小說想回答的是,在這芭樂化的時代,我們還可以怎樣看待作為人的自己。
�伊格言――
關於〈芭樂人生〉,有一件真實發生的芭樂事是這樣的:某日億偉驚訝地發現,在某簡體字中國網站上,有人轉載(盜貼?)了這篇小說,而且,很貼心地將篇名轉成了大陸用語:〈番石榴人生〉。
這實在是太歡樂了,也太芭樂了。這件事本身就跟億偉說的那些笑話一樣。我等待億偉的這本書已經很久了,說笑話確實是他所擅長的(偷偷說,笑話背後的荒謬與苦情也是,不過,呃,現在先不要說這些好了)。他的梗總是很多,又很健康,不但一向青蔥翠綠,而且還會長出很多分枝。我想時候到了,或許還會開花結果。結什麼果呢?
當然是番石榴啊。
�鯨向海――
我認識的吳億偉即便在苦戀失業破產等等鬱苦頓挫之中,也能繼續說笑娛樂別人,茂盛的梗獨特的核,我一直覺得(如果有的話),他應該當選文壇十大搞笑青年!
名人推薦:◎郭強生──
我彷彿看到的是一個林野間長大的孩子,好奇又困惑地走進了城市,對自己的青春消逝於商品消費網路虛擬水泥叢林感到哀傷,我會將他的小說處女作結集看成是一部青春「物」語,是物化時代的青春輓歌。
◎郝譽翔──
在《芭樂人生》中,正常的理性只是被規範的瘋狂,而億偉彷彿是在後現代的喧譁噪音之中,發出了一股與時人不彈同調的、冷冷的輕笑。我喜歡他的不煽情、不耽溺,對於現實有一種直覺的哲學穿透力。
◎孫梓評――
每次一群朋友聚會聊天,億偉總是安靜聆聽他人話語,偶爾冷不...
章節試閱
〈跳舞機〉節錄
我的誕生是從一種規律的動作製造出來的。
父親伏在母親的身上呼嘯,斗大的汗珠在臉上晃動,遲遲滴不下來。父親動得很快,沒有享受性愛的歡愉,好像急著把我丟出來似的,喔喔的喘息聲如老火車頭低緩的鳴叫,噗噗打著引擎前進。
那是母親,我看得到。她臉上線條縱橫,皺摺沿著顴骨一路凹到雙頰,在酒窩陷成一個窟窿。兩顆眼珠轉動不停,眼白和瞳孔交換著位置。她瘋狂扭動她的腰,身體成不自然的形式歪曲,長髮在枕頭間灑成一條條不安分的蚯蚓。
層層贅肉擠壓父親老邁的身體,老人斑在他的皮膚上蠕蠕竄動。就快了。父親吐出舌頭,撐起上半身,下體進出的動作散發猥瑣的氣味。我捏鼻。此時,母親磨著牙齒,一種撕裂紙張的沙啞從母親咽喉底部緩緩爬出,試圖越過乾涸的結繭的雙脣向大氣散逸。
「不要吵!」父親詛咒似的惡罵。母親的指甲流盪在老人斑間抓出數條紅線,汨汨滾著血液。
持續進行,沒有創意的動作。
母親揪著眉頭,鼻孔咻咻吐出氣息,頭搖著,很大力。
很大力。用指甲嵌入肉裡。父親大叫,陽具跟著大叫,在一旁的我也大叫。
父親窩進被子,母親赤裸起身,搖搖擺擺地走到客廳。
我叫她,她回頭。我輕輕撕下她嘴巴上的膠帶。
一層一層數不清的一層,直到撕下最後一層,呼吸到空氣的嘴巴,突然大叫。危顫顫的屋子發抖。
我直視母親跳起舞來,倚著沒有聲音的節奏擺動起來,雙手在頭上交疊,十根手指頭像綁花繩糾在一塊。月光從窗外迆邐而入,豐美的乳房在詭譎的氣氛中,洋溢著母者的喜悅。有那麼一刻,我相信母親是因陌生的我而舞的。
多年後,父親很高興地告訴我,那一晚,還好母親安靜,所以有我。其實我早就知道,不過我沒告訴他那一晚母親為我跳舞這件事。我一直相信當時在肚子裡的我也在跳舞,所以我有著跳舞的基因。
�
我能看到過去。
沒有人知道。
當我在跳舞機上跟阿榮說時,他嗤之以鼻。
你當你是《靈異第六感》的那個小男孩啊!I can see the dead people.
一副不相信的臉,還裝出那小男孩無辜的樣子。
真的。我說,螢幕上反映我的表情,還真的跟那小男孩差不多。
好啦!阿榮看著不斷上升的箭頭,雙腳交叉齊跳。這什麼舞步嘛!你看,都是你和我說話,害我的combo又斷了。
我們正跳著NO.9
的〈END OF THE CENTURY〉等級五個腳印,背景舞者是由許多圈圈組成﹁圈圈人﹂,唯一能分別他們的性別的,就只有頭上的記號。
男生是一個戴著箭頭的圓頭,女生則是一顆圓頭掛著十字架。
看圈圈人跳舞很不舒服,彷彿在看一圈圈脂肪隨著重金屬樂抖動。阿榮跟我有同樣的感覺,可是,我更不舒服的是,那圈圈開閤開閤之間,好像在說些什麼,宣告什麼,挑戰什麼似的。
彷彿被圈住一般不暢快。
阿榮說我想太多,隨著鏡頭忽近忽遠的圈圈人免不了影響我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圈圈人的畫面,我的combo通常都不下於兩百。
�
當我被拉出娘胎時,我沒有哭,父親說那時醫生護士和他急得都快瘋了,但我樣子還是堅毅得很,眼睛望著大家,臉連一點抽動都沒有。
我問父親,為什麼要哭,他說,大家都哭啊!這樣才正常。
或許那時的我就在抗拒生命中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吧!像哭。這是一種示威。我覷向剛從羊水甦醒的自己,幼小蜷曲的身軀,稀疏的頭髮緊緊貼在頭皮上,弱顫顫的手指頭一隻一隻動著,腦子裡還在想那晚母親的舞姿。
後來我有沒有哭?我問父親。他吶吶笑了笑,當然有,不然你怎麼活下來。
我後來怎麼哭的,我繼續問。
他說,就是哭啦!死命地打你屁股吧!太久了,我記不清楚,反正你就是哭了,老子盼你那麼久了,你哪能不活下來。
零歲的我怎麼哭了,我想跟醫生打我是沒有關係的。是十七歲的我輕輕地在他耳邊說你會活下來,至少到十七歲,所以他就哭了。
�
去年夏天我瘋狂迷上跳舞機,一轉眼,都已經從一代的「Dance Dance Revolution」跳去年夏天我瘋狂迷上跳舞機,一轉眼,都已經從一代的「Dance Dance Revolution」跳到三代了。
但要我說一代二代和三代有什麼差,我也說不上來,反正都是投幣之後跟著箭頭音樂跳來跳去。像我這種每天都去跳個幾百元的傢伙只能記得電玩店現在放的跳舞機長怎樣,或許說,跳舞機給我的印象都一樣,只要有音樂箭頭,就是跳舞機。
就像市區一些店被火燒掉之後,我就想不起來當初那些店面長怎樣,甚至是哪些店都不知道了,記憶整個被拔除。
等到那些火燒過的廢墟重新建起,我的記憶再次裝潢翻新,阻斷的黑幕才又升起,噹噹噹一齣新劇。
我跟阿榮說這些的時候,他哈哈哈笑三聲,你的記憶怎麼那麼差,隨後把燒掉的店鉅細靡遺連店長是誰什麼時候開都告訴我。
我說不是啦!我真的覺得有些東西離開我的眼睛,我就再也想不起來了。
他說,我知道,從你的成績就看得出來。
不是啦!我辯解,那是很抽象的東西,就是,就是,你不覺得過去的東西好像都是死掉的。
�
小時候的我日子如影印機,一次亮光,一天。
起床。亮光。早餐。亮光。父親出門。亮光。中餐。亮光。午睡。亮光。父親回來。亮光。晚餐。亮光。看電視。亮光。睡覺。
唯一特別的是夜裡起床上廁所,我坐在馬桶上大力屙著屎,屋簷水珠落下,一滴。一滴。一滴。
規律的一滴。一滴。一滴。聲音很空洞。咚。咚。咚。
像鬼魅歎息。
好恐怖,背脊涼了一片。我起了身趕緊拉著褲子往房間衝去。窩在父親懷裡發抖,但父親的胸部貧瘠乾扁,靠起來不舒服。
於是我懷念起母親的乳房和那晚美麗的線條。它們在夜裡幻化成一朵朵闇黑的花苞,帶著迷濛的吸引力,隨著眷村裡低矮屋頂連成的稜線一路生長。沒有盛開,直接散成花瓣凋落。
就在花瓣落盡那天,我和七歲的我在巷口,看到母親緩緩向我們走來。
�
電玩店裡的青少年都背負著已死的過去而聚集,或說逃避。我看不到別人的過去,但我感覺得到。
於是大家都用一種「現在式」的方式生活著。連對話也是。
我跟阿榮就是這樣。儘管他說他的記憶力很好,可有些東西他就是記不起來,他也想不起來。
不跳舞時,我們就蹲在門口哈啦,靠在亮亮的燈泡旁,東看西看。
然後兩個人「現在的」聊起來。
「你看,前方三點鐘方向有一個辣妹走進來。裙子到屁股而已欸。」
「哪裡哪裡?」
「快看快看,她的三角褲是Hello Kitty的,真噁心。喔喔喔,她坐下來了,露毛了露毛了。」
「你知道○跟╳搞上了嗎?」阿榮見辣妹遠去後,問我。
「真的嗎?」我驚訝。
「他們上旅館被偷拍了,現在錄影帶正在流傳,呵呵,聽說很精采。」
「我也要看。」我忽然想到,「我有K的新寫真,更火辣了。要不要看啊?」
「借我借我!」一臉色狼樣。
「求我啊!我還有T出的新專輯欸,要不要聽啊?」
「他媽的,他唱歌有夠難聽欸,你還買!唱這樣乾脆去吃屎好了。」
「改天我們去看電影,最近新出一部聽說不錯。」我轉變話題。
我們的對話沒有過去式,偶爾摻雜未來式。
大家同一默契地沒有「過去」。因為日曆撕去後,那天就不見了,所以只能談著「現在」。
但自從我能看到過去後,一切卻變了。我發現自己漸漸抓不到這種對話的節奏,阿榮說我變了,講的東西很無趣。
突然打不進這圈子。
誰管你的過去,現在都管不好了。
管好你的跳舞機怎麼跳就好。
�
多半的時間,外婆帶回來的母親很安靜。早上起來洗衣服燒飯抹桌子擦地板,上學前給我個小小的微笑送行。跟大家的母親都一樣。
我有點失望。我總是對朋友驕傲炫耀我有個會跳舞的母親。
他們好羨慕。我說下次帶大家來家裡看母親跳舞。
可母親依舊每天洗衣服燒飯抹桌子擦地板,規律的節奏。父親說這樣的日子很好,可是我覺得很無趣。
然而,母親還是喜歡跳舞呵。
七歲八歲九歲及現在的我躲在屋子的四周窺視,發現母親興致來時,還是會兀自地在客廳臥室廚房踮腳旋轉。
沒有通常。母親可能拿著抹布低喃,我在椅背偷瞄,她低頭,雙眼斂下,搖頭晃腦起來。
連頭髮都飛了起來。母親起身,揮揚抹布,地板彷彿布滿圖釘,雙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快速蹦蹦跳跳。
很用力。母親皺眉咬著抹布。撕裂。身體轉成一個S。
好美。猜不出下一步是什麼。跟老師教我們唱遊不一樣,虎姑婆就要表演老虎的動作,唱到花要把手捧成一個碗。
或是掃把變成麥克風。母親大叫。站在床上,她把畚箕掛在頭上,握把變成一串辮子。電話線交纏在身上,一個叉叉黏上一個叉叉。她看不慣那擺放整齊的物品,把它們統統弄下來。
急速扭動腰臀,啦啦啦雙唇開閤舌頭歙動。母親牽著我的手,果然腳下都是圖釘,蹬著蹬著,像爆竹在地上啪哩啪哩。
母親凝視我。眼神很深,跟酒窩一樣。可以爬進去,裡頭是個神祕又美麗的國度。
母親有兩個樣子,有時跟大家的母親都一樣,有時是我的愛跳舞的母親。
時間與身高抽長的過程中,母親愈來愈專屬我。在家裡,她常常跳舞給我看,父親出門的時候,她把家裡當作舞台,那時我已知道恰恰探戈霹靂舞街舞,但母親的舞步不能歸類,獨一無二。沒有規律的舞步。
我偷偷學她。準備在學校表演,同學一定會說我跳得很好,比虎姑婆哥哥爸爸真偉大好。
母親跳完後,總忘了把東西收回去。很亂。父親回來都皺眉,臉上全是皺摺了,還把線條擠成一起。
空氣中游動的眼神撞擊。
九歲的我發現我,想要跳舞給我看,他說他學了很久,或許能在校慶晚會中表演。
我能感受那種舞動的慾望,整個身體連基因都在不安分蠢動,所以我說好,而他開始跳,從房間到客廳,彷彿一隻響尾蛇在追逐,啊啊啊他叫個不停。
被咬到了。他頭陡地撞向地板,木質地板匡啷一聲。好痛,所以他叫了長長一聲。抽動抽動。臉上的肉虯曲,指甲刮過地板,滋一聲很刺耳。打滾,如蛆。我驚訝一個小孩怎麼那麼厲害,不自覺拍起手來。
沒發現父親正悄悄從前廊踅近,在背後呼吸氣息急促,眼睛瞪大,詫異的連嘴巴都忘了關起來。
父親很氣,大喊:你在幹麼?一把提起九歲的我,一巴掌一巴掌打下去。
你在幹麼?你在幹麼?氣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急促搖晃他的肩膀。
母親躲在紗門後定定瞧著而我慢慢靠近他哭泣的臉。
你不要給老子耍花招。聲音在嘶訴。
我邪惡地譏笑,指著他的鼻子冷冷道,你不知道有些舞是跳不得的嗎?
在我說話之前,九歲的我也意識到這句話將在他心裡生根如馬鞍藤蔓延,紫藍色的花失序散布在沒有海的沙灘上。線段交錯。
�
我跟阿榮認識就等於兩條線的相接,沒人知道另一頭是怎樣。
我們交接在一點。
偶爾在纏繞時會看到我們不同時間卻交疊的過去。
一回我得了SS之後驕傲的下來,擦著額頭的汗時阿榮問,你一直都那麼厲害,難道沒有跳不好的時候?我想了想。有一次啦,我生病,不知道在跳什麼,發燒發到連箭頭都看不清楚。後來得了個D,沒有人同情我還被大笑一場。
是喔,我記得我第一次跳的時候真的很差,選到最高級,幾乎沒有一個箭頭跟得上,硬著頭皮跳完。那天假日人很多,圍觀的人都用眼睛取笑我。真丟人。那些眼睛很傷人。一個接著一個像射箭過來,覺得你很滑稽、很好笑、很奇怪。本來打定主意不來玩了。
有那麼嚴重嗎?我覺得他太誇張了。
你不懂啦。那些眼睛都在說話,譏笑你,很不舒服。他打了冷顫,很認真的說,現在想來都不舒服。
我懂,我懂。我拍拍他的肩,安慰他。
�
我實在羨慕母親,她能那麼簡單地表現自己。
我容易緊張。老師說。尤其在臺上,尤其要考試,尤其大家看我的時候。
背九九乘法表的時候會不停地捏著自己的手指頭,一直捏一直捏。或是折著手指頭,一隻接著一隻。
考試的時候會咬著舌頭,大力大力大力,直到痛得受不了才停止,不痛的時候,再大力大力大力。
上臺時,眼睛會轉個不停,腳失控地搓揉地板。
老師笑咪咪的說,不要害怕啊!但我不舒服,不像母親那麼自在。
大家等著看我表演。那個眼神這個眼神在說,你看你看他又來了呵呵呵。你看你看他的手指頭都紅了。你看你看……我受不了自己,我好緊張,好丟人,窩在廁所敲著自己的腦袋。
我不要這樣。上排牙齒擠著下排牙齒的位置,發出唧唧的聲音。廁所的空氣摻雜大便小便的味道,仍遏不住我吶喊的衝動。
�
跳到一半的時候有人投幣。向我挑戰。
畫面忽然漆黑。機器壞了?回神,阿榮呢?四周都沒有人,聚光燈打在我和一個女人和跳舞機上。
光滑的螢幕反射我們的身影。是母親。撇過頭去,還是那件連身繡花長裙,嘴咧咧地笑,親切的說:要跳囉!沒有主唱者,〈FOLLOW ME〉,沒有等級,零個腳印。
沒跳過這首,哪來的?音樂分貝零。窒息的氛圍。母親跳起來,重複四個簡單的舞步。前、後、左、右。前、後、左、右。螢幕上沒有箭頭啊,我沒法跳。覷向她,我的腳自己動了起來,隨著母親,一模一樣。那是很完美的演出,我能想像,若有人在背後觀賞我們,一定會發現這完全相同的步伐,正呈現畫一的美感。
身體開始一圈一圈分割。圈圈人。跳動時圈圈與圈圈之間還會不協調的撞擊。噹噹,肉做的圈圈發出金屬的聲音。
其實我會怕,規律行進的東西背後藏著魔鬼。可是母親正快樂呢,所以我還在跳。
聚光燈下,我們一起跳。反覆的前、後、左、右、前、後、左、右。
驚醒,日光辣辣地亮。啐!是夢。
�
原來母親也會在外頭跳舞。我終於發現。她特地到學校跳給同學看。
學校無法上課。所有的眼睛被母親釣去,聚在窗口一顆頭一顆頭騷動。
那舞步是新創的,我在家裡也沒看過。連身繡花長裙,在操場上向天空猛抓,喉間發出一聲一聲的呃呃呃。
沒有鞋。長裙底沾著腳底扎傷的血,一片一片紅紅的,遠看像補丁。
廣播器大聲喊著要大家回去上課,沒有人聽,還有人圍在跑道上看。
好美。連我都著迷了。忘了跟大家說那是我的母親,會跳舞的母親。
直到訓導主任和校工把母親抓起來,一路趕同學回教室,我回過神,同學間厭惡表情傳來遞去。
哪裡來的瘋子啦!呵呵。真丟人。
好好笑。誰家的瘋子啊?連老師也一臉嫌惡。不舒服的繼續上課。
九歲的我想起我曾說的,有些舞是跳不得的。彷彿被一箭穿心,趴在桌上嚎啕大哭。
�
你會不會覺得每次都跟著箭頭跳很無聊?幾乎跳爛每首歌的我突然這樣覺得。
會嗎?這樣才好玩啊。
會嗎?我起身,又投下代幣,隨意選了一首N.M.B.的〈KEEP ON MOVING〉。
箭頭開如上升,我的腳恣意跳起來。畫面上一連串的Fail。
你在幹麼?阿榮在一旁擂我。浪費錢咧。
四周圍觀的人報以疑惑的表情,不曉得我在幹麼。
好了啦!認真跳啦。他勸我。
我依舊跳著自己的。這舞步嶄新且獨創,僅此一次的演出,沒重複的餘地。
雙腳創意地在四個箭頭間來去,我跳躍,甚至用手來跳。
音樂結束。那是我得到的第一個E,可是我卻很高興。
我拍拍阿榮。感覺很不錯呀,你可以來試試!不要,很丟人。
其實我跳得不錯啊。你看不出來?他搖頭。
又不是一定要跟著跳才好,要與眾不同。
遊戲都有規則啊。要嘛你就不要來玩這個,到旁邊空地去自己耍就好。
�
母親愈來愈喜歡在外頭跳舞,不喜歡待在家裡。
小村裡的幾條街都看得到她的行蹤。
大家都叫他「笑欸」,本來我以為那是因為母親很愛笑所以叫笑欸,但後來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九歲十歲的我拉著我,要我去看母親在菜市場被人用菜砸,蹲在攤販下拿地上的饅頭猛啃的模樣,沒有跳舞的時候,母親不再那麼美。
九歲十歲的我在我兩旁,他們說還是喜歡看母親跳舞哪。
想學母親跳舞啊。小眼睛咕嘰咕嘰轉動。
我沒說什麼,叫他們去學校。他們跺腳搖頭說不要。
九歲及十歲的我說在學校,沒有人願意跟他們作朋友。
說著說著九歲的我哭起來,大家都叫我「笑欸」。他們都來鬧我,學我咬牙齒,學我跺腳的樣子,學媽媽跳舞的樣子。大家都等著看我上台出糗。可是我害怕,我緊張。
我不是故意這樣的。真的不是。大家都用那種眼神看我,不要跟我作朋友,不要跟我作朋友。
我抱著九歲的我。不要哭,不要哭,會過去的會過去的。
十歲的我臉上有圈黑青,他說,有人鬧我,在我面前裝白癡,故意用歪嘴巴說話。我氣不過,衝過去跟他打起來,一拳一拳,大家在旁邊竟然鼓譟,發瘋了!發瘋了!好恐怖唷!瘋子打人。
太過分了。我按著他的肩膀。
十歲的我吸吸鼻子,用手擦拭流下的眼淚。我沒有哭,就算老師叫我過去時用著討厭的眼神,藤條打下去一板比一板大力。我都沒有哭。
你們沒有跟爸爸說嗎?沒有。九歲和十歲的我,異口同聲。他忙著打媽媽。
�
我很想看看你的過去欸。一天,我們蹲在電玩店門口哈草的時候,我跟阿榮說。
喔。他不太理我。應該說到現在他對「我能看到過去」這事還是很嗤之以鼻。
可是我只能看到自己的過去。
那最好。口氣很慶幸。
喂!看一下會死喔。我伸手過去推他,他重心不穩倒下來。
哼!那你脫光光給我看啊!他起身,一臉不屑。
好啊!我卯起來跟他槓上。
我才不想看。
停頓一下。阿榮突然又說起來:你不要老是過去東過去西的啦,過去的都過去了,重要的是現在,是現在!
一邊說話還一邊吐口水。一沾到我馬上伸出手,把口水擦回他衣服上。
�
十一歲的我常常做的事。折手。咬牙。大叫。慌張。咬舌。跺腳。
躲母親。
那時候,我極度害怕看到起舞的母親,那是個不可抗拒的咒語,我意識到。
我躲,在街上看到她就躲,聽到她的聲音就跑,小心翼翼的轉著彎。
父親則是追,在外頭把她抓回來。拉她頭髮。我不想看。
所以我躲在自己建構的黑幕裡,做著電視裡巫師擅長的事情。破除咒語。
十一歲的我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魔鬼都怕鮮血。用血驅逐他們。
每當在學校折手,回到家午夜十二點,就會拿起石頭敲自己的手。咬牙齒,就打巴掌。想大叫就用膠布貼自己的嘴巴。一切的儀式,要等流出血來才停止。
這是很惡毒的咒語,我必須要犧牲。
我不要再這樣下去。要拯救自己和母親。
十一歲的我,日記裡總不忘再加上一句,我還是喜歡跳舞啊。跟母親。
�
阿榮離去那天跟每天都一樣,我們說著現在式的對話。
把最後的錢用來挑戰一百九十度的「PARANOIA REBIRTH」,這首歌最高級的舞步十分繁雜難解,是跳舞機界裡出了名的,連我都有點害怕。許多人的最終目標就是打敗這首歌。
我每天跳上兩三次,但頂多得到A。阿榮更慘,有B就偷笑了。
那天我們一起站上跳舞機,音樂才開始,機器舞者還沒開始扭動,啪地畫面上箭頭像下雨。
只不過不是落下,而是急速昇回天空。
我跳得很累,瞥向阿榮,他卻異常輕鬆冷靜,沒流多少汗。
我扶著後頭的把手,前後左右的轉身跳起,螢幕上箭頭不停刺進視網膜,催促雙腳運作。
阿榮跳得不錯,combo跟我差不多,今天有鬼唷。
曲子結束,他得了SS,我才A。
我嚇到,難道他偷偷在練?每天看他跟我在一起,怎麼忽然就一躍千里?難道我的功力被偷吸了?他哈哈大笑,換他驕傲了:怎麼,這才是我的實力,不相信吧!哈哈哈。
還在笑。
太誇張了。有鬼。
他拿起背包,就要騎車走了,我問他要去哪裡,他說他要搬家了,不會再來了。
我又嚇到。真的有鬼。
他跟我說聲再見。就這樣跑了。
後來電玩店老闆告訴我什麼生他的新媽媽找到他想要領回他,養他的舊媽媽不願意。他們鬧得不愉快,舊媽媽決定帶他跑掉不讓新媽媽找到。聽說他小時候住孤兒院哪。
你都不知道嗎?我點頭。
我們從不談過去,也沒留過聯絡方式。
因為我們是現在式。
不過這一切出現得太突然,突然到看到跳舞機時我都會想阿榮是不是不曾出現過,他只是我創造出來的人物?跳舞機上還是很多人在跳〈PARANOTA REBIRTH〉,奮力的追著箭頭踏著腳步,只要得到兩個SS就破臺了。
大家奮力是為了什麼?我蹲在一旁想。
PARANOIA REBIRTH。
REBIRTH。
重生。一種對過去的反抗。
�
我永遠忘不了母親最後一次的舞蹈。
儘管我叫自己不要再去看那令人窒息的擾人的舞動,卻仍習慣遁在熄燈後全然的漆黑中,窺望窗外微弱的光,在母親身上竄成一盞盞走馬燈。
她踮腳緩步,異常優雅。那樣輕輕的,柔柔的,長裙在旋轉慢慢揚起,過長的袖管揮成兩條水袖,在空中畫著流暢的弧線。
然而有一把剪刀。她握著,刺破水袖。危險吶。我喚著十二歲的我把它搶過來。不過回應的是一對失了神被蠱惑的眸子。
好美啊。她唱起歌來,曲調如羅曼史般動人。彷彿又回到最初那夜,第一次看見母親起舞。
同樣的舞步,沒有旋律。母親將雙手交疊。十二歲的我受催眠似的從門後站出來,向她爬去。
她卸下所有的衣物,睡衣、胸罩、內褲。裸裎。月光及乳房。我想拉住他,抓緊短褲,可十二歲的我在縮小哪。
愈來愈小,愈來愈小,變成一個小圓球,從母親下體滾回子宮裡去。
我無法阻止。母親意識到我的存在,直對著我笑,呵呵!她笑呵呵!她笑。
剪刀還在手上啊。我說。她點點頭。忽然往肚子捅下去,很大力,撲地撲地捅著,像父親伏在他身上的動作一樣。規律。進出。
大叫。之後,客廳裡有好多血,躺下的母親正驅除所有施咒的魔鬼。
我覺得好痛,那曾是我待過的肚子,所以猛刺的勁道似乎也不留情地朝我而來。刺入刺入。來不及拯救匍回子宮十二歲的我,好痛。
可現在的我就是十二歲的我啊。瞬間忽地被壓縮,一半的我失蹤一半的我變矮。我用矮小的那一半仰望身旁的父親,只可惜外頭連一點月光都隱沒了,什麼都看不到。
好恐懼,只剩北風灌入,好冷,我眼淚因此凍結好幾天,在臉上畫了兩條痕跡,過了好久才消去。
�
阿榮走後,我還是每天報到,對著螢幕蹦蹦跳跳。
近來,我注意到畫面開始的KONAMI,這是出產跳舞機的公司名稱。
但我總覺得那是一個人,不是公司。
KONAMI是個主宰者。他創造了那麼多舞步,大家投了錢,有相連關係的人,跳著相同舞步。
忽地母親的舞蹈浮上眼簾。我覺得那繁複的舞步應該是她從主宰者那兒學來的。她跟隨舞曲的箭頭不停舞動。想教我怎麼跳,但是我沒學好。
還好我血液裡還記著那舞曲那舞步。學不好,我還可以交給我的兒子女兒去學,告訴他們那是阿媽留下的舞步喔。
�
父親不會痛。因為他沒有哭過。一直到我十三歲搬了家,他的眼睛還是乾涸的如沒有綠洲的沙漠。母親像一把伸縮刀,猛刺著父親,父親還是不會痛。
可我還痛,常不定時發作,有個東西總愛扯著我的心瘋狂地打。
尤其是在家裡,獨自一人時,那東西便會像隻潑猴在體內恣意瘋狂。
我沒告訴父親,我想他不能體會。所以我找到治療自己的方法,就是少待在家裡。那痛如針扎啊!愈痛愈不敢回去。
晃蕩。一個街頭又一個街頭。為了治病。
一天,父親在一個轉角抓住我,要我回去,我不肯。
多年前,他也這樣抓過母親,我複製母親那時激烈搖頭的動作。「不要這樣」的念頭遂使我沒骨氣地在街上哭起來。
父親手臂上的皺紋一條裡頭還有一條的。其實他已經老了,也抓不太動我。只是無力感一陣陣襲來,我沒法反抗。
他語無倫次朝我大罵,他奶奶的,你還不回家,為了你老子付了多少心力,還娶了那個瘋婆子。怎麼,你也要這樣,你是著了那婆子什麼魔,發什麼瘋?你給我正常一點,給我回去,老子不信治不了你。
這一刻我才想通,原來不是先有父親母親所以才有我,而是先有父親和我所以才有母親。
最開始的那晚,父親其實是伏在我身上,而不是母親。
好痛。潑猴狂舞。我不要這樣。
�
跳舞機總有被淘汰的一天,就像所有電玩機的命運一樣,一開始擺在門口,後來擺在角落,再後來沒地方放就丟了。
新的很快變成舊的,舊的很快就不見了。
一天,我到電玩店,那跳舞機僅存的角落已被某臺對打機取代。老闆說,這東西過時了。
眼前忽然黑了一片。我意識到自己再也看不到過去了。
可是我還想跳。已是種習慣。
所以必須再到另一家遊樂場去找尋跳舞機。
機車發動時,N&S的〈DEAD END〉,鏘鏘的在我腦子裡唱了起來。
〈跳舞機〉節錄
我的誕生是從一種規律的動作製造出來的。
父親伏在母親的身上呼嘯,斗大的汗珠在臉上晃動,遲遲滴不下來。父親動得很快,沒有享受性愛的歡愉,好像急著把我丟出來似的,喔喔的喘息聲如老火車頭低緩的鳴叫,噗噗打著引擎前進。
那是母親,我看得到。她臉上線條縱橫,皺摺沿著顴骨一路凹到雙頰,在酒窩陷成一個窟窿。兩顆眼珠轉動不停,眼白和瞳孔交換著位置。她瘋狂扭動她的腰,身體成不自然的形式歪曲,長髮在枕頭間灑成一條條不安分的蚯蚓。
層層贅肉擠壓父親老邁的身體,老人斑在他的皮膚上蠕蠕竄動。就快了。父親吐出舌...
目錄
目次
推薦序一:荒謬的青春,迷失在物語 郭強生
推薦序二:逃逸與自由──吳億偉《芭樂人生》 郝譽翔
芭樂人生
他
借貸家庭
蒼蠅
一九九九的最後一天
名字
跳舞機
蜻蜓隊伍
網路失火事件
後記:許正平V.S.吳億偉 對談
目次
推薦序一:荒謬的青春,迷失在物語 郭強生
推薦序二:逃逸與自由──吳億偉《芭樂人生》 郝譽翔
芭樂人生
他
借貸家庭
蒼蠅
一九九九的最後一天
名字
跳舞機
蜻蜓隊伍
網路失火事件
後記:許正平V.S.吳億偉 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