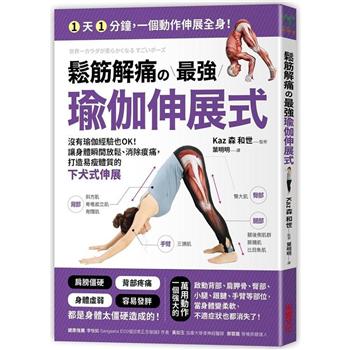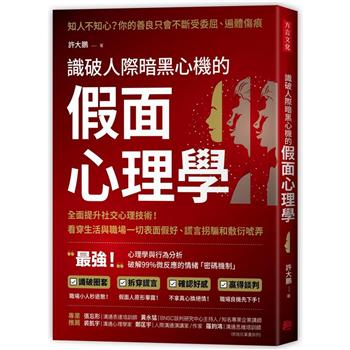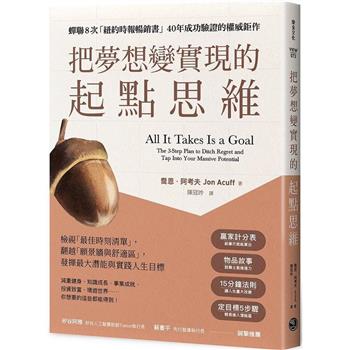本書收錄施如芳六齣歌仔戲的創作劇本《帝女.萬歲.劫》、《大漠胭脂》、《人間盜》、《梨園天神桂郎君》、《無情遊》、《凍水牡丹》,寫的雖是古人古事,卻取材新穎,意境動人,鋪陳了人性的溫度與生命的深度。不論是父王殺女的血淚掙扎、北周公主大漠和親的愛恨情仇或醜惡的音樂奇才受世人嫌棄的憤恨不平,這些舞台角色在精心布局的劇本中精采呈現,一向通俗的歌仔戲,在施如芳冷靜卻深情的筆下,表現出不同於一般傳統戲曲的文學性與精緻性。在光影交錯、氤氳迷濛的戲曲舞台謝幕後,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劇中人在文字裡活靈活現、如泣如訴……
作者簡介:
施如芳
台灣彰化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現為編劇,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級專技人員。
志在一劇之本,寫自己想看的戲;與「唐美雲歌仔戲團」搭檔創作多年,為歌仔戲走出言淺意深、雅俗共賞的路向;近年開始參與其他戲曲、戲劇劇團,除了仍耽溺於載歌載舞說故事,其餘形式不拘,寫過歌仔戲、京劇、崑曲、豫劇、歌劇、音樂歌舞劇;擅於量身設戲,合作過的演員和劇團,幾乎囊括臺灣戲曲中壯年輩的眾名角;作品質量可觀,跨界的觸角甚廣,獲2010年《表演藝術》十年回顧特別企劃「戲曲」、「戲劇」兩類並舉,京劇作品《快雪時晴》獲文學評論家王德威高度期許,《天下雜誌》特刊驚豔推薦;應邀為「豫劇皇后」王海玲表演藝術生涯五十週年編創《花嫁巫娘》。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王安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向陽(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所長).李敏勇(詩人).林谷芳(禪者)
徐亞湘(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鄭清文(作家)
聯名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如芳並不堆砌美文雅詞,一切從深情出發,她的人生體悟極為深刻,心思極為細膩,風生水湧、月落潮生,自然界瞬息萬變皆有感於心,且又不只是少女般的纖細柔情,如芳冷靜觀照,能為歌仔戲注入寬廣的大格局。
——王安祈
施如芳是當代臺灣戲曲的最佳詮釋者。
——王德威
施如芳做為一個讓人矚目的歌仔戲劇作家,是她在傳統上的創新。她大膽打破歌仔戲的封閉性,讓戲劇元素更豐富、動人,更臻於藝術的高度。
——李敏勇
讓古典連接當代,又不因當代失卻古典,兩者得兼,戲曲才有未來可言,如芳的劇本就在此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林谷芳
看如芳的劇本要比看演出有著更大的享受和愉悅,讀者的意會與想像,將遠遠超越舞台上可能會有的局限。看過演出最好,沒看過的讀者也不會遺憾,因為那在閱讀當下的情感流動與藝術交會將會是一致的。
——徐亞湘
推薦序1
一切從深情出發 王安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
我對如芳的認識從她的戲開始。
大約一九九○年代初,我看了唐美雲歌仔戲團的新編戲《榮華富貴》和《添燈記》,深覺劇本情味醇厚,開始注意編劇名字,從此知道了「施如芳」。
而後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漠胭脂》,歌仔戲唱詞一向給人的印象是通俗的,如芳的《大漠胭脂》卻高度文學化,不僅融入樂府民歌「天蒼蒼,野茫茫」,如芳自己新編的幾段宛如現代詩的唱詞,更令人驚嘆。唐美雲歌仔戲的精緻化與如芳劇本的文學性是交相成就的。
如芳文學劇本最高的表現在《無情遊》和《梨園天神桂郎君》。前者劇名取材自李白詩,後者改編自《歌劇魅影》,如芳的文學視野出入古今中外,而一切出之於心有所感,不只是題材炫奇而已。《無情遊》一段古月今塵意境的營造,首度呈現了歌仔戲「交互觀照」的視角,同一女子超越時間跨度,今昔對看,抒情境界之高前所未見。此刻,「分割舞台」不僅是劇場設計,也不是敘事手段,而是情境到位之必然。《梨園天神桂郎君》一段〈且慢來〉,也使這齣戲的價值拋開「歌仔戲改編自音樂劇」的話題糾纏,體現了自我獨立的文學意義。當文筆鉤出了人心底層流動搖曳的萬縷千絲,當文筆能在抒情達意之上更體現意境,古今中外各種文學形式頓時相通。此時討論什麼「跨文化」或「劇種語言特質」都是多餘的,如芳深邃幽杳的情思與冷靜清剛的筆調,本身即是純粹的美。
有些歌仔戲專家認為如芳的唱詞並非歌仔戲的本格正宗,但我認為,現代詩般的語言或許是打開歌仔戲現有格局、提升文學意境的一把鑰匙。
如芳並不堆砌美文雅詞,一切從深情出發,她的人生體悟極為深刻,心思極為細膩,風生水湧、月落潮生,自然界瞬息萬變皆有感於心,且又不只是少女般的纖細柔情,如芳冷靜觀照,能為歌仔戲注入寬廣的大格局。更為可喜的是,世情諸般體驗,如芳常願與我伊媚兒分享,這些年來,我們幾乎成為談心筆友,有時無事,通信只談會心處,彼此雖難得一見,卻總覺肝膽相見。
二○○五年左右國光劇團接到教育部關切,希望演一部「本土京劇」,我當下想到了如芳。我在邀請她編劇時,首先表明了官方的期待,而如芳不疾不徐,不管政治正確與否,竟從「外省人家書」裡讀出了感動,想到了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的題材,藉尋帖的動作貫串東晉至民國五個世代,編出的劇本遠遠超越政治的提示,進而至於古往今來流離心事的祕境。這齣戲是京劇與交響樂的跨界,更是如芳跨越現實的例子。
同樣的情形見於《黃虎印》,這是姚嘉文獄中所寫以台灣民主國為背景的小說,而如芳應其所邀編為歌仔戲。這齣戲的政治前提使人未看先擔心,但看戲之後,竟有一種奇異的感受。雖然其中有些片段水準參差,但最後男女主角在廢墟裡的一段愛戀,竟予人〈傾城之戀〉的意蘊。民主國失敗,兩人戀情成就,頹圮之中的情愛滋生,悲喜雜糅,哀樂交織,是人生之荒謬,也是人生之必然。
如芳告知要把她的歌仔戲作品編為劇本集出版,我非常高興,戲曲劇本的出版極為不易,戲曲編劇的同好更為難尋,寂寞艱辛的路上且喜有友人相伴,謹以此文祝福如芳的劇本集廣為流傳。
推薦序2
因堅持而自由 徐亞湘(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
如芳是懂得堅持的人,不論在為人及藝術創作上皆然,我一直這麼認為著。
記得二○○二年如芳還在《表演藝術》雜誌擔任文編時向我邀了一篇稿子,交稿後,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稱職」地向我提出了文稿多處需要修改、調整之處,老實說,當時對於她言之成理的盡責善意,當下我是有些情緒的,但是,我很清楚,打從心底我佩服她的專業態度及自我要求。而往後多年,我則持續地在她的編劇創作及諸多作品中,在在印證了這樣的印象。
當代戲曲編劇實實地難為,肩上既有「傳統」的包袱,後面又有你該「創新」的不斷催促。跨的步伐小,被人嫌保守,步子跨得大些,又被批評失了根本。進退之間,「觀眾要的只是一齣好戲」這樣的普世價值,就常常被高談劇種特質美學的言論所模糊。
如芳很幸運,她並未在「傳統/創新」的擺盪間浪費過多的氣力與能量,創作的前期,她得唐美雲的知遇之恩,讓她的才情可以放心、集中地為好戲的追求而施展揮灑,而她欲召喚的觀眾定位明確,則讓她的作品能不為傳統的形式所縛而有新的可能與視界。如芳在她的〈孤獨而自由——我的歌仔戲編劇之路〉一文中說得好:「我時時提醒自己不能只在乎戲曲的內在程式,畢竟,作品有無足可服人、感動人的藝術性和思想內涵,才是戲曲文本能否與其他文學品類平起平坐的關鍵。」我相當認同她「深入人物的靈魂」、「先說好一個故事」的創作理念,這畢竟是觀眾審美的最大公約數,也才是戲曲藝術在未來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
儘管沒有編劇專業訓練的背景,如芳因著新編戲的創作特質及其秀異才情,仍然為我們創作出一齣齣的好戲,而後者,更是能一顯其藝術堅持意義的關鍵。她的劇本文詞質美,常能寫出人物至情至性,讓人在觀賞/閱讀當下,立即產生認同與共鳴,比如在《凍水牡丹》裡瓊枝的唱詞:「若不是這款的艱苦囝,哪會開嘴唱歌就藏悲聲?」一語把廖瓊枝老師的生命與藝術聯繫點得通透,而在小瓊枝與瓊枝的輪唱中:「我在台頂哭到心肝痛,假戲真作想的是家己無阿娘」、「越來越茫霧是您的面容形影,您甘猶認會出瓊枝仔的歌聲?」則讓我在淚眼中憶起了《夏王悲歌》一劇李元昊憶子段的悲鳴。相同的藝術感動,只因作者有情,情至生春。
台灣當代新編戲曲劇本的發表除散見在相關專業期刊之外,劇本集專書的出版屈指可數。原因無他,一因戲曲編劇少,持續創作且具一定品質者更少;二來是可能的讀者少,小眾中的小眾似乎是難逃的宿命;三則演出的延伸性小,新編戲多為名角量身打造,原有優勢難為他團他人所能複製。所以,編劇是否有高知名度及其作品是否具備一定的文學性,即成為新編戲在舞台閃過片刻光芒後,是否得以文字永銘的關鍵。
當如芳告訴我她的六個歌仔戲劇本將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時,我真為她及讀者感到高興,身為她的戲迷我必須實說,看她的劇本要比看演出有著更大的享受和愉悅,讀者的意會與想像,將遠遠超越舞台上可能會有的局限。看過演出最好,沒看過的讀者也不會遺憾,因為那在閱讀當下的情感流動與藝術交會將會是一致的。
人生的聚合離散在「緣」一字。我雖曾深切地希望如芳與唐美雲的合作能長長久久,但二人各自的發展不也都為歌仔戲創造出不同的藝術可能嗎?念此也就釋然。堅持寫自己想看的戲,堅持下筆前以情先行,堅持編劇心中恆有觀眾在,堅持齣齣得見開創性的如芳,我確信妳的創作因堅持而更自由了!
名人推薦:王安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向陽(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所長).李敏勇(詩人).林谷芳(禪者)
徐亞湘(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鄭清文(作家)
聯名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如芳並不堆砌美文雅詞,一切從深情出發,她的人生體悟極為深刻,心思極為細膩,風生水湧、月落潮生,自然界瞬息萬變皆有感於心,且又不只是少女般的纖細柔情,如芳冷靜觀照,能為歌仔戲注入寬廣的大格局。
——王安祈
施如芳是當代臺灣...
作者序
在劇場的光裡說故事
戲劇(曲)不分東西方,其源頭,都和儀式脫不了干係。劇場原是聚眾乞靈之事呀,劇本因此不比其他文學品類,作者但憑胸中丘壑,在案頭上自給自足地完成,文責自負,光彩獨得。劇本為劇場而生,身為劇作者,註定要與有緣人共創共享作品,「無情」的歷練,從本子寫完的那一刻,才剛開始。
面對二度創作的演員、導演、編腔作曲,面對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來的觀眾,劇本得不得人心、挺不挺得出場面,永遠要當下驗證的。然而,也就是這樣了:聲色一場,戛然而止,和行了一場儀式,或做了一場夢,並無兩樣。
我在最典型的演員劇場以編劇立身。行禮如儀,夢過一場又一場後,終於生出了可笑復可憐的念頭:取幾個舊作,收拾俐落些,用文字留點雪泥鴻爪吧。
□■
「什麼?出劇本書!」一般人肯定叫出來:「看戲多好!誰要讀劇本啊?」雖少喝采,我心意已決。於是,驚動亦師亦友的安祈總監、亞湘老師早早賜了序,自己沒完沒了地大修小改,還「慧眼」獨具地找上青年版畫家王午,在此之前,他根本沒看過這六齣歌仔戲,卻願共襄「盛舉」,以其內熱外剛、不落俗套的木刻,為拙作凝練意象,最後,承蒙聯合文學編印出版,使這本書別有一番繁華落盡的氣蘊。
在藝術之路上,外子柯宗明殷勤守護於我,時時擎歷史之燈為我照見境界,他見我這一迷,就是兩年多,硬是把小書做成了「年度大戲」,真是啼笑皆非,一語道破我的不切實際:「劇本要上舞臺才算數,妳改了本不見得能再演,何必花這種工夫?值得妳精益求精的,是下一個作品!」
欸,我何嘗不知道出劇本書是虛妄的執念呢?但這麼多年來,眼睜睜看著嘔心瀝血寫的作品,落在「首演定終身」、「首演即是絕唱」的循環中,幾乎沒有機會修本重演,來不及看到演出的人,永遠比看過的人多——即使這是大環境使然,我也滅不了創作者的一點志氣呀!
對我來說,每一部新編戲都始於混沌未明的想像,只能老老實實地跌撞進去,同劇中人行住坐臥活過一回,甚至,步步逼到懸崖撒手供出底氣,他們才肯吐出「氣口」與你交心,容你在他們的人身缺憾上作文章。如此貼近生命情態的全本戲經驗,讓我讀到泰戈爾的詩句「我將一次又一次地死去,藉以認識生命的無限」(I shall die again and again to know that life is inexhaustible)時,忍不住掉下淚來。筆下的劇中人們,豈是為了一次亮相而召喚我的?我總得在劇場的生滅不息裡,為他們爭個氣長!
■□
過去,見聞「未完成」的藝術作品,或聽到有人帶著「一定來不及完成」的自覺在創作某作品,總感到莫名悽愴,尤其是後者,「做不完為什麼要開始呢?」我不相信也不願想像,人何以要許這樣的悲願!
直到寫了京劇《快雪時晴》,如幻似真地看見書聖王羲之寫下「未果為結,力不次」,以頓首之姿敬領天意:「牽掛的事沒有結果,終究做不到了呀」;直到父親飄然往生,真的一次也沒有進劇場看過女兒的戲,鈍根的我才認了:寫了那麼多年戲,何曾真正明白生死呢?原來,人生總有一些事,註定來不及。
在父親生命倒數的日子裡,我寫得特別勤、特別多,一琢磨出樣子,就呈到父親面前,他身子快活些,就會戴上老花眼鏡讀劇本。晚年他寫舊體詩,讀起戲曲本子津津有味,「沒看到演出有什麼關係?妳的劇本,老爸可是比別人多讀好幾版呀」,在病榻上,他這樣寬慰過我。我也想,老人家是故意不去看戲的。他要教給我,善解「未果為結,力不次」的遺憾,是劇作家的天命;他要鼓勵我,知音者,可以從文字看見獨立而完整的靈魂。
□■
而母親傳達給我的,則是戲迷大眾的心聲。她說過好幾次:「我最喜歡《大漠胭脂》了,唐美雲作將軍,許秀年作公主,戲演得好,衣服又穿得漂亮……」
啊,二○○三年的《大漠胭脂》!正是這一齣戲,讓我開了心眼:第一次接收到劇中人深刻的召喚,第一次在排練場上,移位到中央的位子,直勾勾地望進名角眼睛裡去。從那一刻起,我更不肯馴服於戲曲的程式,也不想寫那叫我仰望的人與事,因為我知道,我的創作不只是戲,更是有機的生命。「靈犀引路,願得一心人」,往後立主腦、掘靈魂,對應當下,當是為酬知己而寫了。
如今盤點起來,在《大漠胭脂》之後,我已不知不覺地展開光影交錯的探索,再也沒有一個作品,按順敘法,一環一扣地說故事,採場景光,照亮小生小旦的愛恨情仇和一身華服——《無情遊》穿插倒敘,《人間盜》五更燈火掩翳,《梨園天神桂郎君》三股時空扭纏呼應,《帝女‧萬歲‧劫》兩刃相交、血光慘然,小品如《凍水牡丹》,也在意識流裡往來穿透。
重修《大漠胭脂》,驚詫於字裡行間匍匐前進往死裡寫的蠻勁,想當年呵,那是我與唐美雲共同擁有過的純真年代!正是這位名小生發豪語:「不管什麼樣的題材、人物,只要妳寫得出來,我就演得出來!」讓我在歌仔戲的母土上,一念精誠地為她和劇團量身創作,恣肆揮灑,一本接一本寫了十年,練就了「『本』立而道生」的膽識。
■□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至今,我還在劇場的光裡說故事。
我仍然偏愛戲曲。它的聲色歌舞令人愉悅,足以對抗現實世界的不美;它有浸透時間的老靈魂,足以笑看人間煙火中的庸碌與迷茫。不過,戲曲當真需要能與當代對話的故事;好的故事可觀可感可招展,一如人身難得,而我情願寤寐求之,只因為,渴望與更多人分享戲曲曾經帶給我的「神聖時光」。一劇之本若寫得夠好,便能召喚觀眾,召喚創作夥伴,甚至為這文化世故度甚高的表演藝術,召喚出更貼切而美妙的形式。
謝謝邱婷女士,是承傳北管世家衣缽的她挺身製作,讓我有信心為歌仔戲寫出《帝女‧萬歲‧劫》;謝謝廖瓊枝老師,是她拼一身為歌仔戲樹立「不只是明星」的藝術典範,還容我不知天高地厚,戲裡戲外慢慢領略她的好;對於唐美雲,我無意說謝,只想給她一個盡在不言中的擁抱,是她眼底有人性的深、生命的深,觸動我內在的鼓聲,讓我在這條路上有了不尋常的入處。
因為寫戲、作戲,我一次次忍受著作品必然不完美,也一次次地,在時間之流裡乘願再來,試圖在下一個作品彌補上一個作品來不及做到的事。當我為這六齣戲一一新擬故事大綱時,赫然發現,自己真愛用刪節號呀,或許,我從不曾具足了斷劇中人生死的信心,我想說的是,緣起不可思議,板盡處餘音繚繞,戲雖然落幕了,故事還在繼續……
在劇場的光裡說故事
戲劇(曲)不分東西方,其源頭,都和儀式脫不了干係。劇場原是聚眾乞靈之事呀,劇本因此不比其他文學品類,作者但憑胸中丘壑,在案頭上自給自足地完成,文責自負,光彩獨得。劇本為劇場而生,身為劇作者,註定要與有緣人共創共享作品,「無情」的歷練,從本子寫完的那一刻,才剛開始。
面對二度創作的演員、導演、編腔作曲,面對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來的觀眾,劇本得不得人心、挺不挺得出場面,永遠要當下驗證的。然而,也就是這樣了:聲色一場,戛然而止,和行了一場儀式,或做了一場夢,並無兩樣。
我在最典型的演...
目錄
推薦序:一切從深情出發 王安祈
推薦序:因堅持而自由 徐亞湘
自序:在劇場的光裡說故事
帝女‧萬歲‧劫
大漠胭脂
人間盜
梨園天神桂郎君
無情遊
凍水牡丹
施如芳編劇作品演出一覽表
推薦序:一切從深情出發 王安祈
推薦序:因堅持而自由 徐亞湘
自序:在劇場的光裡說故事
帝女‧萬歲‧劫
大漠胭脂
人間盜
梨園天神桂郎君
無情遊
凍水牡丹
施如芳編劇作品演出一覽表